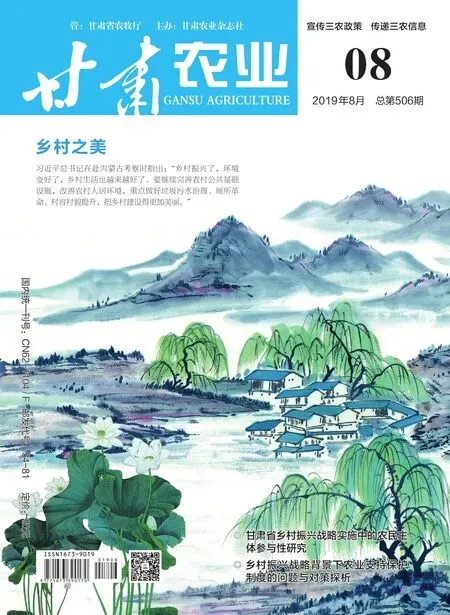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農業支持保護制度的問題與對策探析
李 曌,魏曉卓,邵煒藝
1.江蘇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江蘇 鎮江 212003
2.鎮江市審計局,江蘇 鎮江 212000
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時,明確要求要“完善農業支持保護制度”。事實上,作為一項制度存在形式,我國的農業支持保護制度是進入21世紀以來才逐步形成的,主要包括農業補貼、糧食等主要農產品價格支持、農業保險等一系列政策,成為獨具特色的農業支持保護體系,對于保證糧食安全、實現農民增收、維護農村社會的和諧穩定等均發揮了重大作用,也為實施鄉村振興的戰略目標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然而,由于近年來國內外農業發展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農業支持保護制度也面臨許多新的情況及問題,必須不失時機地對農業支持保護制度中的不適應新形勢發展要求的部分進行改革與完善。鑒于農業支持保護制度包含多項內容,本文僅探析農業補貼、糧食等主要農產品價格支持、農業保險政策等存在的問題,并相應地提出完善以上三項內容的意見與建議,以便有利于國家對農業的支持保護及與鄉村振興目標更好地相適應。
一、農業支持保護制度存在的問題分析
(一)關于農業補貼政策的問題
一般認為,農業補貼政策是我國農業支持保護制度中最重要的內容,而其又主要指自2004年以來陸續實施的種糧直接補貼、良種補貼、農資綜合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等四項,并于2016年將前三項合并為農業支持保護補貼。自實施農業補貼政策后,對提高糧食產量等發揮了巨大作用。然而,農業補貼政策在實施過程中,也存在一些問題,主要表現為:第一,補貼金額仍然較低。在農業生產資料等漲價幅度較大的情況下,農民實際得到的補貼依然是“杯水車薪”,不足以抵消農業生產資料等成本的增加。另外,各個地方的補貼標準與辦法不太一致,農民的種糧效益相對低下,種糧積極性難以得到真正的提高。第二,可能存在著種糧補貼面積申報不實的情況。現在糧食補貼主要應根據種糧實際面積來申報,但由于基層工作人員數量有限,基本上按照農民自行申報的承包地面積,對其內非種糧的部分一般也不進行核減,甚至對于那些已經撂荒的或者已無種糧條件等的土地也納入了補貼范圍,人為因素影響較大。第三,種糧面積和主體的審核或把關存在缺陷。雖然政策要求誰種糧誰得補貼,但實際操作難度較大,各地一般按照農戶承包地面積計發,相關主管部門沒有時間及精力確切審核上報面積。另外,現實中存在許多土地流轉的農戶,在糧食補貼發放到基層的過程中,基層如果把關不嚴,也極易將有限的糧食補貼資金發給承包戶而不是實際的種糧戶,影響發展糧食適度規模經營農戶的種糧積極性。第四,補貼未能突出重點且創新性不夠。現有補貼基本上實行的是按承包地面積等發放的普惠式收入性補貼,而對于那些能自覺提升耕地地力、有利于保護生態環境、發展糧食適度規模經營的農戶及其農機具購置等行為,未能加大補貼力度或新增補貼。第五,存在資金發放層層拖延的現象,政策實施也缺乏有效的監督等[1]。因此,進一步完善農業補貼政策這一農業支持保護制度,顯得尤為緊迫與重要。
(二)關于糧食等主要農產品價格支持政策的問題
糧食等主要農產品價格支持政策主要是指自2004年以來陸續實施的糧食最低收購價及糧油臨時收儲政策等,前者主要適用于糧食主產區的稻谷與小麥,而后者的政策指向是東北、內蒙古的玉米與大豆以及湖北、四川等油菜產區的油菜籽,它們均由政策執行主體負責具體實施事宜。雖然最低收購價及政策性收儲價有利于糧食安全和農民增收,避免了“谷賤傷農”,但其顯然缺乏彈性,有時明顯滯后于國內外市場供求及價格的變化,造成供求結構的失衡,致使整個糧食產業鏈缺乏活力與效益。實際運行與政策初衷漸行漸遠,最低收購價不再是“最低價”,臨時收儲也不再“臨時”,市場機制難以發揮作用,帶來諸多問題,比如糧食庫存巨大、市場競爭力下降、加工企業虧損、財政不堪重負等[1]。2014年國家取消新疆棉花、東北和內蒙古大豆臨時收儲,進行目標價格補貼試點;2014年對食糖、2015年對油菜籽收儲也進行了改革;2016年取消了玉米臨時收儲,但仍繼續執行稻谷和小麥的最低收購價政策。由于近期作為主要口糧的稻谷和小麥的最低收購價仍然偏高,加之收購量并不封頂等原因,也導致了倉容不足、稻強米弱和麥強面弱、加工企業生存艱難、財政負擔重等問題[2]。所以,迫切需要改革與完善糧食等主要農產品價格支持政策,以保護農民利益,穩定糧食生產。
(三)關于農業保險政策的問題
我國是世界上遭受農業自然災害較為嚴重的國家之一,但長期以來農業保險發展滯后。近年來,我國已經開始意識到農業保險在農業支持保護中的重要性,農業保險作為有效分散現代農業發展風險的重要工具和助力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保障手段,其在農業支持保護制度中的地位和權重應該得到大幅提高,因此我國適時建立了政策性農業保險制度[3]。尤其是自2007年啟動農業保險保費補貼試點以來,我國初步形成了多功能的農業保險體系。然而,“大國小農、人多地少”仍是我國基本國情,況且當前農業需要補貼的領域和環節較多,國家尚不具備全面、大規模補貼農業的能力[4]。農業保險當前還存在以下主要問題:地方財政配套資金困難,拖期現象嚴重;農民參保積極性不高,保險面不穩定;保險公司還存在一定程度的“懼農”心理等[5]。因此,加快構建適合我國國情的農業保險體系,既是完善農業支持保護制度的客觀需求,也是服務好鄉村振興戰略的具體體現。
二、完善農業支持保護制度的對策探析
(一)完善農業補貼政策的對策
當前的農業補貼政策應當在保持連續性與穩定性的同時,調整改進“黃箱政策”,逐步擴大“綠箱政策”的實施規模和范圍,完善更具針對性與靈活性且符合國際規則的農業補貼政策[6]。一是在糧種、化肥、農藥等生產資料漲價的情況下,在政策允許及適應規則范圍內,整體加大補貼力度[1]。同時,各地可以根據其具體情況,規范補貼標準及辦法。二是借助信息化成果發放補貼。比如可以運用信息遙感技術全面采集種植業數據,依托種植業大數據系統發放補貼[2]。而實行土地流轉的農戶,若通過這種方式取得了種糧補貼,應當在流轉費中自覺扣除,以維護實際種糧戶的利益,提高其發展糧食適度規模經營的積極性。三是創新補貼形式。增加有利于保護生態環境的補貼,進一步推進化肥、農藥減量增效,廣泛開展生物農藥、有機肥使用等;而對于有利于提升耕地地力的農戶,如自覺進行輪作休耕、深松整地、秸稈還田、殘膜回收利用等繼續加大補貼力度。另外,對于農業科研及技術推廣、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實行農業結構調整及鄉村產業發展的給予一定的支持[3]。四是實行重點補貼。支持糧食適度規模經營補貼要重點向種糧大戶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傾斜,并通過貼息、現金直補等多種方式,解決其“融資難、融資貴”,推進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為農業支持保護制度提供“助推器”[6];繼續完善農機具購置補貼,推進農業全程機械化。五是簡化補貼申請、審核及發放流程,健全監督體系,確保糧食補貼及時準確地發放給實際一線種糧戶。
(二)完善糧食等主要農產品價格支持政策的對策
現階段對于該項政策,政府宜按“價補分離、市場定價及主體多元”的改革方向,分品種繼續探索,著力走出一條兼顧農民利益、農業發展和財政負擔、政策執行的新路子。比如:目前仍需堅持并完善稻谷、小麥最低收購價政策,即可以保留稻谷、小麥最低收購價格政策框架,但要降低最低收購價水平,降到正常市場價格的80%左右,主要是起“托底”作用,特殊情況下才啟用[7]。事實上,從2014年開始,國家下調了稻谷最低收購價。2018年,作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開局之年,國家首次調低小麥、繼續調低稻谷最低收購價。2019年繼續調低小麥最低收購價,維持稻谷最低收購價。同時,為了防止出現賣糧難等情況的發生,可以引導具有資質的多元市場主體入市收購。為了保障貧困地區的農產品不愁賣,農民增收多條路,力爭實現所有具備條件的國家級貧困縣電子商務全覆蓋。糧食庫存不宜超過年消費量的40%[2],要多措并舉去庫存,如定向、包干銷售及拍賣機制等消化庫存;實施坡地退耕還林還草、好地輪作休耕、秸稈還田等,將“藏糧于庫”變為“藏糧于地”及“藏糧于技”。要推進農業由增產轉向提質,加快國內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積極發展綠色、健康、安全、緊缺的優質農產品,逐步替代“大路貨”[2],引導農民種植高品質水稻、小麥等。
(三)完善農業保險政策的對策
根據我國農業保險所面臨的現狀及問題,要充分認識到農業保險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的重要性,樹立“農業保險+鄉村振興”理念,圍繞新時代鄉村振興目標進行相應改革。目前主要是持續推進農業保險擴面、增品、提標。一是實現口糧等主要糧食作物全覆蓋;二是加快建立主要農產品市場風險保險制度;三是加快構建多層次大災風險分散制度。據此有建議指出可從補貼力度與農戶類型兩個維度,來構建包括商業性農業保險等在內的全方位、分層次的農業保險體系[4]。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還要求“推進稻谷、小麥、玉米完全成本保險和收入保險試點,擴大農業大災保險試點和‘保險+期貨’試點,探索對地方優勢特色農產品保險實施以獎代補試點”等。因此,要通過積極構建與鄉村振興目標相適應的全方位、多層次的農業保險體系,更好地完善農業支持保護制度,實現農業保險機制與鄉村振興戰略的深度融合,有效助推鄉村振興工作。
三、結語
完善的農業支持保護制度對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至關重要。根據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關于“完善農業支持保護制度”的精神以及2018年、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對“完善農業支持保護制度”作出的系統部署,本文分析了農業支持保護制度中有關農業補貼、糧食等主要農產品價格支持、農業保險政策等存在的新情況、新問題,并據此相應地提出了一些積極的思路與建議,以便更好地完善農業支持保護制度,從而使其能夠充分適應現代農業轉型升級和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客觀需求,爭取早日實現“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的鄉村振興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