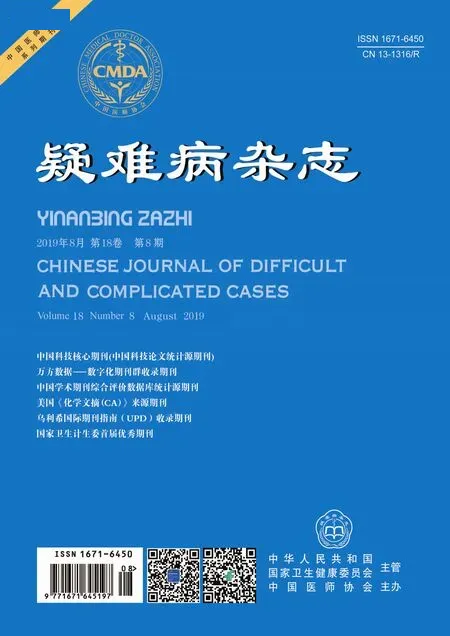具有非典型影像改變的肺泡蛋白沉積癥3例報道并文獻復習
趙婷婷,蔡后榮,李燕,李慧,孫琦,張英為
肺泡蛋白沉積癥(pulmonary alveolar proteinosis,PAP)是一種罕見的肺部疾病,在1958年被Rosen及其同事首次報道,其患病率大約4/100萬[1]。胸部CT表現為“鋪路石征”或“地圖樣”分布,結合支氣管鏡肺泡灌洗液(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BALF)呈現特征性的過碘酸雪夫(periodic acid schiff,PAS)染色陽性物質沉積即可確立診斷[2]。但當胸部CT表現不典型,BALF呈PAS陰性反應時,易出現誤診。現報道3例胸部CT表現不典型的PAP,并結合文獻進行復習,提高臨床醫師對非典型PAP的認識。
1 臨床資料
例1.男,53歲。因“體檢發現肺間質改變5月”于2008年9月1日入院。患者5個月前體檢時全胸片示肺間質改變。因無不適,未進一步診治。1個月前復查胸片較前未見吸收,查胸部CT示雙肺縱隔旁及胸膜下少許磨玻璃影及網狀影(圖1A、1B)而入院。從事鑄造工作10年。入院查體:T 36.0℃,P 72次/min,R 20次/min,BP 110/64 mmHg。雙肺未聞及干濕性啰音,心腹查體未見異常,雙下肢無水腫。初步診斷:職業相關性間質性肺炎?入院后完善檢查,血氣分析(未吸氧):pH 7.424,PaO279 mmHg,PaCO238.4 mmHg;血常規、生化、免疫均正常,自身抗體、血抗中性粒細胞胞漿抗體(ANCA)均陰性;肺功能示輕度混合性通氣功能障礙。為進一步明確診斷,9月4日行胸腔鏡下肺活檢。術后病理提示:多數肺泡內見大量粉染蛋白樣物質充盈,顆粒狀;特殊染色:PAS(+),PAS-D(+),AB(-),GMS(-)(圖2A見封3)。明確診斷為肺泡蛋白沉積癥。綜合患者臨床表現、血氣分析及肺功能等,未予特殊處理,醫囑出院。門診隨訪5年,病情穩定。后失訪。
例2.男,37歲。因“反復咳嗽、咯痰1年余”于2014年11月12日入院。患者1年前開始出現咳嗽、咯痰,痰色白質稠,伴活動后氣喘,無發熱,抗感染治療療效不佳。2013年11月外院查胸部CT示兩肺斑片影,密度不均。PET/CT示兩肺多發片絮狀及結節狀高密度影,部分結節代謝增高。行電子支氣管鏡檢查未見異常,臨床考慮肺結核,予利福噴丁、乙胺丁醇、吡嗪酰胺等試驗性抗結核治療。治療約9個月后癥狀未緩解,后至我院門診復查胸部CT示:病灶較前無明顯吸收(圖1C、1D)。故入住院。個人史及家族史無特殊。入院查體:T 37.1℃,R 20次/min,P 66次/min,BP 129/73 mmHg。口唇無紫紺,兩下肺可聞及捻發音,心腹查體未見異常,雙下肢無水腫。初步診斷:間質性肺炎。
入院后完善檢查,血常規、生化、血氣分析、肺癌四項、免疫常規均正常;自身抗體、ANCA、痰涂片找抗酸桿菌均陰性;T細胞γ干擾素檢查陽性。肺功能檢查示中度混合性通氣功能減退,彌散功能基本正常。為進一步明確診斷,2014年11月17日行胸腔鏡下肺活檢。術后病理示:送檢肺組織見部分區域肺泡腔、遠端氣道內大量均質、嗜伊紅樣物質沉積,部分區域肺泡隔炎性增寬,組織學符合肺泡蛋白沉積癥(圖2B見封3)。予霧化吸入重組人粒細胞巨噬細胞刺激因子治療(75 μg,每天2次,隔周應用)。后失訪。
例3.女,48歲。因“反復咳嗽、氣喘1年余,加重伴發熱8 d”于2016年3月25日入院。患者1年前無明顯誘因出現咳嗽,咯少許白黏痰,伴活動后氣喘。2015年5月于當地醫院查胸部CT示左下肺實變,兩肺間質性炎性反應。行支氣管鏡檢未見異常。1年來癥狀遷延,時輕時重。8 d前受涼后癥狀加重伴發熱,體溫最高38.6℃,當地醫院治療效果不佳,遂來我院。既往有甲狀腺功能減退病史。入院查體:T 36.3℃,R 20次/min,P 67次/min,BP 122/72 mmHg。口唇無紫紺,雙肺呼吸音粗,雙下肺可聞及捻發音,余陰性。入院血氣分析(鼻導管吸氧2 L/min):pH 7.441,PaO280 mmHg,PaCO239.9 mmHg。初步診斷:(1)間質性肺炎伴感染;(2)Ⅰ型呼吸衰竭;(3)甲狀腺功能減退癥。入院后檢查,血WBC 22.3×109/L,N 80%,Hb 111 g/L。肺功能檢查示中度以限制為主的混合性通氣功能減退,彌散功能重度減退。胸部CT示兩肺彌漫性磨玻璃影及網狀影,部分斑片及實變影,伴小葉間隔增厚(圖1E、1F)。為明確診斷,2016年4月5日行胸腔鏡下肺活檢。術后病理示:多數區域肺泡腔內見多少不等的嗜伊紅蛋白樣物質沉積,伴多量膽固醇結晶形成,組織學符合肺泡蛋白沉積癥(圖2C見封3)。予霧化吸入重組人粒細胞巨噬細胞刺激因子治療(150 μg, 每天2次,隔周應用),病情改善后出院。2016年8月因癥狀加重伴發熱再次入住我科,查血WBC 20.6×109/L,N 72.2%,Hb 77 g/L,PLT 65×109/L。遂于8月29日行骨髓穿刺檢查,明確為多發性骨髓瘤(MDS-EB-2)。2016年9月19日開始行CAG方案化療(阿柔比星12 mg,靜脈注射,d 1~8,阿糖胞苷 0.015 g,皮下注射,q 12 h,d 1~14,重組人粒細胞刺激因子注射液 300 μg,皮下注射,d 1~14,白細胞<20×109/L用)。化療期間癥狀改善不佳,2016年12月死于嚴重肺部感染。

注:A、B.例1 胸部HRCT示雙肺縱隔旁及胸膜下少許磨玻璃影及網狀影;C、D.例2 胸部HRCT示兩肺網狀陰影、磨玻璃結節影及部分實性結節影;E、F.例3 胸部HRCT示兩肺彌漫性磨玻璃影及網狀影,散在斑片影,伴小葉間隔增厚
圖1 胸部HRCT檢查影像學變化
2 文獻回顧
先后以“非典型”并“肺泡蛋白沉積癥(atypical pulmonary alveolar proteinosis)”以及“肺泡蛋白沉積癥”并“誤診”為關鍵詞在中國知網和萬方數據庫中檢索,以“atypical pulmonary alveolar proteinosis”為檢索詞通過PubMed數據庫進行檢索,檢索時間自1980年3月1日—2018年12月31日,并重點關注誤診病例的影像特征描述部分,剔除兒童病例,共檢索到中文文獻2篇,1篇為個案報道,1篇為臨床總結分析;英文文獻12篇,均為個案報道,見表1。

表1 非典型PAP臨床資料比較
3 討 論
肺泡蛋白沉積癥(PAP)是一類以肺泡表面活性物質在肺泡腔的異常聚積為特點的疾病,其機制為肺泡巨噬細胞清除表面活性物質能力下降[14]。根據發病原因不同,PAP分為3類:(1)自身免疫性PAP,是由于粒細胞—巨噬細胞集落刺激因子(granulocyte macrophage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GM-CSF)自身抗體存在所致;(2)先天性PAP,由于編碼表面活性物質基因突變所致;(3)繼發性PAP,由于血液系統或實體惡性腫瘤、無機粉塵吸入、化療、機會性感染、賴氨酸尿性蛋白質不耐受等引起[15]。
PAP往往起病隱匿,亞急性病程[16]。臨床表現并無特異性,大約有1/3的患者無明顯癥狀,咳嗽、氣喘為較常見癥狀;部分患者可有杵狀指及肺部濕啰音[14]。
胸部影像學檢查是診斷PAP的重要手段。典型的胸部CT特點為“鋪路石征”和“地圖樣”分布。當HRCT提示以上征象時,診斷PAP并不困難。但尚有PAP的影像學表現并非典型影像特征,根據文獻報道這些表現包括:(1)結節影,包括部分實性結節[6]、孤立的純磨玻璃結節[4,7]、兩肺多發的磨玻璃結節[9]、均勻一致的小葉內結節[2]、部分鈣化的結節。(2)磨玻璃影,除磨玻璃結節影外,尚有片狀分布的磨玻璃影,但不與小葉間隔增厚重疊存在。(3)局限分布的“鋪路石征”[6]。(4)網狀陰影[3,12]、斑片及實變影[3,5-6]。(5)不同的影像學特點之間可以相互演變[6]。綜上所述,當出現上述不典型征象時,較易出現誤診。PET/CT對于PAP的診斷并無明顯幫助,甚至會增加診斷難度[5]。
特征性的HRCT表現以及典型BALF結果對于診斷PAP是足夠的,不需要組織病理學檢查,但對于影像學表現不典型的病例,僅靠典型的BALF診斷是不夠的[17],此時還需要組織病理學確診。本次報道的3例患者均經開胸肺活檢確診。文獻報道的病例中,外科肺活檢取材是主要手段。故當患者的影像學無明顯特異性、支氣管鏡診斷難以明確時,應盡快行外科肺活檢明確診斷。
先天性、特發性PAP或輕型的PAP可應用非侵襲性醫療策略,如皮下注射或霧化吸入GM-CSF、單克隆抗體、血漿置換、高壓氧等。繼發性或重型PAP需全肺灌洗[1]。全肺灌洗目前被認為是最有效的治療方法,最終的治療方法則是肺移植[1]。
綜上所述,隨著越來越多的PAP被診斷及報道,PAP的CT表現多種多樣,已不局限于“鋪路石征”或“地圖樣”分布。當患者胸部CT出現分布各異的磨玻璃影、結節影、實變影及網狀陰影時,在鑒別診斷時需考慮到PAP的可能;對于BALF或TBLB診斷困難者,需盡快完善外科肺活檢,以免延誤診治。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聲明
趙婷婷: 文獻檢索、總結及論文撰寫;蔡后榮:文章修訂;李燕、李慧:提供病例資料;孫琦:核對病理圖片;張英為:提出研究思路及修訂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