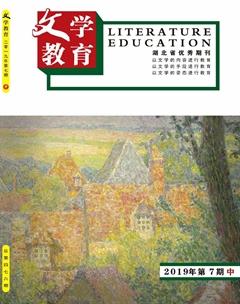我的姥爺我的爺
郝文明,我的姥爺,去世了,在襄陽的太平店鎮。
從1935年5月,到2019年4月,八十四年的人生,風風雨雨,起起伏伏。總之,是不平靜。
姥爺是老共產黨員,在雙溝、老襄陽縣、太平店當過干部。為革命奮斗了幾十年,沒有在領導崗位上為家庭、為子女撈過一點好處,沒有占公家一點便宜。相反,舍己為公的事他倒是做了不少。
代表單位到縣里開會,六十多里的路,他寧可頂著烈日、滿頭大汗地騎自行車,也不搭汽車,只是為了給單位節約車費。到省城為單位跑項目,他的包里總是裝滿了饅頭和咸菜,能吃上好幾天,就是為了給公家省點用餐補助。退休后,看到單位的公廁臟了,坑槽滿了,他拿起自家的掃帚、鐵鍬、水桶,就當起了義務清潔工,這一當就是二十年……
在工作中,因為過于堅持原則,有脾氣,姥爺得罪過人。但是,不可否認,他為人善良,正直且無私。
大概兩歲左右,我開始記事。成年后,腦子還時不時回想起在樊城一橋某個家屬院玩耍的情景。而記憶的閘門正式打開,卻是在太平店,這個漢江邊的小鎮,曾經的全國明星鄉鎮。
當時,我母親是太平店中學的英語老師,之后又在當地中心小學任教。父親是當時襄陽縣報的記者、編輯,工作地點在樊城藝苑巷。因為父母分居兩地,而且工作都太忙,我大部分時間和姥爺姥姥一起生活。
為了感謝養育之恩,長期以來,我母親一直讓我以“爺爺奶奶”稱呼他們。記得有一次,姥爺抱我出門逛街,路上遇見熟人,被問到“老郝(襄陽方言讀he,陽平),這是你孫娃子?”姥爺回道:“不是的,是外孫子。”我見到母親后,就問“啥是外孫子”“為啥不是孫娃子”,心里憤憤然。
在姥爺姥姥家,姥爺主外,姥姥主內,中國傳統家庭相處模式。讀幼兒園時,每天早上,天剛亮,吃完早餐,我到家對面的小賣部,在昏黃的燈光下,掏出幾分錢的零花錢,買一小包快餐面,當零食。之后,姥爺便推著老式的永久牌自行車過來,一把將我抱起來,放在前面的單杠上。他再一個橫跨上車,雙腳穩穩踩在腳踏上,不緊不慢地騎著,送我上學。
當時大概是夏天,空氣里水分足,十多分鐘的路程。我的雙手交錯扶在車把上,等到了幼兒園,我一摸手,涼涼的,原來手背上已經凝滿露珠。
一天夜里,我的急性喉炎發作,氣管壁充血嚴重,導致氣管堵塞,無法呼吸。姥爺發現后,急匆匆把我送到鎮衛生所。醫生用手術刀放掉淤積的血,再給我輸上液,我這才撿回一條命。
我上小學后,姥爺工作的單位開始制作菌種,能夠長蘑菇。菌種的原料是棉絮碎屑和木頭渣,必須清洗過后,塞在小開口的圓形玻璃瓶里,用木塞封上,再酒精燈或者特制高壓鍋高溫加熱殺菌后,才能往里放菌類。
我之所以記得這么清楚,是因為姥爺經常讓我給他幫忙。尤其是,他常讓我注意特制高壓鍋上壓力表,一遍遍叮囑我別把火燒太大。我倒是不辱使命,目不轉睛地盯著壓力表上的指針,好長時間。
有一次,姥爺單位的工人們正從倉庫里拿出數百個空玻璃瓶,放在家屬院的空地上,用水管沖洗,準備重新使用。我當時不知道是看了《大俠霍元甲》,還是《楚留香傳奇》,反正是部武俠片,一時覺得自己神功護體,能夠一腳跳得老遠。看著眼前大概只有腳踝般高、一人多寬、擺放整齊的長方形玻璃瓶陣,我突然有了飛越的沖動。就退后幾步,沖刺,縱身一跳……
結果,嘩啦嘩啦,玻璃瓶陣被踢倒,碎了一地,我的左小腿重重磕在玻璃碴上。當我看到左小腳上,突然長出一個拇指大小的玻璃片,還有血,一下就嚇暈過去。之后,我很快被送到衛生所,玻璃片取了出來,傷口上了藥,那個疼。當然,沒有躲過姥爺的罵。
就這樣,我在姥爺姥姥家,度過了幼兒園、學前班和小學一、二、三年級。直到我八歲,我母親調離了原單位,到了襄陽縣政府在張灣鎮的新治所,與父親團聚,我才離開太平店,離開了和姥爺姥姥朝夕相處的生活。
其后,我父母和我逢年過節都會去探望姥爺姥姥。在午后,我們和姥爺沿漢江河堤逛逛,看看千年銀杏樹,看看老街,和中心小學以前的住處,不時還能遇見多年不見的熟人,一聊聊很久。
姥爺與作家李敖同歲,算是李大師的粉絲。內地還能不費力地收到鳳凰衛視的時候,姥爺經常收看《李敖有話說》,和李敖一樣臧否人物、月旦春秋,觀點總能與眾不同。每每我問及他生活過的年代,他目睹的風波,他親歷的事件,他也總能直言不諱,讓記憶得以傳承。
大概五年前,姥爺突然中風,用了不少保健品,進過不少次醫院,但最終選擇在家里休養。一直到今年4月20日,他突然去世。細節上難以言說,總之,他離開時,親人環簇,神態安詳。
靈棚搭起,安放遺體的冰柜、遺像、長明燈、香爐、花圈,置放停當,然后是哀樂聲、嗩吶聲。我長跪在靈前,火紙一張張地燒,舍不得讓盆中的火熄滅。我的姥爺,我的“爺爺”,一路走好。
朱科,湖北襄陽日報首席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