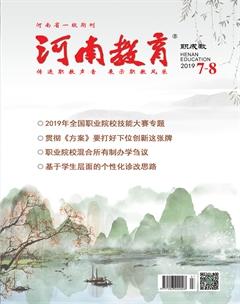不為彼岸只為海
崔志鈺
今年的夏天特別熱,熱得讓人難以靜下心來思考與寫作;也正因為熱,只能蝸居在家,做一些讀和寫的事——任何事情都有積極的意義,關鍵在于自己的心態。
人的表達方式是多樣的,說是一種表達,寫也是一種表達;有的人能說,有的人善寫。這些其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每個人都要尋找到一種適合自己的表達方式。
近些年,我從未停止過“胡思亂想”,受能力水平所限,這些想法是凌亂的,不成體系的,有的想法已付諸實踐,有的想法卻成了空想。想回望一下自己的思路歷程,想通過這種階段性的回望讓自己“深刻”起來,想留下這些思維的“影子”,想為自己的四十年留下些回憶,想對自己有一個好的交代……人就是這樣,往往有一種負重感。
有人說,人來到這個世界是為了看日出,因為每天都有日出,所以日子每天都是新的,每天都有期盼和念想。我也有自己的念想,就是怎樣使自己的每一天都不虛度、富有意義,不辜負生命,不虧欠歲月,每天以全新的姿態迎接日出。也有人說,人生如同遠航,只為彼岸不為海。我卻不愿茍同,彼岸固然重要,這是我們要到達的地方,然而有時會突然困惑,到達又是為了什么?難道我們的出發就是為了到達嗎?近些年,自己相繼被評為省特級教師、正高級教師,獲得了省教學名師、省人民教育家培養對象、全國黃炎培職業教育獎、全國萬人計劃教學名師等稱號,似乎正在抵達所謂的“彼岸”,這難道就是我的目標嗎?我在內心深處不停地問自己,也不停地告誡自己。這種在別人眼中的“彼岸”并非是我的“目的地”,我的初心始終是“不為彼岸只為海”。教育其實是沒有彼岸的,教育只有地平線,而地平線只能逐漸地靠近,永遠無法抵達,所以我們的“航行”只能永遠在“海”上,遼闊的海洋正是我們揮灑汗水、劈波斬浪的理想“舞臺”。汪國真說過,既然目標是地平線,留給世界的就只能是背影。教育的魅力也許就在于這“背影”。人生的意義也在于這“背影”。
人是意義的存在,這種意義是一種自我感知。同樣一件事,對有的人有意義,對另一些人可能就沒有意義,意義是因人而異的;同樣一件事,在某一階段可能富含意義,而在另一階段可能就會失去意義,意義是因時而異的。我始終認為,要讓生活富有意義,你就必須賦予生活以意義,意義其實是自己賦予的,不要太在乎別人眼中的意義,如果你太在乎別人眼中的意義,就會被意義所困,就會掉進別人的意義之網。意義是自我賦予的,當然這種自我賦予應符合社會的主流價值,不是一種自我封閉,但必須要有自己的定見,并設法與主流體系保持理性的距離,在相對的孤立中完善自己。
有一年我到五臺山旅游,在一個景點墻上看到醒目的四個大字“活在當下”,當時就非常感慨:我們把太多的精力放在了過去和未來,有的人始終活在過去,陷入過去的泥潭中難以自拔,有的人被過去的功名所累,有的人被過去的遭遇所絆,卻沒有意識到“前塵往事成煙云”,過去只是一種經歷而已;有的人活在未來,為了未來的美好而寧愿犧牲當下,卻沒有意識到“人生只有三萬多天”。對“活在當下”,若是在以前,我肯定會鄙視這種生活哲學,而現在我認為這是一種值得追求的生活境界。作為教師,教育生活占了人生最重要的光陰,“活在當下”就是要追尋教育的現實美好,讓每一天都富有意義,只有追尋教育的現實美好才能開創更美好的未來。
很多人說我已經到達了作為一個教師的最“高峰”,這顯然站在功利化視角,以所謂的職稱和榮譽作為主要衡量標準。作為一名教師,應該會經歷從功利邁向非功利的過程,當然有的教師可能一輩子難以擺脫功利的束縛,我很慶幸自己在人生的不惑之年開始擺脫功利的枷鎖。盡管一個教師可能已經站在了“功利”教育的最“高峰”,但是他可能還站在“非功利”教育的山腳下。一個人只有拋棄功利的思維,沒有了功利的羈絆,他才會走得更加堅定,也會走得更快、更遠,因為他已經遠離世俗的功利,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心靈旅程”。
我想象過自己能走多遠,我也想象過我們教學改革研究的最終形態呈現,甚至夢見過自己到達目的地的神態,然而占據我內心深處的始終是“旅程”,想那么多干什么,走就是了。既然“不為彼岸只為海”,又何必苛求。在心中描繪出理想的教育形態,執著前行,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責編 ?王鵬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