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軍旅作家徐懷中 盡最后力量去完成精彩的一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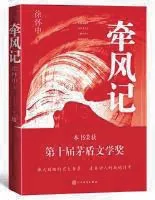

《人民文學》主編施戰軍、副主編徐坤在徐懷中家中商討文稿(朱向前攝)

去年徐懷中、莫言、朱向前師徒在軍藝文學系(資料圖)
90歲高齡的著名軍旅作家徐懷中,憑借長篇小說《牽風記》榮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這是軍旅文學的榮耀,也是當代文學的傳奇。
他是從槍林彈雨中走過來的老八路,戎馬生涯,筆耕不輟,《我們播種愛情》《無情的情人》《西線軼事》《阮氏丁香》《底色》都是膾炙人口的佳作。年已九旬,又捧出了長篇新作《牽風記》。這部小說,既是作者對戰爭與人性的深刻沉思,也展現了他矢志不渝的寫作追求:“盡最后力量去完成精彩的一擊。”
兩部短篇小說打了一個前哨戰
《牽風記》是一個理想主義的敘事文本,是一種新的審美建構和想象,是一種浪漫自由精神的張揚。這在中外戰爭文學中都是不多見的,尤其是在中國軍旅文學中更是獨樹一幟。徐懷中說:“我很高興,沒想到還能獲獎。追求某種新的構建,這種意圖肯定是存在的。我注意到你發表在《解放軍報》及《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叢刊》上的兩篇文章,提及‘超越性寫作’這個概念。我寫《牽風記》沒有寫作提綱,先后有過兩個塑料硬皮小本子,偶爾想起一個生活細節、一句有意味的話,便隨手記下來。也抄寫過一些古人先賢的格言,及有關文學創作的一些名家語錄,用以激勵自己。其中便記錄下了愛默生的這樣一段話:‘太陽白白照亮了成年人的眼睛,可它一直透過孩子的眼睛照亮了他們的心靈。熱愛大自然的人,是那種內外感覺仍然協調一致的人,他在成年之后依然保持了孩童般的純真。’整個寫作過程,愛默生的這段話一直縈繞在我的腦海。”
1999年第一期《人民文學》發表了徐懷中的短篇小說《來也匆匆,去也匆匆》,2000年第一期《人民文學》又發表了徐懷中的短篇小說《或許你曾見到過日出》。小說自然平淡到極點,這些作品都是在為這部集大成之作《牽風記》做準備吧?
徐懷中說:“集大成之作不敢當,但寫那兩個短篇,確實是為十多年以后才姍姍來遲的這部長篇小說打了一個前哨戰……小說開篇,正是由這樣的一個匪夷所思的生活細節切入,無形中為情節的展開帶來了一層空幻的神秘感。”
“必須完全放開手腳作最后一擊”
90歲寫出一部具有嶄新審美觀念與文體風格的《牽風記》,這實在是一件很有意味的事情。促使徐懷中創作這樣一部作品的動力,或者說哲學依據是什么?
徐懷中說:“隨野戰軍挺進大別山這段經歷,是我寫作生涯中至為珍貴的一個題材。我暗自發誓,不把它團弄到完全滿意的地步,寧可窩在手里,也不拿出去。正如你所說,歷經滄桑風風雨雨,跨越世紀門檻,一路過來了。我不再瞻前顧后,最后關頭,必須完全放開手腳作最后一擊。希望能以一副全新面孔示人,如一只鳥兒獨立枝頭,避免與任何人雷同。其實,所謂獨創性夠幾分成色,無明確界限,只在讀者心中。話又要說回來,《牽風記》意在憑借自己戰地生活的積累,抽絲剝繭,織造出一番激越浩蕩的生命氣象。戰爭背景最大限度地被隱沒被淡化了,小船撥轉頭來,駛入了亦真亦幻的另一重天地。小說的文體風格,自然而然與詩歌——最早產生的這種古色古香的文學體裁相契合。適宜如詩歌藝術那樣無限開拓想象空間,充分發揮抒情性,以至于汲取詩歌聲調節律的醇美與韻致。”
“我是在戰爭交響樂熏陶之下長大成人的,文韜武略馬革裹尸,那種無可替代的熾烈的藝術魅力,時時在吸引著我,何嘗不想寫出一部概括性極強的大部頭戰爭小說呢!但我不曾給自己設定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偉大目標,那樣怕只能是苦害自己了。但就我的寫作心態而言,卻又不肯屈就現狀,不肯向文學藝術時尚化妥協退讓,時常處于一種心有不甘的情緒之中。仿佛一個建制部隊,因為未能達成戰斗任務不得不退出戰場,以至于被取消了番號,不知道這樣的一種心境年輕一輩人能否理解?”
徐懷中說:“‘七七事變’以后,大量知識分子如百鳥朝鳳,從大后方各地會聚于延安寶塔山及各大戰區前線,以自己一腔熱血,為服務戰爭與根據地建設作出了不可或缺的巨大貢獻。我在太行山中學讀書時,從校長到所有男女教師,大都是從北平、上海、南京、重慶來的。我所在的第二野戰軍總部及各縱隊宣傳部長,大多是從國外回來的留學生。解放戰爭末期,又有大批知識分子加入到革命洪流中來,為新中國開國大業準備了雄厚的人才隊伍。這種情況令我感觸很深,所以對我而言,知識分子的形象在軍事文學作品中應該占據一定地位,是自不待言的。”
大美之音,強化了小說的主題內涵
小說中多次描寫汪可逾彈奏古琴,給在場者留下了刻骨銘心、超越時空的記憶。其實,震撼人心的不是外在的旋律,而是這種音樂存在對人心靈的沖擊。徐老在描寫彈奏古琴的段落時,內心聽覺響起的是什么樣的音樂?徐懷中:“《琴賦》的作者嵇康講:‘在我看來,萬物都有盛衰,唯音聲不變(譯文)。’那么也就是說,我們的先人削桐為琴繩絲為弦,所制作出的第一張古琴,彈奏出的第一個單音,至今還應該是原本原樣存在的。汪可逾一生夢想所追求的,正是逆時針回返歷史的原點,聽到這個世界上最初始發出的那一聲古琴空弦音。古琴,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一個特別光彩的符號出現在這部長篇中,是塑造汪可逾藝術形象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同時,我也借用這件古老樂器的大美之音,不斷延伸與強化了小說的主題內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