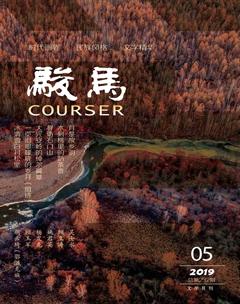懷念
李洪英
一直想拿起筆寫篇紀念父親的文章,可每每坐下來,傷感備至,情感難控,又無從下筆了。父親,書寫上就兩個字,我卻整整琢磨了八年。
八年前,父親因突發腦出血,術后昏迷了十六天,便永遠地離開了我們……
父親出生在黑龍江省雙城縣,是爺爺奶奶的獨苗兒。那時的三口之家,日子過得相當殷實。父親很小的時候,爺爺奶奶突然間相繼莫名其妙地去世。有關那段往事父親很少提及,可能是不愿意觸及內心的痛楚吧。但我長大后從史料和一些文藝作品中才知道了真相:爺爺奶奶是死于民國時期的一場鼠疫。這是當時在哈爾濱周圍流行的一種新型鼠疫——肺鼠疫,它可以飛沫傳染,當時的醫療條件對此是無可奈何的。爺爺奶奶居住的縣城也遭到了那場鼠疫的浩劫,他們就這樣過早地離開了人世。作家遲子建的長篇小說《白雪烏鴉》就描寫了那段歷史,后來還拍成了電視劇,上了銀幕。
父親1948年參加工作,當時在黑龍江省雙城總工會文工隊。1950年父親和當時文工隊的幾個同事一起進入了中國林業文工團,駐地在沈陽,再后,由沈陽遷至哈爾濱。上世紀60年代國家大規模開發建設林區,中國林業文工團又遷入伊春林區。
聽母親回憶,那時的條件極其艱苦。由于工作的特殊性,經常搬遷,父親單位就給每戶發了兩個大木頭箱子。在我的記憶里,那兩個箱子一直伴隨著我走過了童年、少年……乃至現在,依然記憶猶新。因為當年無論怎樣搬遷,那兩個箱子里一直裝著我們家的全部家當啊!進入林區,條件更加惡劣。文工團常年在基層演出,父親很少在家,家里的瑣事都由母親一人操持。當時父親在文工團很繁忙,他是多面手,從創編到后勤,父親干一行愛一行,不論從事哪個行當,都任勞任怨。
在一次巡回演出中,舞臺燈光出現了故障。父親不顧他人的勸阻,決定親自去排除,當爬到那盞掛在十多米高的故障燈前時,他不慎掉落下來……
這件事父親從來沒有和我們提起過,多年后母親告訴我們:那次父親摔得很重,他的健忘,還有不時的絮絮叨叨,乃至動不動的無名之火,都和當年那場意外事故留下的后遺癥有關。但父親從來不認可。
父親無論是工作還是生活中,從不與人爭高低。鄰里之間也是如此,左鄰右舍住著,難免磕磕碰碰,每每母親抱怨時,父親總是淡淡一笑,“隨他去吧。”還寬慰母親吃虧是福。就是這句話,在此后的日子里讓我們有了更多的感悟……
父親一生淡泊名利。
文革后期,父親調到伊春市政府信訪辦工作。那期間文革剛剛結束,信訪辦的工作量很大。父親一上任,就把全部的精力都投放在工作上,就是下班時間也不得休息,常有上訪人員找到家里。有送禮的,有訴冤的,還有上門威脅的……對此類事情,父親認真對待,從不給人臉色看,趕上飯時還熱情地留人家吃飯。父親對待工作認真負責,從不馬虎懈怠,用母親的話說:“你爸滿腦子就是工作,家里的事什么都不想。”
后來,經過考核,父親借調到中央國務院辦公廳工作了兩年,主要是從事黑龍江省在文革期間造成的冤假錯案的平反工作。那時,父親的空間很大,抽調北京的工作即將結束時,領導找到父親問是否愿意留在京城工作,父親婉言拒絕了。一大家子人,父親沒法把家安在北京。領導又說,那就回省城吧,父親還是婉言謝絕。最后父親回到了伊春,上級安排父親擔任歌舞劇院院長,父親沒有去報到,仍然回到了原來的信訪辦。
父親就是這么任性。后來中央辦公廳的同志一再叮囑,今后不論是父親個人工作安排還是家里有什么困難,包括子女的工作等等,只要提出來,組織都會考慮的。但父親從退休到去世,從沒向組織提起過。有時,母親嘮叨幾句,父親總是和顏悅色地告誡我們:“做人要踏實,要憑自己的本事,不要指望別人,靠一時靠不了一輩子……”
淳樸的語言和淳樸的忠告在我們兄弟姐妹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也使我們形成了良好的家風。我們的兄弟姐妹也一直秉承著父親做人的良好品德。
父親多才多藝。
父親會拍照片,這在當年令人另眼相看。家里每個人留存下來的照片很多:一幀幀,一幅幅,工作照,生活照;單人照,多人照;集體照,風景照;普通照,光榮照;熟人照,生人照……父親用膠卷是慷慨的。
那時父母是年輕健康的,兄弟姐妹是活潑快樂的,一個大家庭融洽和諧,令人難忘……現在每每翻出相冊,看著那些定格的歷史,看著父母慈祥的笑容,心中總會升騰起一種莫名的傷感,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流。
父親對我尤為關愛。
記憶中,父親是慈祥的。他從沒打罵過我們。我是家中的幺女,從小受到父母的寵愛多些。盡管當時舉家很困難,但我和父親從來吃的都是“小灶”,這讓哥哥姐姐們很是羨慕和嫉妒。
人小鬼大。我從小就喜歡體育,剛上小學,就被選進體校。因為年齡小,爸爸負責接送。坐在爸爸自行車上的情形,現在回憶起來依然那么清晰。遇到刮風下雨爸爸總是先把我保護好,不顧自己被淋濕。有一次,雨下得很大,我們放學又很晚。父親在門洞里用雨衣把我裹起來,訓練了一個下午,我又累又餓,真想馬上回到家。可是父親遲遲沒有動作。我急了:“快回家吧,爸,我餓!”父親沉吟了一下:“雨下大了。”我說:“爸,我餓!”馬上,我聽到了自行車輪子轉動的聲音,我還聽到了雨點打著裹在我身上雨衣的噼啪聲……這樣的往事太多太多。
父親對我也很嚴厲。那時,每天早晨五點就要起床去體校訓練,我十幾歲,每每賴床不起,母親總是心疼女兒的,護著我,讓我睡到自然醒。父親卻不同,每每這時,他就繃著臉把我從被窩里拽出來,騎上自行車把我送到體校去。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現在回想起來,我性格當中剛強的一面,應該說是童年時期的那些過往經歷所賦予的。
大學畢業后我去往異鄉工作。每年回到家里,總能看到父親興奮的樣子:“嘿,我老姑娘洪英回來了,快弄好吃的來!”一向節儉的父親這時特別地大方,張羅家人做上一大桌子豐盛的佳肴,全家人聚在一起。父親專注地看著我,那眼睛失去了年輕時的睿智與明亮,那神態沒有了當年的火熱和激情。但我從父親渾濁的眼睛里依然能感覺到他對我的關懷、呵護與掛念。真是父愛如山啊!
讓我終生難忘的是2006年的夏天,假期我回到家鄉,臨走的時候父親送我出門,很遠了,父親在身后叮嚀:“洪英,常回家啊!”他渾濁而又戀戀不舍的目光盯著我。
我看著父親,昔日腰桿硬朗、面色紅潤的父親拄著拐杖,脊背微駝,稀疏灰白的頭發在光線下顯得蓬松、無奈,疲憊又慵懶……一種憂傷悄悄襲上我的心頭——父親真的蒼老了。我向父親擺擺手:“老爸,以后我會常回來看望您的!”
我淚流滿面……
誰知,這一次竟是我與父親的永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