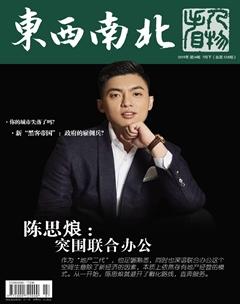Uber上市,華爾街不愛“網紅”
陳洋

美國時間5月10日上午8點半左右,Travis Kalanick現身紐約證券交易所。這一天本應是Travis Kalanick的高光時刻,只是,對他來說,過程難言完美,甚至有些難堪——作為聯合創始人,Kalanick沒能出現在敲鐘臺上。
這位曾經帶領Uber一路搏得行業領先地位的聯合創始人,當年因為面臨性騷擾、性別歧視、知識產權盜竊等一系列指控,迫于各方壓力,不得不去職Uber CEO,甚至被斥為Uber連串“文化災難”的源頭。雖然保留下董事會席位,但他的人生軌跡開始和Uber漸行漸遠。
兩年間,繼任者Dara Khosrowshahi一直試圖變革Kalanick時代“激進好斗”、“無視法律規則”、“內部不透明”的企業文化,希望讓這家聲名狼藉的創業公司盡快從負面泥沼中脫身。如今,成立十年的Uber終于站在了IPO門口。據彭博社消息,在其IPO路演的第三天,計劃發售的1.8億股股票就獲得了足額認購。
事實上,早在上市前一周多,當Kalanick在董事會上首次提出站在敲鐘臺上的要求時,Khosrowshahi就拒絕了Kalanick的要求,僅邀請其觀禮。
作為一位聲名顯赫的億萬富翁,42歲的Kalanick接下來有很多選擇。去年3月,他宣布創建了一個名為“10100 Fund”的新基金,用于營利性和非營利性的項目投資。一年后,他公布了基金在東南亞的第一筆投資,這是一個前Uber員工的創業項目。不過,在一些知情人眼中,Kalanick最大的愿望還是回到Uber,重新掌管這個他一手打造的帝國。
十年等來的艱難開局?
即便高光時刻被剝奪,這依然是Kalanick “收獲頗豐”的一天。
除掉2018年初,他以14億美元價格轉讓給軟銀的部分股票,如今他依然持有Uber公司8.6%的股份。不過,要真正完成套現,他還需要度過6個月的上市鎖定期。而在此之前,Uber的市場價格可能還會大幅波動。
事實上,不用6個月那么遠,交易第一天,股價的波動就遠遠超過了很多人的想象——作為多年來最令人期待的IPO之一,Uber在成為上市公司的前5個小時就損失了近60億美元的市值,首日收盤時股價下跌了7.6%。
《紐約時報》的報道記錄了當時交易所氣氛的驟變。“原本的嘈雜開始被緊張所取代,交易大廳顯示屏上的數字不斷下降——44美元、43美元、42美元,這是Uber最終的開盤價。聊天的聲音漸息,最后轉入一片寂靜。”42美元的價格甚至低于較早時候45美元的發行價。
在稍后的采訪中,Kalanick將這個并不理想的開局歸咎于大環境——“艱難的一周里艱難的一天。”至少這次,沒人會覺得他在全然推諉。
Uber上市前,標普大盤已連跌5日。Uber上市當天,美股三大指數低開,開盤后,跌幅收窄后再度擴大。美股科技股迎來集體下跌,以蘋果公司為例,其在上周最深累跌幅度達9%,創2019年以來最大單周跌幅,市值縮水近750億美元。而Uber最大的競爭對手之一、“網約車第一股”——Lyft,上周五收盤時也大跌7.41%。
Khosrowshahi試圖在這場“完美風暴”中為Uber爭取更多的市場信心,他引用了“華爾街教父”本杰明·格雷厄姆的名言,“從短期來看,市場是一臺投票機;但從長期來看,則是一臺稱重機。”他強調Uber會繼續專注于提升質量和規模,“行情會隨之而來。”
一些評論也嘗試從積極的角度去消解Uber開局不利帶來的不安,“Facebook在上市首日僅上漲23美分,在IPO的前15個月,股價一直低于發行價。而現在,它是全球第四大最有價值的公司。”
新故事的誕生伴隨不確定性??
對于Uber斥2億美金聘請的傳奇職業經理人Khosrowshahi來說,給市場打雞血最有效的方式肯定不是引用名言。
或許頂著壓力,代表管理層拒絕Kalanick出現在敲鐘臺,是他們眼中為了與Uber“舊形象”切割的必要之舉。那么Uber的新形象又是什么呢?顯然不是同樣受困于股價泥沼的Lyft。
在IPO前的路演中,Khosrowshahi給出了他的答案——Amazon(亞馬遜)。
在投資者眼中,Uber面臨的兩個最主要的問題是增長和盈利。在作為初創公司的頭幾年,Uber在增長上表現優異,到2018年,已經進駐了全球63個國家。但是近幾年來,其營收增速等多項核心指標均開始放緩。而另一方面,去年18 億美元的虧損,以及長期看尚難轉虧為盈的局面,更是加深了投資者的憂慮。
正是基于這兩點,對標亞馬遜成為Khosrowshahi最好的選擇。作為一家上市公司,亞馬遜也曾經歷多年的虧損。面對華爾街的壓力,亞馬遜始終堅守自己的策略,即通過大額的投入拉開和競爭者的距離,同時拓寬業務布局,發展多元化的商業模式。幸運的是,就當投資者快要耗盡耐心時,亞馬遜開始盈利了,多元化布局步入良性循環。從1997年上市開始,亞馬遜的股價已經從18美元/股上漲到如今的近2000美元/股。
Khosrowshahi希望說服投資人Uber也擁有同樣的潛力。“車對于我們來說,就像書對于亞馬遜。”不同于Lyft,Uber的業務構成更為豐富,除打車業務外,還有送餐業務Uber Eats、連接貨主和貨運公司的Uber Freight,收購Jump后又涉足共享電動自行車業務。顯然,Khosrowshahi希望通過持續的資本投入將Uber打造為一個集成多種出行服務的綜合平臺。
雖然亞馬遜創始人Jeff Bezos也是Uber的早期投資人,但是Khosrowshahi的類比在很多投資人看來,多少有些“一廂情愿”。相比經歷過經濟大蕭條考驗的亞馬遜,Uber更像是在溫室里成長起來的獨角獸;不同于亞馬遜在核心業務上的盈利能力,Uber的盈利能力依然是硬傷;相比上市時的亞馬遜,Uber的體量已經太大。很大程度上,Uber的股價也反映了華爾街對于持續虧損的科技獨角獸的態度。
而Uber面臨的不確定性還不止于此。
正如其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提交的文件中對潛在問題的描述,除了Uber原有公司文化帶來的聲譽債以及長期來看對公司發展的影響,“不滿的司機”也是Uber必須應對的問題之一。

Uber 聯合創始人、前CEO Travis Kalanic 和父親一起觀看敲鐘儀式
關于Uber司機身份的界定一直是平臺和司機的爭執焦點——Uber希望將司機們視為平臺的獨立承包商,以節省開支;而司機們則希望被視作“員工”,以享受“最低工資、加班費、保險”等其他福利。
近年來,包括美國和英國在內的多地訴訟,陸續產生了有利于Uber司機的判罰。這恰恰是被盈利所困的Uber最不愿意看到的。在此次公開披露中,Uber坦言,如果被迫開始將Uber司機劃分為“員工”,則必須“從根本上改變其商業模式”。事實上,“我們的目標是減少司機的激勵措施,以提高我們的財務業績”,“我們預計司機的不滿情緒會增加。”
自5月10日至5月14日,Kalanick的Twitter沒有更新。IPO似乎是一抹幻夢,不值得留下任何痕跡。
而Khosrowshahi則在5月11日,即Uber上市次日,轉發了2018年底上任的Uber首席法務官Tony West 的Twitter。Twitter配圖的上半部分是紐交所門口懸掛的巨大Uber牌匾,下半部分是一個雙手叉腰、昂首挺胸的小女孩雕塑,Tony West在配文中寫道,“Fearless about the future. @Uber onward!”
戰壕或許換了士兵,但戰爭永不停歇。
(王敏薦自搜狐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