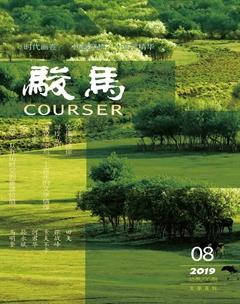個人史
何君華
第一本書
很多年后跟我的小學語文老師陳海英取得聯系,竟然是源于一則網絡求助信息。
人世間有許多相遇毫無預兆,而這一次相逢卻是如此讓人措手不及:陳老師的女兒被確診患了白血病,治療費用需要幾十萬元,對于一名曾經的鄉村教師來說,這無疑是天文數字,迫不得已,他只好上網求助。
2000年,只有二十歲的陳海英大學畢業來到湖北黃岡的蘄春縣何鋪小學教六年級語文,我從此榮幸地成了他的學生。他是我們簡陋的鄉村小學第一個有大學文憑的老師,也是第一個上課時操一口流利普通話的人。更重要的是,他有許多書,有魯迅的小說集《吶喊》和《彷徨》,曹禺的《雷雨》,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復活》,還有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當時怎么也記不住這個前蘇聯作家的名字)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甚至還有《金瓶梅詞話》。在他那里,我讀到了人生中第一批文學書。盡管這些書我多數讀不懂,內容也多已忘卻,但晚上十點在宿舍走廊昏暗的燈光下讀書的欣喜與滿足至今記憶猶新。
我感覺我的小學時光極其短暫,而我的六年級生涯卻極其漫長,甚至比整個小學時光都要漫長。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但在我的記憶中卻的確如此。我感覺跟著陳老師做了很多事情,而那些事情都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經歷的。比如,他讓我以老師的身份去給五年級的學生講課,盡管我講得一塌糊涂,還鬧出過把學生們回答正確的問題判為錯誤的笑話,但他依然熱情洋溢地鼓勵了我。他帶領我們去登山、郊游,甚至野炊,帶領我們在操場上打球,給我們展示他自己的畫作。我記得當中甚至有全裸的女體。我們為此驚駭,也從此打開眼界,看見了許多課本以外的事物。在黃岡這樣一個應試教育根深蒂固并因此揚名全國的地方,他帶領我們做一切與考試無關的事情,做一切在別人眼里“出格”的事情,并因此招致我們班主任的不滿,甚至遭到校長的批評。
時至今日,我的少時同窗黃福青仍然記得陳老師拿著我的作文在班上朗讀的情景。他說我的作文已經超過了初三的水平。如今我當然已不記得那些拙劣的作文寫了些什么,它們當然足夠稚嫩,但陳老師鼓勵了我,甚至說要把我的作文拿去發表,我為此興奮無比,每次寫作文都格外認真。
多年后我不止一次跟身邊的朋友說過,如果沒有陳老師,我很可能不會寫作。這句話當然是事實。人世間有許多行當可供選擇,我為何沒有成為一個植物學家、建筑師或是醫生、警察,偏偏成了一個作家?我想大抵是因為陳老師。
很多年里我都羞于承認自己是“作家”,因為自知寫的東西還遠遠當不起一個作家的分量。但當越來越多的人或以真心或以假意稱呼我為“作家”時,我再不以作家自稱就顯得矯情了。盡管這些年我仍然沒有寫出什么值得驕傲的作品,但我卻越來越敢于以一個作家的面目招搖過市而不感到羞愧了,除了在陳老師面前。
在陳老師面前,我仍然羞愧難當。由于自己無可救藥的懶惰和意志力的不堅定,一直沒能靜下心來寫出有足夠分量的作品,每每自感愧對陳老師的教誨。這也是這么多年來我一直不敢聯系陳老師的原因。我實在沒有勇氣拿那點小小的成績去面見他,以致這么多年我從未以任何形式主動聯系過他。
乾坤朗朗,星漢迢迢,多少人在陽光下作惡萬端而問心無愧,又有多少人在夜色里受盡苦難仍然內心澄明。多年前,陳老師為我們打開人生中的第一本書,教給我們正直和善良。多年后,當面對陌生人的善意,陳老師請他們一一留下姓名,以期來日如數奉還。
陳老師名叫陳海英,但他總是把名字寫成“陳海鷹”,大海上翱翔的鷹,那是一種本能的不屈的力量。
許多時候我們并不明白上蒼的安排用意何在,明明豁朗的天空為何偏偏被披掛上濃重的陰霾?但或許上蒼也給出了答案,因為那些被陰霾擊中的地方已經有人舉起火把,那些光亮會盡力到達盡可能遠的地方。
等信
今天微信時代的年輕人可能很難理解我們那個年代“等信”的煎熬,盡管我所說的“我們那個年代”距離今天也僅僅是十個年頭而已。
美國有一句著名的俚語叫TextPurgato? ry,意思是“等待回信的煉獄般的煎熬”。Purgatory是一個宗教詞匯,指人死后所經歷的凈化靈魂、除去罪惡的洗滌過程,也就是“煉獄”。把等信比喻成煉獄,說明等信該是怎樣一種煎熬。
我也曾經歷過這種煎熬。那是2009年的10月,我照著從學校圖書館報刊閱覽室抄來的地址,給《青春》雜志寄去了我的第一個短篇小說《花衣裳》。接下來便是漫長的煎熬——等信,等來自《青春》的信。
2007年9月,我考入內蒙古民族大學文學院,然后開始寫小說。
我天天跑去學校門口的郵政信箱看,一個星期過去了,兩個星期過去了,沒有我的信。于是我又迫不及待地給《青春》寄去我的第二個短篇小說《玩具》。然后繼續重復昨天的故事——等信,就像1957年的加西亞·馬爾克斯。
1957年,被哥倫比亞《觀察家報》派駐歐洲的年輕記者馬爾克斯一天天地跑到旅館樓下的門房問有沒有他的信,得到的回復往往只有兩個字:沒有。不久前,由于哥倫比亞國內政局動蕩,《觀察家報》被查封,租住在巴黎索邦大學附近小旅館的馬爾克斯斷了口糧,非但支付不起房租,甚至連吃飯都成了問題。饑餓難耐的馬爾克斯只好一遍遍地給友人們寫信尋求接濟,然而回復者寥寥。
盡管如此,馬爾克斯并沒有放棄生活的希望,因為還有一件事像火光一樣指引著他前行,那就是文學。彼時的他無論如何困頓,也從未停止去寫一部叫作《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的中篇小說。
《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本來寫的是他外祖父的故事,一個落魄的老上校每天去郵局看有沒有他的信和救濟金,不幸的是,這個悲傷的故事現在看起來就像是在說三十歲的馬爾克斯自己。
幸運的是,與老上校終其一生也沒能等到來信不同,馬爾克斯總算熬過來了,盡管那是很多年后的事。整整十年后,長篇小說《百年孤獨》出版,全世界都知道了這個倔強的哥倫比亞人。
我也終于迎來了我的幸運。那是一通以南京區號025開頭的電話。電話里的人告訴我,我的短篇小說《玩具》將在《青春》發表,但需要修改,并給了我十分具體的修改建議。我至今記得打電話的人的名字,她叫裴秋秋。
沒過幾天,我又接到一個南京區號025開頭的電話,我以為還是裴秋秋,但并不是(原諒我至今都不知道她的名字),她是《青春》的另一位編輯,她告訴我,我的短篇小說《花衣裳》也將在《青春》發表。
她并不知道,《青春》此前已經留用了我的一篇小說。她更加不知道,她和她的同事裴秋秋不約而同地兩次將我從絕望的煉獄中拯救了出來。
我激動地連夜按裴秋秋的建議改好了小說。第二天一早,我便帶著手機獨自走到宿舍樓下,興奮地給裴秋秋打去電話,告訴她我已經將小說改好,請她“指點”。
跟許多孤獨的寫作者一樣,我一直都是隱匿地、怯生生地躲在角落里寫小說,從來不敢在人前張揚這樣一件“不好意思”的事——我實在不敢在宿舍里當著舍友們的面撥出這通關于文學的電話。
直到彼時,我仍然不敢相信,我寫的小說當真可以發表。多少年了,我一直都是這樣隱秘地喜愛著文學啊。中學時每一個月的月底,我總是怯生生地跑去書店問新一期的《中學生閱讀》或是《中國校園文學》來了沒有。如果來了,就一定要省下當天的晚飯錢買下來,然后一個人躲起來偷偷地看,仿佛這是一件非常令人難為情的事。
及至上了大學,我開始偷偷地寫起小說來。沒有人知道我在寫作(畢業多年后,我回母校做一個文學交流活動,偶然得知當時學校圖書館電子閱覽室的管理員王妍老師竟然關注到了我的寫作,因為我總去那里將我手寫的小說稿錄成電子版,她在巡視時偶然發現了我,從此記住了我的名字。如果不是她后來調到文學院,我們得以在這次活動上重逢,我可能終身都不知道當時竟真的有人知曉我寫作的“隱秘”),現在,我的小說就要白紙黑字在雜志上發表,我感覺自己就像在夢里一樣。
我又開始等信了,天天往學校門口的郵政信箱跑,盼望著刊登我小說的《青春》雜志早日寄到。
我等到了,并且真的是兩次,《青春》2009年第12期和2010年第1期連續兩期發表了我的第一個和第二個小說。
這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議又多么令人激動的事。
余華說:“一個天天寫的人,不怕成不了作家。”從此,一個不可救藥的孤獨寫作者頭也不回地踏上了文學的“不歸路”。
看得見風景的房間
高行健說:“由種種機緣造成的這偶然,不妨稱之為命運。”我想,作為南方人的我,到內蒙古定居生活,并在這里寫作,便是我的命運。
2007年高考,因為兩分之差,我的第一志愿落榜,被調劑到坐落于內蒙古通遼市的內蒙古民族大學。彼時我尚不知通遼市的具體地理位置,在地圖上沿著呼和浩特市周邊找了許久,就在我快要放棄尋找時,無意間在另一個省會城市沈陽西北二百公里處找到了它。我實在想不到內蒙古的幅員面積竟是如此之遼闊(它甚至比我的家鄉湖北省的面積要大六倍之多),已經學過三年高中地理的我對內蒙古的誤解如此之深簡直讓人感到不可思議,但更加不可思議的事情還在后面,我竟然很快便適應并習慣了這里的生活:寒冷,沙塵肆虐,有著跟南方故鄉完全不一樣的氣候環境和飲食習慣,但我幾乎沒有感到任何不適。
更重要的是,四年大學生活之后,我竟然沒有離開通遼,而是繼續留在這片我此前從未想過要涉足的地方。盡管我從未將高考失利看作命運無情的捉弄,但我當然也并不明白造物主如此安排用意何在。我只是以我向來逆來順受的性格平和地接受了這荒唐的安排。及至后來我在這里寫下我人生中第一篇真正意義上的小說,我才終于理解了命運如此安排的因由——原來它是想讓我到內蒙來繼續完成寫作的夙愿呀。
寫作,幾乎是我從小就樹立的夢想。
人世間有千奇百怪的興趣愛好,而我偏偏鐘情于一個個小巧的方塊文字。明明是再普通不過的漢字,誰都會寫誰都會用,可是在作家筆下卻能開出花來,經過他們的生花妙筆一番排列組合,一個個毫無干系的文字就會變成一篇令人沉迷的小說故事。這簡直太不可思議了,作家簡直是這世間最神奇的魔術家。我甚至會因此羨慕我的同齡人們發表在學生雜志上的稚嫩文字,不止一次夢見自己的文字也變成鉛字發表在上面。后來我的作文當真發表了,而那本發表我“處女作”的雜志我一直保存了多年,直到它終于遺落在時間的縫隙里。
到內蒙念大學之后,我關于寫作的夢想很快就被重新激活了。因為自從我來到這里之后,我便發現自己住進了一個看得見風景的房間。透過這個房間的門窗,我看見了迥異于南方故鄉的奇異風景。從我們的學生宿舍向北望去,你會看見一座公園,這是一座再普通不過的公園,但它的名字叫西拉木倫,你根本不明白它的意思,但這絲毫不影響它所散發出的異域般的神秘氣質,迫使你不得不像嬰孩般好奇地走近它。在內蒙古,這樣類似的詞匯舉不勝舉:科爾沁、哲里木、達爾罕、額爾古納、花吐古拉、烏珠穆沁、白音胡碩……我為此找來《蒙古秘史》,找來《成吉思汗箴言》,“你的心胸有多寬廣,你的戰馬就能馳騁多遠……”捧在手心里閱讀,于是一幕幕更加瑰麗的風景便在我的眼前次第展開,我的小眼睛睜得大而圓,也因此看得更高更遠。
草原文化一如一座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文學富礦,我仿佛一下子找到了寫作的靈感,于是一篇篇“草原小說”在一個來自南方的小說學徒筆下誕生:《頭羊》《呼日勒的自行車》《希仁花》《少年與海》《禮拜二午睡時刻》……有人看了這些“草原小說”,甚至疑心我是不是一個土生土長的內蒙人,甚至問我是不是蒙古族,我只好笑而不語。我想說的是,如果你也愿意用心體悟草原上的事物,或許你也會寫出屬于你的“草原小說”來。
異域總是令人心生向往,遠方總是讓人無限著迷。博爾赫斯寫出了迷幻的中國故事《小徑分叉的花園》,卡夫卡寫出了令人震驚的《中國長城建造時》,而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的《看不見的城市》甚至可以算作一部徹頭徹尾的“草原小說”,因為它講述的正是馬可·波羅向忽必烈汗描述他在草原帝國旅行的見聞和故事。而我遠比當年的卡夫卡、博爾赫斯和卡爾維諾們要幸運得多,他們一生從未踏足中國的土地,更不用說內蒙古大草原,他們的“中國故事”、“草原小說”完全是憑空杜撰,而我好歹就居住在一個看得見風景的房間里,推開門窗便是活生生的壯麗圖景。
盡管今日的草原不得不承受環境污染、生態失衡等種種令人絕望的痛苦,但它仍然是美的,依然值得我們用手中的筆去書寫。盡管一如我借我筆下一名虛構人物、一位草原畫家那日蘇所說的,草原的美是我這支拙劣的筆所不能書寫萬分之一的,但寫下去是有意義的。起碼之于我自己,之于十幾年前那個沉迷于方塊字的小男孩來說,是有意義的。因為這便是命運,這是命中注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