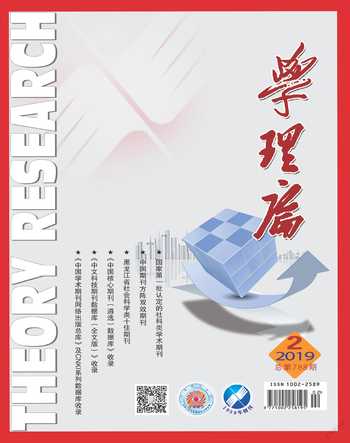論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的效力
陳姝元
摘要:《立法法》既規定我國的法律解釋權專屬于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又賦予最高人民法院進行司法解釋的權力,但沒有明確司法解釋在整個法律體系中的效力地位,使得最高法院司法解釋游離于整個法律體系之外。最高法院司法解釋的這種效力不明確引發了大量問題,不僅無法完全滿足司法實踐的需要,更是引發了法律規范適用的嚴重沖突。立法機關應規定最高法院制定司法解釋在我國立法體系中的地位,對司法解釋的效力加以明確,實現法律解釋形式的規范化。
關鍵詞: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法律效力
中圖分類號:D920.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9)02-0110-02
法律解釋是法律適用過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環,法律解釋分為立法解釋與司法解釋兩類,其中司法解釋即是國家最高司法機關在適用法律過程中對具體應用法律問題所做的解釋。司法解釋又包括審判解釋和檢察解釋兩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在性質上屬于審判解釋。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通過發布專門的司法解釋文件對法律進行解釋,在形式上與立法一樣表現為抽象的法律條文,承擔著彌補法律漏洞、填補法律空白,和使法律的原則性規定具體化的功能。
最高人民法院發布司法解釋的歷史在我國由來已久,究其本源要追溯到新中國成立伊始,法律體系尚不完善,在立法缺位的情況下最高人民法院不得不承擔起以解釋創設法律、以解釋細化法律的功能。乃至發展到今天,每一部法律出臺后,通常都會有相應的司法解釋與之配套。司法解釋具有法律效力,可以被裁判引用,在一定程度上構成我國的“法律淵源”,對構建中國社會主義法制秩序和法治建設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最高法院司法解釋的效力問題主要涉及兩個方面,其一是司法解釋在我國法律規范體系中的效力定位,其二是司法解釋與其他法律解釋發生沖突時如何確定效力位階。探索最高法院司法解釋的效力問題,有助于規范我國法律體系,促進司法機關通過審判活動推動法律的完善與法治建設。
一、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的類型與內容
1981年6月10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布了《關于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該決議規定:“凡關于法律、法令條文本身需要進一步明確界限或做補充規定的,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進行解釋或用法令加以規定。凡屬于法院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由最高人民法院進行解釋。”這是最高人民法院進行司法解釋的法律依據。
2007年4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法發[2007]12號《關于司法解釋工作的規定》開始施行,1997年7月1日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司法解釋工作的若干規定》同時廢止,進一步明確了司法解釋的性質、效力、分類和程序。該文件第6條規定:司法解釋的形式分為“解釋”“規定”“批復”和“決定”四種。對在審判工作中如何具體應用某一法律或者對某一類案件、某一類問題如何應用法律制定的司法解釋,采用“解釋”的形式。根據立法精神對審判工作中需要制定的規范、意見等司法解釋,采用“規定”的形式。對高級人民法院、解放軍軍事法院就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問題的請示制定的司法解釋,采用“批復”的形式。修改或者廢止司法解釋,采用“決定”的形式。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主要的內容大致分為五類。
第一類是直接對頒布的某部法律進行全面系統的細則性解釋,如《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二類是對某一類型的案件做出解釋,如《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第三類對某一類問題的系統解釋,如《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四類是人民法院內部有關司法程序操作的規定,如《關于人民法庭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五類是對日常工作中高級法院就具體法律適用問題的請示做出的解釋,這一類解釋占了已有司法解釋的大多數。
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的效力定位
前文已經說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的法律依據是198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由此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具有進行司法解釋的權力,但其發布的司法解釋究竟具有何種效力,是否能夠將其理解為司法解釋具有與法律同樣的效力,我國目前還沒有相關法律做出規定。
我國目前關于司法解釋效力的學說,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類型化說”,認為對司法解釋的效力可以采用類型化的方法來認定。對具體法律條文進行解釋的司法解釋,其效力等同于法律。為法院內部審判工作需要而制定的司法解釋,相當于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部門規章”。第二種是認為司法解釋效力低于法律的學說。這種學說認為司法解釋的效力低于憲法和法律,但根據上位法制定的司法解釋的效力是否低于下位法,持這種觀點學者還未就這個問題給出答案。第三種學說則認為司法解釋的效力等同于行政法規。第三種觀點與第二種觀點有一個大的前提相同,即都認為司法解釋的效力低于法律。不同的是,行政法規說將他們的結論向前推進了一步,將司法解釋的效力問題納入我國現行的立法體系當中。
在筆者看來,“類型化說”中的“對具體法律條文進行解釋的司法解釋,其效力等同于法律”這一觀點更具合理性。筆者認為,最高法院司法解釋應當與其解釋的具體法律條文具有同一效力。如果被解釋的條文屬于上位法,則解釋該條文的司法解釋就應當按照該上位法確定效力,下位法不得與該解釋相抵觸。如果新法律條文的司法解釋與舊法律條文相抵觸,應該按照新法優于舊法的規則適用。同時,筆者認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中除解釋具體法律條文這一部分之外的內容,亦即關于某一類型案件、司法程序操作、具體法律問題適用等方面的司法解釋,可以將其效力等同于“行政法規”。既明確了這類解釋的效力低于法律,又使其處于我國現行立法體系中較高的位階,能夠在實踐中得到更有效的應用。
三、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的效力位階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的效力位階問題,主要是最高法院司法解釋與立法解釋、檢察解釋、行政解釋之間的位階問題。司法解釋權是法律解釋權的一種,是法律解釋權分配于司法機關形成的權力。不同主體做出的法律解釋效力高低,與不同主體權力層級高低有關,也與解釋主體在訴訟中的地位有關。
立法解釋位階高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這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與最高人民法院的監督關系決定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監督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法律委員會和有關專門委員會經審查認為最高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檢察院做出的具體應用法律的解釋同法律規定相抵觸,而最高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檢察院不予修改或者廢止的,可以提出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檢察院廢止的議案,或者提出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做出法律解釋的議案,由委員長會議決定提請常務委員會審議。由此可見,全國人大常委會可以對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合法性進行審查,有權要求其修改或廢止,也可以以做出法律解釋的形式解決司法解釋同法律規定相抵觸的問題,這就說明了立法解釋的效力是高于司法解釋的。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與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解釋的位階應該是同級的。司法解釋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的審判解釋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做出的檢察解釋,《關于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解釋如果有原則性的分歧,報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解釋或決定。這個規定表明了審判解釋與檢察解釋之間沒有位階高低之分。當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檢察解釋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審判解釋對同一問題的規定不同時,具體適用哪種解釋目前沒有定論。筆者認為,當檢察院處理案件的時候,如果有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檢察解釋,自然應當適用。但當該案件進入審判流程時,則應當適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
行政解釋與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各自發生效力的領域不同。《關于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對行政解釋的對象做出了規定,包括法律和地方性法規,而司法解釋的對象僅限于法律,二者存在重合。審判機關、行政機關的解釋,只能對各自的下級機關有約束力,不約束其他機關。
應當注意的是,在司法實踐中經常會出現具體案件審判依據是某一司法解釋而非相對應的法律條文的情況,因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對下級法院具有普遍約束力,這實際上變相地在審判實踐中推動了司法解釋朝著“立法化”的方向發展,導致實踐中低于法律與立法解釋的應用價值反而低于低位階的司法解釋。
四、結語
長久以來,我國立法工作中對于一些具體的事項,往往都不進行規定。這種“立法宜粗不宜細”的整體原則是鄧小平確立的,我國司法實踐中逐漸演變成由最高人民法院發布司法解釋來填補具體規則層面法律的空白。從實踐經驗角度來看,司法機關由于具體承擔了適用制定法裁判案件的職能,這使得司法機關對于制定法的漏洞與不足最為敏感也最有深切體會,為司法機關通過審判活動推動法律的完善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司法機關能夠通過制定司法解釋為審判活動規定具體的操作細則。然而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效力的不明確,越來越多的問題也暴露在人民視野中。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要從源頭的效力問題人手。站在立法角度來說,立法機關應當以立法形式對最高法院制定司法解釋的效力地位及其位階做出規定,將最高法院司法解釋納入我國立法體系之中。而從最高人民法院自身的角度來說,最高法院應當對自身進行司法解釋的權力做出規范限制,應當僅就具體條文的應用進行解釋,并須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則和原意。如此,也更能契合十九大厲行法治的精神。
(責任編輯:李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