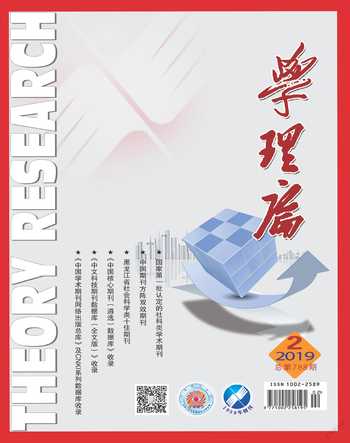人·文化·教育
李旭
摘要:歷史上關于教育起源的觀點很多,大多數觀點有一個共同的缺陷就是將教育產生的可能條件和必要條件割裂開了。文章認為,教育起源是一個發生在人類起源之后的故事。要探明教育起源問題,就要回到人類歷史發展背景中,找到教育產生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結合的歷史節點。基于此,文章緊緊依托于遠古人類歷史發展的背景,借助于人類考古學、文化人類學、解剖學、心理學等領域的研究成果,從文化的產生、文化傳承的需要、文化傳承的需要對教育的選擇等方面進行了分析,得出“教育源于文化傳承的需要”這一結論。
關鍵詞:教育起源;文化產生;文化傳承;需要
中圖分類號:G4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9)02-0143-04
關于教育起源主要有三種經典理論:一是生物起源說,認為人類的教育起源于動物界中各類動物的生存本能活動;二是心理起源說,認為教育起源于兒童對成人的無意識的模仿;三是勞動起源說,認為教育起源于勞動,起源于勞動過程中社會生產需要和人的發展需要的辯證統一。圍繞經典理論,學者們陸續提出了教育的社會需要起源說、前身起源說、晚期智人說、超生物經驗傳承與交流說、交往起源說等觀點,試圖闡明對教育最本質的認識。
無疑,以上關于教育起源的觀點為教育研究及其教育學科的發展做出了頗有意義的嘗試,提供了一定的基礎和動力。然而,筆者認為,這些觀點在一定程度上都將教育產生的可能條件和必要條件割裂開了,缺乏教育產生的充分條件。事實上,教育起源問題是人類起源問題的延續。要探討教育起源問題,必須回到人類發展歷程的廣闊視野中,尋找教育產生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歷史結合點。
一、從人類生存環境的改變到文化的產生
(一)人類生存環境的改變及其挑戰應對
在人類的進化過程中,人類祖先邁出的最為重要的一步就是從樹上來到地面。來到地面的原因,大多數學者認為主要是由于氣候條件的變化。人類學家理查德,利基認為:大約1500萬年前的非洲,從西向東覆蓋著一片森林,居住著形形色色的靈長類,包括很多種類的猴和猿。由于地殼運動,非洲東部逐漸隆起,改變了非洲的氣候和地貌。以前從西向東的一致的氣流被破壞了,隆起的高地使得東部的地面成為少雨的地區,喪失了森林生存的條件,原本連續的森林覆蓋開始斷裂成一片片樹林,形成一種片林、疏林和灌木地鑲嵌的環境。于是,“森林古猿原來棲息的森林大面積地消失,從而導致古猿的生存環境從原來的林棲過渡到林地棲,再過渡到地棲,最后則一直過渡到完全過熱帶草原生活。”同時,地球植被結構的重大變化也“使得當時主要的食物來源—植物果實變得越來越少。迫使人類祖先來到地上覓食,其中一部分逐漸適應了地面的生活而永遠的留在了地上”。
從樹上來到地面,人類祖先面臨兩類挑戰:一是需要在新的環境中獲取食物,以維持其生存;二是在失去了樹上的優勢位置后,要在新的環境中抵御猛獸的攻擊。為了應對挑戰,一方面人類祖先在新環境中需要將上肢解放出來,從事狩獵、捕魚和采集等勞動,以獲取足夠的食物。另一方面,為了抵御猛獸攻擊,除需要手握石塊或木棒以抵御猛獸外,還需要強勁的下肢獲得較快的奔跑速度,從而擺脫或獵殺猛獸。因此,在新的環境中,為了生存,人類祖先要解決的就是效益問題——用最小的消耗取得最大的收獲,實現對身體和環境的最有效利用。人類學家彼得·羅德曼(Peter Rodman)和亨利·麥克亨利(Henry Mc Henry)將人類與黑猩猩進行比較,證明了人類的兩足行走比黑猩猩的四足行走的效率要高得多,從而推論出“能量效益作為有利于兩足行走的自然選擇的力量是有道理的”。正是基于能量效益的最大化,人類祖先上肢與下肢逐漸分化,完成了從四足行走到直立行走的進化。
(二)人類腦功能的完善與意識、語言的出現
直立行走導致了人類的生理性早產。“兩足行走的工程學原理和由于直立行走所帶來的更大的地球引力導致了有限的骨盆尺寸和產道出口不允許大腦在母體子宮內繼續增大,把2/3的大腦發育空間留到產后的歷程中去發展。”另一個重要的證據來自霍普金斯大學的解剖學家艾倫·沃克,他計算出了直立人新生兒的腦量大約為275毫升,相當于當時直立成人腦量的三分之一。利基做出了進一步的推測,“如果能人的嬰兒生下來時腦子有直立人新生兒那樣大,那么他們也會需要‘過早地’出生,但不及直立人之甚。”
于是,人類祖先的新生兒帶著一顆極不成熟的大腦來到世界。相對于母體的子宮,外界環境為人類祖先的新生兒提供更為豐富的資源以刺激其各種感官。這些豐富的刺激對人類大腦有著非凡的意義。一方面,各種刺激使早期人類祖先的新生兒在腦的量的方面獲得持續的增長,使人類在漫長的進化歷程中,腦量相應得到了逐步擴大。早在約350萬年前,阿法南方古猿就采取了直立行走的方式。在最初的150萬年間,人類祖先的大腦容量維持在425-550毫升之間;當人類祖先進入200萬年前內的能人時代,其平均腦容量已達到700毫升;其后,直立人的平均腦量達到950毫升;直至距今3萬年左右的現代人(解剖意義上的)時代,腦量達到1330毫升。
另一方面,外界環境刺激定位、強化、穩固了大腦皮層和神經連接,激發了新的大腦功能區,為大腦高級機能的出現奠定了生物性基礎。對比人類與類人猿的大腦,與認知記憶有關的腦區中,人的裂腦、海馬回、間腦以及新皮層指數分別是4.43、4.87、14.76和196.41,而包含三個亞種的類人猿平均值僅為2.38、2.99、8.57和61.88。南方古猿的下前額葉(布羅卡區)已經有所發展……能人的腦尺寸增長了40%,更重要的是前語言腦區的顯現。“就投射到初級和中級聽覺皮層腦區的神經通路而言,迄今沒有發現在從猴到猿再到人的進化演變中有什么變化。但高級皮層區則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類人猿不具備對應于人類布羅卡前語言區的腦區。更重要的是,位于人類碩大下頂葉的角回(39區)和上緣區(40區),在猩猩和長臂猿中至多只是勉強可見,而在黑猩猩腦中也可能只是一個很小的區域。”與此同時,“原始人前額皮層的極大進化擴展(是以現代猩猩為模型的古代類人猿的五倍)并不均勻。與39區和40區相似,新的前額皮層腦區演化具有特殊功能的腦區,對人類的思維和記憶起主導作用”。
至此,我們得以窺見人類的大腦與其近親的大腦的差異。正是從樹上來到了地面,迫使人類祖先從四足行走進化為直立行走,才引起了這種差異的出現—一人類祖先獨特的行走方式導致生理性早產,提升了人類大腦的質量水平。這是人類意識和語言乃至其他高級心理機能得以出現的基礎。人類在從猿向人進化的過程中,并沒有浪費這一寶貴財富。在人類祖先適應環境的實踐中,大腦的意識和語言以及其他各種高級機能得以出現并逐漸完善,為文化的產生提供重要的基礎條件。
(三)人類文化的產生
意識和語言為文化的產生提供必要條件,二者從出現之初就緊密結合在一起。“意識是人對客觀事物的認識活動,包括外在事物或情境的認識活動,也包括對自己的內在活動的認識活動,并包括對自己的認識活動的認識活動,即對意識的意識……意識包括感覺、知覺、思維這三種認識活動,因此也就是這三種認識活動所構成,但以思維為主。”與此同時,“語言是用聲音表達思想的符號系統,符號是用以表示者和被表示者的結合”。“人類意識不僅作為語言的表達內容,而且作為一種內在的驅動力,驅使人類對意識外化的形式進行選擇,并使其按人類意識要求的方向演化。”同時,“外化手段的選擇與不斷外化的意識有一個互相推進的過程,在二者相互作用的歷史長河中,人類意識有一種不斷增長和發展的趨勢,于是要求表達形式和表達手段與此相適應,從而實現相互推進”。語言作為人類意識的外化手段,推動了人類意識進一步發展,使得人類抽象思維得以產生,進而擴展了人類的認識視野。“有了語言,人們就能夠使自己的認識不僅馳騁于無限的現實世界,而且奔騰于神奇的幻想境地;不僅可以追憶久遠的過去,而且能夠展望引人入勝的未來。”
自然中大多數生命體只能感知到環境的存在,并根據環境的改變不斷調整自身。即使在靈長類動物中,也僅僅只有高級意識的萌芽。與此有著重大區別的是,人類能將感覺、知覺、思維三種認識活動綜合在一起,形成特屬于人類的自我意識。“自我意識就是一個人對自己以及自己和他人關系的意識。”“這意味著一個個體知道他自己知道,當然最初這是一個主觀的或自省性的判斷標準。”人類祖先在生產生活實踐中,憑借自我意識與語言,逐步意識到自我與非我、主體與客體的區別與聯系,并將環境(自然和他人)與自我作為審視對象,從而產生了與環境的關系、與他人的關系和與自我的關系。這構成了人類文化最基本的三個層面。在生產生活實踐中,與自然的關系從最初對自然的適應走向對自然的改造,使自然體現出一種合目的性的趨勢。借助這種目的性的改造,人類創造了物質文化。與他人的關系體現為人類共同生產生活所必需的群體規則,表現為人類的制度文化。與自我的關系體現為對人類核心價值和基本理念的認識評價和價值判斷,構成了人類文化體系最深層的內核。
人類祖先創造了文化,同時文化又反哺其自身。在漫長的進化過程中,人類逐步從自然的人走向文化的人。“文化的本質是‘人化’和‘化人’……‘人化’是按人的方式改變、改造世界,使任何事物都帶上人文的性質;‘化人’是反過來,再用這些改造世界的成果來培養人、裝備人、提高人,使人的發展更全面、更自由。”至此,人類開啟了一條文化獨舞之路,人科動物與猿科動物分道揚鑣,步入文化進化的旅程。
二、人類生存發展的需要驅動了文化的傳承
(一)人類生存發展的需要與文化進化
人類創造出文化之后,就以兩種相互聯系的方式繼續向前進化:一種是生物進化,另一種是文化進化。生物進化主要表現在腦的進化方面,為人類文化的進化提供必要的物質基礎;同時,文化進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和形塑著人腦。事實上,現代人類(解剖意義上,下同)的文化使得人的生物本能逐漸趨弱,人類生物進化的空間已越來越小。根據間斷平衡理論,只有當一個局部小群體棲息于其祖輩生活區的邊緣地帶而且與其祖輩隔絕的情況下,新的物種才能產生。這樣的局部小群體被稱為邊緣隔離種群(peripheral isolates)。如果各種隔離機制(isolating mecha-nisms)能夠阻止新基因型在未來遭遇其祖輩時其基因流回歸到起始狀態的話,一個邊緣隔離種群才會演變成一個新物種。然而,從人類出現第一個工具文化起,人口就獲得了持續的增長。人口的增長使得發生在人類身上的任何基因中的變異都受到了極大的稀釋,以致這些變異無法保存下去;同時,人與人之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不大可能為生物進化提供必要的邊緣隔離機制。而且,到了人類社會較晚期,出于倫理考慮,決定某個人能否獲得生存的權力已不取決于自然選擇,而是取決于當時社會的理念和所擁有的醫療條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現代人類的生物進化已經接近巔峰。
文化進化則不一樣,它突破了人類的生物局限性,其走向取決于人類的創造力。于是,在今天的人類身上出現了奇怪的現象:人類身體的外部特征在進化的過程中,好像越來越不符合自然選擇的法則,呈現出整體趨弱的情形(如我們今天的感官能力、四肢的運動能力等與人類祖先相比,整體趨弱)。我們不禁驚詫于人類以如此孱弱的身體特征如何得以躋身于萬物之靈的頂端——秘密就在于人類大腦物質基礎所帶來的文化進化。人類的生物進化似乎是把所有的優勢能量都集中在了大腦機能的完善上,在其身體外部特征總體趨弱的同時,不斷鞏固和完善大腦的機能,為人類文化的進化提供源源不斷的支持,創造出非凡的文化成就。
在此,我們要再次感謝原始人類在進化過程中所創造的人腦,它所蘊含的潛力是人類取之不竭的寶貴財富。在人類大腦的基因型的生物進化過程中,經歷了從具有語言潛能的人腦、經具有利他行為傾向的人腦、向具有所有文化特性功能傾向的人腦進化的過程;借助于腦的基礎,在自我意識的參與下,與此相應出現了人類獨有的文化進化:從學習特定人類語言、經學習利他語言、到學習文化的過程。這顆無與倫比的大腦,奠定了人類文化進化的基礎,伴隨人類勇敢地適應各種環境。
(二)文化進化與文化傳承
生物進化信息通過遺傳機制傳遞,人類的文化進化則主要是借助文化傳承得以實現。文化習得和文化分享是文化傳承互為聯系的兩個方面,同時也是文化的重要特征。一種觀念只有在既是習得的又是分享的條件下才能成為文化。沒有習得和分享,就不可能有人類整體觀念的出現,也就不可能有文化的產生。在人類早期,當人群中某些人首先掌握了較為粗陋的經驗(文化的雛形)時,由于共同生產、生活的原因,使另一些人有了通過模仿而習得他人經驗的機會。這種模仿最初是無意識發生的。隨著經驗的習得所帶來的巨大好處,并且人們越來越意識到了這種好處,經驗的分享逐漸就演變為一種有意識的行為。當經驗的習得和分享的范圍逐漸擴大,越來越為早期人類社會所認同時,這種經驗就轉化為了文化。于是,在經驗分享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文化共享。稍后,伴隨著人類自我意識和語言的持續發展,使得文化分享在代際間得以進行,就構成了文化傳承。
文化傳承實現了文化的累積性和持續性的過程,對維持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具有非凡的意義。一方面,通過文化傳承,將上一輩的文化經驗有所選擇地傳承給年輕一輩,維系了一個同質的社會,進一步鞏固了人類共同體;另一方面,年輕一輩既對上一輩的文化觀念有所選擇,又積極參與到具體的文化創造過程中,保持一種異質的張力,為文化創新注入活力。正是在文化的同與異之間,人類文化不斷向前發展,為人類社會的持續進步提供創造力之源,促進人類社會的革新。
至此,我們初步觸摸到了人類進化為萬物之靈的些許秘密。與生物進化相比,文化進化的速度要快得多:生物特征的適應性變化可能需要成百年的時間,而文化特質的普及可能僅需要幾年。正是由于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需要,驅動了文化傳承。通過文化傳承,人類持續實現著文化進化,在與其他物種的競爭中處于有利地位,在同質和創造之間平衡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
三、文化傳承的需要選擇了教育
早期人類社會生活是渾然一體的,缺少功能的分化。生產寓于生活,生活包含于生產。最初的文化傳承就是在生產生活實踐中進行的。一種活動既發揮政治、經濟的功能,也發揮著文化傳承及其他功能。隱匿于生產生活實踐中的言傳身教就成了最初文化傳承的形式。這種隱匿的言傳身教的文化傳承并不為人們所意識到,具有極大的偶發性和隨意性。
然而,隨著人類文化經驗的積累,文化傳承在維持人類生存和發展中的作用日益凸顯,并且人類也越來越認識到其重要性。于是,文化傳承不僅成為早期人類的客觀需要,也成為人類的主觀需求。這就要求有意識的言傳身教代替隱匿的言傳身教。借此我們可以設想出這樣一幅畫面:人類在狩獵、捕魚、采集、工具制作、群體集會與交流等活動中,經常帶上自己的后代,有意識地向他們展示(也有比較粗淺的講解)從事這些活動所應具備的技術,達到了傳承文化經驗的目的。這是教育真正的發源地,人類教育正是起源于這一歷史的節點。為了保證文化傳承的效益,教育借助有意識的言傳身教使文化傳承從社會生活中彰顯出來。這注定教育從產生之初就與文化傳承、培養人緊密聯系在一起,并將此二者內化于自身的本質功能中。《說文》有曰:“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養子使作善。”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教”最初是發生在代際之間的,文化經驗從上一代向下一代傳承;“育”是培養下一代的活動,善作為活動的價值取向,體現了活動的目的性。因此,教育在產生之初,就是在人的主體意識的參與下,將上一代的文化經驗有所選擇地傳承給下一代,實現了文化經驗的再生產,維系整個人類社會的生存和發展。
教育注定是為文化傳承而生的,文化傳承的需要將人類置入了一種特殊的社會活動——教育——之中。自有了這種特殊活動,人類更好地完成了文化選擇的過程,并形成了專職文化傳承的重要機制,推動了人類進化,幫助人類更好地適應和改造環境。
回顧前文,關于教育起源的各種學說與觀點——生物起源說、心理起源說、勞動起源說、社會生活需要起源說等,都沒有揭示出文化在整個人類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意義。人類文化中既凝聚了大腦的各種機能,同時在其產生過程中又必然包含了人類的生產生活實踐。教育的起源既不在人類生物本能和心理意識的端點,也不在早期人類渾然一體的社會生活。這些因素僅僅是為教育的出現提供了可能條件或必要條件。教育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活動,毫無疑問,其最初得以產生是由于它所具有能滿足人類需要的某種本質功能——這是早期人類首先要考慮的。作為與本文觀點最為接近的社會生活需要起源說,我們認為這一提法稍嫌寬泛。因為人類社會生活的需要有很多方面,將它們放人社會生活的整體中作為教育的起源,沒能凸顯出教育最為本質(原初)的含義。文化傳承需要是社會生活需要的一種,正如政治的需要催生了國家等政治實體、經濟的需要催生了各種經濟實體一樣,文化傳承的需要催生了教育及其實體。在人類歷史上,文化傳承的需要是距離教育產生的最近的臨界點,而社會生活的需要還處于這個臨界點之前——作為一種必要的前提條件存在。
文化傳承凝聚了人類的生理、心理等物質條件,同時也包含在勞動、社會生活之中。正是文化傳承凝聚了教育產生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條件、從客觀需要走向主觀需求,使教育成為現實。如果說教育自產生之日起就是握在人類手中的一柄火炬的話,那凝聚各種條件的文化傳承的需要則是點燃火炬的按鈕——需要一經產生,按鈕隨即按下。教育之火炬一旦點燃,將照亮人類在歷史與現實的旅程中堅定前行。
四、結語
在漫長的人類發展歷史中,人類祖先從樹上來到地上,選擇了直立行走,導致了生理性早產。生理性早產使得人類2/3的大腦需在母體外發育完善,大大提升了人類大腦的品質水平,為新的大腦功能區的出現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基礎。借助這一基礎,人類形成了特有的語言、意識、文化,踏上一條文化獨舞之路——通過文化不斷適應著整個世界。從自在的經驗分享、到自為的文化共享、再到文化傳承,人類教育將文化傳承從社會生活中凸顯出來,更好地維持著人類的生存和發展。不論時代如何改變,文化傳承都將是教育最為本質的規定和功能,也將是一定社會人才培養的出發點。文化傳承凝聚了整個人類的希望和未來;教育作為這種希望和未來的最大承擔者、最為忠實的踐行者,任重而道遠。
(責任編輯:李鵬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