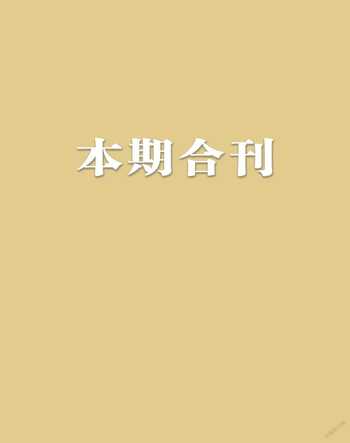不散不見
周云龍
人生三桌飯,出生時擺一桌,結婚時擺一桌,去世時擺一桌。第一桌,你不會吃;第二桌,你沒空吃;第三桌,別人在吃。
大姨哥的愛人,在與病魔抗爭十多年后,在她70歲生日前幾天走了。
親友們都有心理準備,所以少了一點“化悲痛為力量”的感傷,告別儀式輕輕松松,全然沒有生離死別的悲悲戚戚。
骨灰安放結束,親友們直奔飯店。在這里,見到多年未遇的姨姐,姨姐夫,也見到他們在上海創業有成的兒子。好多年前,和他見過一面,而現在,我們彼此都沒有印象。換個場合,在飯桌上碰面、碰杯,也一定不會認識,更難知曉我們血脈相連。
在這個以追思為主題的喪宴上,平生第一次見到小姨哥,小姨嫂。如果不是因為大姨嫂的去世,我們或許難得有機會碰面,我甚至都不記得還有這樣一個姨哥,從小在上海生活,學習,說一口上海“噯哦”。仔細回想,小時候媽媽在抽屜里精心收藏的一張照片上,好像見過他一眼,胖胖的,帥帥的。——其實,沒有那張照片的印象打底,只要看看姨哥姨姐們的外貌,就知道什么叫“如出一轍”,他們是姨媽一個模子“刻”出來的。
后來問姨姐的兒子,他和我表哥的兒子,兩人平輩,同在一個縣城,他們竟然也是第一次見面。年輕時,都在忙學業,后來都忙事業,各奔東西,難有交集。
人生的遇見,如此不可捉摸。一棵親情大樹上的枝葉,有時不曾失散,卻可能勝似失散。大姨嫂的去世,讓大家從大江南北趕來,在這個冬日坐到一起,而我們打撈出來的記憶碎片,卻是一組不對稱的親情信息。因為血緣的聯系,我們一見如故,彼此又都覺得相見恨晚。——有一種親密,叫“不見不散”;有一種親情,叫“不散不見”。
有意思的是,和我來往最為密切的大姨哥,他常常轉幾路公交車跑到我的辦公樓下,而他前天在給我電話報喪時,居然一時卡殼,忘記了我的姓,通訊錄里怎么也找不到,平時都是隨口喊喊“云龍”“云龍”,姓什么呢?他愣在那里,想了一個多小時。
鄉村過去有種說法,一代親,兩代表,三代就拉倒。意思是,即使是至親,隨著代際關系鏈的不斷加長,人與人的交往也會日漸疏遠,直到形如陌路,譬如,我和那些姨侄,姨侄孫。在這個飛速變化的時代,人和人的疏遠可能也處于加速度,各有備的忙。——不過,家族里一位長者的離世,卻可以在一兩天之內將我們迅速拉到起點,拉回原點。
可是,之后呢?之后往往就沒有了“之后”。而在此之前呢?真的期待那種“活久見”嗎?移動互聯時代,“失散多年”,好像不再有借口。
網上有人調侃,人生三桌飯,出生時擺一桌,結婚時擺一桌,去世時擺一桌。第一桌,你不會吃:第二桌,你沒空吃:第三桌,別人在吃。——人生三桌飯,和“我”不相干?其實,在別人的三桌飯里,我們也都可能是座上賓。當然,不只在“吃”,不只在碰杯,還有心靈的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