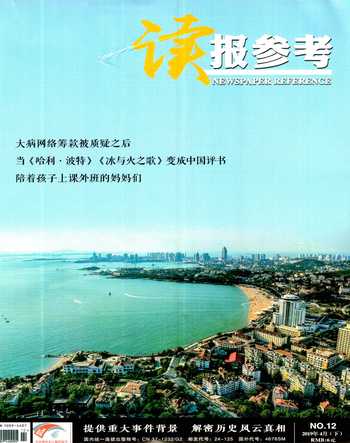明星在老爸面前談戀愛
今年第一季度,《我家那閨女》《女兒們的戀愛》《女兒們的男朋友》《妻子的浪漫旅行》等同類型綜藝節目集中播出,并在收視成績、話題度上都有不錯的表現。這標志著新的節目類型——觀察類綜藝走紅。
這些熱播的觀察類綜藝都聚焦代際溝通、戀愛困境、婚姻焦慮等社會話題,也成為繼戶外競技類真人秀、慢綜藝、親子綜藝后,集中爆發的新綜藝類型。節目走紅的背后,究竟挑動哪些公眾情緒?又面臨怎樣的問題?
“離有個女婿又遠了一步”
演播室的屏幕上,播放著演員袁姍姍的生活片段。嘗試煎雞蛋,收拾房間,去超市采購,為朋友們的到來準備食材。與此同時,袁姍姍的父親坐在演播室,指著屏幕上正在做家務的女兒,調侃道:“她煮餃子就不會,我那天聽她跟她媽媽打電話,問怎么煮”“她拿菜刀就拿不好”“她第一次煎雞蛋”。
這是在播綜藝《我家那閨女》的片段。節目中,四位明星的父親坐在演播室觀察女兒的生活狀態。這種形式之所以被稱為觀察類綜藝,是因為節目分為演播室和戶外兩個空間,由觀察者和被觀察者組成。
在電視評論人楊智帆看來,中國綜藝一大特征是“扎堆”。“每個階段都會有比較流行的節目出現,有一個試水成功的案例出來之后,市場就會認可,平臺,商業客戶會追著這個模式連續做,至少做個兩年以上。”
觀察類綜藝試水成功的案例,要追溯到去年夏天湖南衛視的《我家那小子》。楊智帆認為,《我家那小子》是國內最早把演播室和戶外的關系處理得最清楚的一檔節目。當時,嘉賓朱雨辰母親的教育觀念,一度霸占微博熱搜。去年秋季騰訊視頻《心動的信號》熱播,再次向市場證明了這種類型的可復制性。
事實上,“演播室觀察”的元素,早在《我們相愛吧》《女人有話說》等節目中就出現過。這些節目大多邀請情感專家或心理學家,對明星或素人(日語音譯,通常指非專業人士)的行為和心理進行點評。但楊智帆覺得,他們并沒有把“觀察”設計成節目的“模式點”。楊智帆認為,觀察類綜藝最重要的是觀察者和被觀察者之間的關系。“演播室選擇的嘉賓,跟戶外部分的嘉賓,他們的人物關系是不是成立,或者說演播室本身有沒有一套邏輯,這一點很關鍵。”
《女兒們的戀愛》《我家那閨女》《妻子的浪漫旅行》等觀察類節目,都選用了藝人的親人作為觀察者。《女兒們的戀愛》制片人兼總導演晏吉告訴記者,進行節目設計時,主創一直在思考究竟以怎樣的視角切入戀愛題材。經過推演,他們覺得年輕人戀愛時,父母一定是最關心的人,因此讓藝人的父親坐在演播室里觀看女兒與異性約會的視頻。“對于父母來說,他們是有欲望和權力,還有責任去關心和介入。在節目中,我們增加這個視角,讓父母來監督把關,甚至來作為權威認證。”
于是,我們看到這樣的畫面:在《女兒們的戀愛》中,沈夢辰為男友杜海濤的父母準備豐盛的午餐時,沈夢辰的父親在演播室一臉認真地說:“不管你會做(飯)還是不會做,不要太刻意了。但是老人家來了,你還是應該主動一點兒。”彈幕上出現“和我爸說的一樣”的字樣。
楊智帆認可這樣的觀察模式。他認為,親情關系的加入,能夠在演播室形成更加有效的信息延伸。“父母評價自己子女的時候,他們所放出來的任何一個信息點都是真實有趣的。從節目的頂層邏輯和任務關系的設計來說,是合理的。”
艾瑞咨詢研究經理徐燕妮告訴記者,觀察類綜藝帶來的最大改變是,讓素人與節目有機地結合,使綜藝更加生活化。“戶外競技類、慢綜藝,觀眾經常質疑綜藝劇本的痕跡過重,看著不夠自然。情感觀察類綜藝比較大的改變是引進素人參加綜藝的錄制。素人的表現看起來更加自然,也容易讓觀眾產生情感上的共鳴,因為他們的舉動、方式,和平常生活比較相似。”
這就能夠解釋,為什么參與錄制的素人父親,反倒頻頻登上熱搜。《我家那閨女》第一期播出后,袁姍姍的父親問她,會因為自己在節目上拆臺她不會干家務而生氣嗎?袁姍姍回應道:“不生氣啊,但離你有個女婿又遠了一步。”
觀察的終極目的是人
那么,如何在節目中觸發代際之間的矛盾和溝通?幾檔觀察類綜藝幾乎都從觀念分歧最為尖銳的婚戀問題下手。《女兒們的戀愛》《女兒們的男朋友》直接安排父親觀察女兒談戀愛,《我家那閨女》則把話題聚焦在“婚戀焦慮”上。有人統計,《我家那閨女》前三期,四位女嘉賓共被催婚了二十三次。
而《女兒們的戀愛》選擇的四位女嘉賓,對于感情的態度也具有代表性。任家萱是成熟女性的代表,經歷過生活和情感的波折,對愛情既想靠近又有不安;任容萱的情感困惑與曾經的感情經歷和父親的態度有關;沈夢辰與杜海濤相戀多年,但一直承受外界的壓力;傅園慧代表感情經歷空白,不知道如何與異性接觸的女性群體。
于是,想戀愛,卻不會戀愛;不愿結婚,反遭逼婚;對生活迷茫,卻無法和父母溝通……種種社會性話題,赤裸裸地沖擊公眾的情緒,讓節目在輿論聲中迅速走紅。在楊智帆看來,這恰恰說明,綜藝節目正在承載社會意義——過去,人們對于綜藝的認知停留在娛樂層面。“好的節目要有時代背景,甚至有記錄時代的功能和意義。不能脫離時代,作一些純烏托邦的東西。好的節目要跟當下發生關系,要有點大事記的意思。”
“觀點都是平等的,沒有對錯,只是分享出來,讓社會形成討論點。對于節目來說,有沖突和矛盾才可以引起適當的社會話題,形成所謂的討論熱度。”徐燕妮點評道。
但是,綜觀市場上火爆的觀察類綜藝,呈現出同質化的特征:幾乎均以婚戀為切入口。楊智帆覺得,觀察類節目里,婚戀話題完全可以由一位嘉賓來完成,其他的嘉賓則應該完成其他層面,比如職業屬性的內容。“像《我家那閨女》,節目展示的閨女們的生活狀態和職業身份應當是多個維度的。最開始出現的何雯娜,是退役的奧運冠軍,面臨著運動員的職業再轉型,她應該走職業標簽的路線和成長線。不同的嘉賓承擔的功能不一樣,豐富性會更好。”
徐燕妮也認為,觀察類節目無需局限于情感關系。“還可以觀察特定的職業人群,或者說特定的年齡段,因為生活觀察類的主題是很寬泛的。”徐燕妮提到騰訊視頻近期推出的網絡綜藝節目《我和我的經紀人》。節目以明星和經紀人的關系為觀察對象,以職場為核心,滿足了觀眾對娛樂圈運營規則和明星人設打造的獵奇心理。據貓眼專業版統計,該節目目前累計播放量超過4100萬次。
放眼日韓,觀察類綜藝的類型五花八門。韓國JTBC的節目《網線生活》,記錄美妝博主、吃播博主等網紅在鏡頭之外的生活;日本東京電視臺的《可以跟著去你家嗎》,隨機跟隨素人去家中進行拍攝;日本TBS的綜藝《人類觀察》則在當事人不知情的情況下,與他的身邊人合謀,暗中記錄人們在特殊情況下的反應,比如在沙灘上,當妻子離開時,有美女搭訕讓幫忙涂防曬霜,你會怎么做?
楊智帆則聯想到紀錄片《我的時代和我》。該作品的第一期全程跟拍易烊千璽的工作行程,從商業活動到舞蹈排練、拍攝廣告等。節目最后,當時尚未成年的易烊千璽坐在酒店的床上,拿著毛巾擦著下巴,一臉疲憊。當他暢想著能和朋友出來玩時,眼睛突然發亮,嘶啞的聲音說:“一個星期就行。”
楊智帆覺得,這樣的觀察與記錄才是觀察類節目的終極目的,因為它成功地觀察到生活中的人,“讓大家知道標簽之下的這個人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
“但是很遺憾,現在好多節目好像都沒有太往這個角度去切。”楊智帆說。
(摘自《看天下》王一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