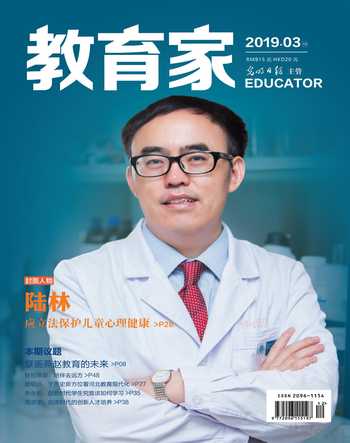陸林:應立法保護兒童心理健康
王湘蓉 呂虹


【記者手記】
初春時節,天氣仍是寒涼,伴著午后斜陽,我們如約來到了北京大學第六醫院五樓的會議室,一身醫者白衣的陸林教授已經在此等候。作為教育記者,采訪醫生并不多,正是因為這一襲白衣,如清風一縷,讓人莫名心安,跨界采訪的拘束感瞬間蕩然無存。初見陸林教授,以為他會給人世事練達的持重感,不曾想舉手投足之間,竟是朝氣勃發的書生氣度,讓人不覺莞爾。采訪中,他用極“科普”的大白話回答我們所提問題。并就我國兒童青少年的教育問題直抒己見,亦是深入淺出,對兒童青少年精神心理疾病進行了理性分析。記者的筆尖記錄著時代,也見證著時代的發展,那些推動時代前進的磅礴力量,應該流淌在記錄時代的文字中,凝練成時代的符號。對陸林教授的采訪,也是一次記錄,如果用最直觀的語言來表達的話,那便是——醫者之心,懸壺濟世,樸素而溫暖。
世界衛生組織(WHO)在2014年的《世界青少年健康報告》指出:2012年全球有大約130萬青少年死亡,15~19歲為高風險階段;自殺是全球青少年死亡的第三大死因;在10~19歲青少年中,抑郁癥是致殘和致病的主要原因。
2016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上強調,要加大心理健康問題基礎性研究,做好心理健康知識和心理疾病科普工作。這無疑為中國的心理健康行業打了一針強心劑。
據統計,我國由精神疾病導致的疾病負擔占非傳染性疾病總負擔的13%,給社會和家庭帶來了沉重負擔。而從全球范圍來看,精神疾病的負擔僅次于心血管疾病和癌癥,為第三大疾病負擔源。《中國青年發展報告》顯示,我國17歲以下兒童青少年中,約3000萬人受到各種情緒障礙和行為問題的困擾。相關數據同時表明,我國10%~15%的兒童存在焦慮抑郁、行為障礙等心理衛生問題,留守兒童群體內甚至高達30%。
有效阻擊青少年精神心理疾病,需要病患群體、醫院和整個國家的重視和參與,加強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對于個人成長、國家人才培養、社會的和諧發展,都具有時代意義。日前,針對我國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我們專訪了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第六醫院院長陸林教授。
精神疾病的發病機制非常復雜
《教育家》:陸院長,我們了解到,您主要從事精神心理疾病的臨床診療技術和發病機制研究。那么,我國現階段兒童青少年心理衛生面臨的挑戰都有哪些呢?您作為“中國腦計劃”中研究腦與精神疾病專家組的成員,您認為精神疾病研究在腦計劃中的地位與預期如何?
陸林:從精神疾病的發生情況來看,我國兒童孤獨癥發病率近幾年增加明顯;在青少年中,由于學習壓力導致的睡眠障礙與抑郁癥的確診率也逐年升高。要說挑戰呢,有這樣幾個方面。一是國家層面的立法。盡管有兒童保護相關的法律法規,但對兒童心理健康方面的立法還有所欠缺。二是社會支持系統的建立。當前,學校、家庭往往更看重學習成績,對兒童心理健康重視不足,這導致孩子成長壓力過大,容易讓孩子出現焦慮的情緒。目前比較普遍的不適切的隔代撫養、學業應試壓力等,都是心理健康問題加劇的因素。此外,社會對心理衛生疾病的認知水平普遍不足,重視程度不夠。理念層面的制約最為嚴重,比如早期,家長、老師對心理問題并不了解,這在留守兒童群體方面尤甚。三是專業人才隊伍的培養。目前,我國兒童心理健康相關醫務人員數量不足,全國兒童精神科醫生不足500人,父母尋求專業幫助的渠道有限。
常見精神心理疾病患病率的增加,一方面和社會發展太快,競爭壓力增加有關;另一方面也和公眾對心理疾病的認識提高,使這類疾病更易被發現有關。
30年前,一個人如果愁眉苦臉、郁郁寡歡,周圍人往往以為他在鬧情緒,而現在大家慢慢認識到,他可能是抑郁了,會給他多些包容。精神疾病的發病機制非常復雜,遠遠超過癌癥、心腦血管疾病等。人類的器官中,最復雜的就是大腦,對大腦的結構和功能,我們還知之甚少。精神疾病的復雜性、病因機制的不明確性,提示我們需要從國家政策、專業領域等層面,重視精神醫學。在“中國腦計劃”項目中,抑郁癥、自閉癥和老年癡呆成為最受關注的三個領域。希望通過“中國腦計劃”建立抑郁癥、自閉癥、老年癡呆的隊列研究,對腦部疾病的診療方法和干預措施開展進一步探索。
《教育家》: 現在社會、學校、家庭對于兒童身體健康的保障相對完善,而早期精神衛生篩查是相對薄弱的。您作為國內研究精神心理健康問題的權威專家,在您看來,如何判斷孩子出現了心理問題呢?
陸林:有一些比較簡單的方法,家長和教師如果有這方面的意識,就可以學習和觀察。一是縱向觀察孩子的日常生活習慣,包括飲食、睡眠、學習等。如果孩子以前一切正常,近期突然出現食欲下降、失眠、做噩夢、學習注意力不集中、成績下降等現象,這些都可能是抑郁等精神心理問題的早期表現,需要我們家長和老師引起重視。二是橫向比較同齡孩子的行為,包括日常學習方式、學習進度、社交態度、體育運動狀況等。如果他們行為明顯不符合常態,和其他孩子明顯不同,做事懶散,社交退縮或疑心很大,都需要引起重視,尋求相關專家幫助。
應將心理輔導機制納入學校常規教育體系
《教育家》:有資料顯示,青少年期是精神心理疾患早期癥狀出現的高發期,而在兒童青少年階段進行診治,比成人階段更為有效。例如抑郁癥的早期篩查,請問,目前國內青少年的抑郁癥發病率怎樣?在病癥早期,如何進行干預?
陸林:精神疾病對青少年及年輕人,尤其是15~30歲這個年齡段帶來的負擔尤其明顯。這一年齡群體正是社會未來建設的生力軍,精神疾病對患者本人及整個社會的影響都很大。具體到抑郁癥,其發病機制目前尚不完全清楚。我們知道,首先研究發病機制要立足大量準確的數據樣本,目前,我國抑郁癥患病率約為5%左右,然而18歲以下青少年精神疾病的患病率,目前沒有全國范圍內的調查結果。這就需要由國家層面牽頭進行頂層設計。
的確,很多成人精神心理問題起始于在兒童青少年階段,如能早期發現早期干預將會獲得較好效果,即早發現、早治療、早恢復。但實際情況是,社會、學校、家長常常忽視或不懂得識別,病人往往發展為慢性,變得難于診治。數據顯示,目前我國抑郁癥患者的就診率不到30%,也就是說不到三成的患者會主動尋找醫生幫助,農村地區的抑郁癥就診率更低,甚至低于10%。
目前,心理咨詢和心理治療資格國家標準尚未出臺,兒童青少年屬于多動癥、抑郁癥、精神分裂癥等疾病的易感人群,我們可以借鑒西方國家的心理治療師制度,將心理輔導機制納入校園常規教育體系。抑郁癥表現多樣,需要精神科醫生、內科醫生、心理咨詢師等不同領域的專業人員共同參與,形成協作模式,做好患者轉介,提高診療效率。比如有些孩子處于疾病前期,并不想去醫院問診,學校、社會的心理咨詢機構就可以提供時間相對充足的心理疏導服務,做好疾病前的早期干預;若情況嚴重,就轉給醫療機構,等情況好轉,需要心理疏導時,醫療機構再轉介給咨詢機構。這種模式實際更有可操作性,對患者也更有幫助。當然,這也需要政府制定良好的患者轉介機制。
《教育家》:抑郁癥患病率約為5%,成了一種常見病,但目前中國社會對抑郁癥還存在比較多的誤解,怎樣看待這種情況?
陸林:青少年是抑郁癥的易感人群,青少年正處于人生的極大變動期間,屬于精神敏感人群。在成年人群中,抑郁癥女性比男性患病率高。這里面包含多種因素,如女性在生育、工作之外往往還要承擔較多的家庭責任,產后抑郁等也是常見情況。還有一類易感人群是老年人,比如“退休”帶來的生活失落感導致的抑郁情緒等。
在綜合醫院就醫的病人中,抑郁癥的平均識別率只有20%~30%。這除了醫院各科室醫生對精神心理的知識訓練不夠外,還有老百姓存在病恥感的原因。其實抑郁癥跟很多其他病一樣,與人的道德、品格、人格沒有直接關系。但是,很多人即便已認識到自己可能是抑郁癥,也不愿意告訴別人,也不愿意找醫生。所以,很多病人識別不出來。實際上,很多首次發病的抑郁癥患者如果得到完善的治療就不會復發。但如果治療不徹底會增加復發風險。
《教育家》:您曾研究發現了快速抗抑郁的新靶點,我們也了解到許多抑郁癥患者對于用藥有許多顧慮。請問,抑郁癥的治療一定要用藥嗎?目前上市的抗抑郁藥安全性如何?
陸林:很早以前研發出的抑郁癥治療藥物雖然療效尚佳,但是不良反應較多,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隨著精神學科領域的研究不斷發展,目前的藥物在保證療效的前提下,減少了不良反應,患者的日常生活并未受到太多影響。同時,一些新的治療方法也正在研究中,不久的將來相關的技術臨床轉化可幫助病人更好地減輕痛苦。
關于用藥的問題,中度以上抑郁癥的治療建議進行藥物治療,如果門診藥物治療效果不好,可能還需住院。當然,藥能幫助病人解決一些問題,但不能僅僅靠藥物。如果只是輕度抑郁,一般建議病人通過適當的體育鍛煉、健康的生活方式、充足的睡眠、良好的支持,或在心理治療師的幫助下克服抑郁癥狀。
對于抑郁癥的治療,除藥物治療外,病人還可以進行物理治療和心理治療。這也是全世界通行的做法。我們一般建議:第一次藥物治療,最少要服藥6~12個月,不能吃幾天就停了;如果復發,第二次服藥至少需要堅持2~3年;如果第三次復發,我們建議終身服藥。
對于抑郁癥來說,一定是早發現、早治療效果會比較好。具體病到了什么程度,是不是需要藥物治療,什么時候停藥,要由醫生來判斷。目前市場上常見的抗抑郁藥也有十幾種,一般都是安全的,除了安定類藥物之外,也很少出現藥物依賴性。
應將挫折教育和心理疏導設計成課程
《教育家》:您覺得目前兒童青少年精神問題的干預治療過程中,如何形成適切的家校共育?
陸林:剛才說了抑郁癥,再說自閉癥,這類疾病往往是先天與后天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有很大一部分來自遺傳。比如“老夫少妻”這類模式的婚姻家庭出現自閉癥、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的兒童比例就高于正常同齡段夫妻的家庭。但遺傳之外,后天的作用也很明顯。有些孩子一直潛伏著這類基因,但他終生不會外顯成疾病,這也與后天成長的環境和人的性格緊密相關。
家校共育就是家庭、學校、老師給予孩子多方面的支持體系,這在干預治療中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和諧的家庭關系和家庭氛圍,能給青少年帶來更多的安全感。家庭關系差,或父母的關系長期不和諧,或單親家庭,孩子發生心理問題的機率會增加。父母的教育方式與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緊密相關,家長應避免給青少年過多的壓力和關注,應注重了解孩子的內心想法,多表揚孩子,讓孩子感受來自現實生活的成就感。
學校應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要把心理健康教育潤物無聲地納入各項教育活動,要鼓勵青少年積極參與文體活動和社會實踐活動。除了學習之外,同伴之間的溝通和交流,對青少年的成長是非常有幫助的。有些青少年的精神疾患因為沒有得到及時的心理疏導,導致自傷、自殺的悲劇發生,所以學校的課程體系需要調整,應將挫折教育和心理疏導作為常規的教育項目,設計成學校的課程。希望學校能夠努力營造有利于學生成長的良好氛圍,做好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務。比如通過個別或團體的咨詢、電話咨詢、網絡咨詢,還有豐富多彩的班級活動,促進孩子心理健康的發育,減少不良行為和心理問題的發生。
對青少年自身而言,要正確認識網絡,正確認識和評價自己,把注意力放在學習上,加強體育鍛煉,培養自己興趣;要適當鍛煉,規律生活,建議每周要有一定的鍛煉時間。除了特殊情況外,盡量不熬夜。
避免出現“網癮少年”,最好的治療就是預防
《教育家》:近年來,對于網絡成癮是否是一種疾病,社會爭議較大。2018年6月,世衛組織宣布將游戲成癮列入《國際疾病分類》,“網癮少年”再次引發社會關注。我國有沒有網絡成癮的相關診療標準?您對此有什么預防與治療建議?對于一些藥物成癮疾病的致病成因,是否與抑郁等情緒也存在共病性等關聯?
陸林:目前,我國還尚未發布針對網絡成癮的診療規范,但正在制定當中。網絡成癮是比較復雜的綜合性問題,要經過較長時間的討論和認識,才能形成診療規范。在這里需要強調的是,許多網絡成癮的孩子會伴隨其他精神心理問題,比如網絡成癮者中約有五分之一的人罹患注意缺陷多動障礙,抑郁障礙或焦慮障礙也遠高于一般人群,同時也易伴生與父母關系問題、學業問題等。
除了網絡游戲本身的成癮,還有很大一部分孩子是對網絡上的不良內容成癮,例如沉迷于網上的日本成人動漫、成人直播等,延續到生活中就時不時出現很多類似的模仿行為。
遇到這類比較嚴重的問題時,家長就應該去專業醫療機構,尋求專業人員的幫助,比如說咨詢心理治療師、專科醫生,絕對不能諱疾忌醫。我接觸很多病例里,很多父母長期不承認這個現實,時間拖得越長,問題會越嚴重。
最好的治療就是預防,我的建議就是加快相關法規的制定,依法依規管理青少年的網絡行為,通過證件、面孔識別等人工智能手段,限制青少年(包括成人)的在線游戲時長。
對于網癮,目前還沒有成熟的藥物治療方案,主要還是靠心理疏導。但是近年來,抱有“病急亂投醫”心態的父母把孩子送到“戒癮醫院”和“戒癮學校”接受“專業”的治療。曾經,電擊療法治療網絡成癮一度受到許多家長的追捧,然而,這種無臨床研究和循證醫學依據的治療手段,給孩子的身心健康帶來巨大傷害,包括極大的恐怖和應激創傷。所以對于網癮的治療我強調一定要去專業科學的心理機構和醫院,借助科學的治療手段對其進行干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