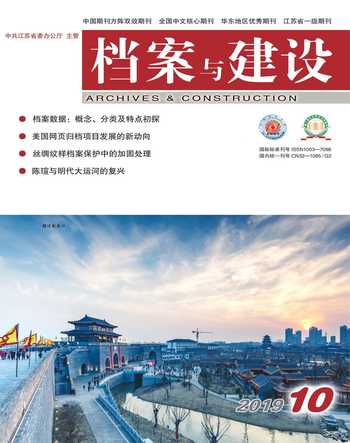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村史文化場館的價值取向
董長春

摘要:2017年6月起,常州村史檔案文化研究課題組對江蘇省內外村鎮文化場館建設情況展開了實地調研。自2005年《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文化建設的意見》下發以來,鄉村(社區)歷史文化場館在探索中發展,急需明確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導向。文章基于調研結果,立足于鄉村振興戰略背景,梳理了中國鄉村公共文化場館的歷史演變,著力探索了村史文化場館在鄉村文化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存在的全新價值和意義,以期為基層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發展和鄉村文化建設提供決策參考。
關鍵詞:鄉村振興;村史館;檔案文化;價值
黨的十九大作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大決策部署,《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指出:繁榮興盛農村文化,煥發鄉風文明新氣象,要“傳承發展提升農村優秀傳統文化,切實保護好優秀農耕文化遺產,推動優秀農耕文化遺產合理適度利用。”“劃定鄉村建設的歷史文化保護線,保護好文物古跡、傳統村落、民族村寨、傳統建筑、農業遺跡、灌溉工程遺產。”新時期,加強農村文化建設已經成為鄉村振興戰略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以常州為例,2009年常州市內首個村史館(五一村村史館)建成,近十年來,已建成的村(社區)史館不足10個,加上已建的村史室(長廊)和在建(已有規劃)的村史館也不到20個,普及率相對較低,發展速度較慢。在鄉村振興的戰略背景下,有必要首先梳理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歷史變遷,明晰鄉村文化的內涵要素,確立村史文化場館的地位、價值取向,使村史文化建設的發展思路與其所承載的歷史責任相適應,與鄉村振興的核心價值導向相統一。
一、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嬗變
古代中國是一個充滿鄉土情誼的社會,古代中國的農村大多是同姓聚群而居形成的家族式村落。鄉村公共文化空間是一種村民群體共同營造和擁有的空間,承載著鄉村集體記憶與公共倫理,使家族、禮儀、鄉土生活方式得以存在,使鄉愁和根的眷念得以存續,具有文化的內涵、價值和意義,對強化村民的文化認同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舊社會鄉村公共文化空間——以“祠堂”為典型代表
傳統鄉村公共文化空間根據功能的不同,可以劃分為三類:一是具有精神寄予內涵的祠堂、寺廟等;二是具有娛樂活動性質的戲臺(樓)、禮堂、會堂等;三是具有宣傳教育性質的學堂、書院、講堂等。
“祠堂”最早出現于漢代,當時均建于墓所,日墓祠;南宋朱熹《家禮》立祠堂之制,從此稱家廟為祠堂。當時修建祠堂有等級之限,民間不得立祠。至1536年,明代嘉靖皇帝允許民間“聯宗立廟”。從此,宗祠成為家族最重要的象征,成為以宗族或家族式村落為單元,族內或村內居民開展公共文化事務,見證鄉村歷史、維系精神存在的重要場所。祠堂有五大功能:祭祖敬宗、內外交往、道德審判、文化休閑、歷史教育。隨著時代的發展,祠堂的政治和教化功能基本退化,舉辦紅白喜事、節日慶典等活動的文化娛樂功能逐漸成為其主要功能。
(二)近現代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從“通俗教育館”到“民眾教育館”
北洋政府時期籌建“通俗教育館”以推行社會教育,是一個集圖書館、博物館、體育場、音樂廳等各種社會功能,采取閱讀報刊、看戲、辦壁報、講演等方式對民眾進行啟蒙教育的公共文化機構。1915年8月,江蘇省立通俗教育館正式創建。此后,全國各地陸續出現了通俗教育館或與之類似的機構。1929年,中華民國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國,將“通俗教育館”改為“民眾教育館”。民眾教育館被定性為民眾教育服務的綜合性社會教育中心機構。多設館于原有的祠堂、城隍廟等,向公眾免費開放,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政府對基層(農村)社會的管理“缺位”。
1949年后,人民政府接手了當地的民眾教育館,改造成為農工俱樂部或人民文化館,從事群眾文化藝術建設工作。20世紀80年代,《關于活躍農村文化生活的幾點意見》《關于加強群眾文化工作的幾點意見》《關于進一步鞏固和發展農村集鎮文化中心的報告》相繼出臺。此后,鄉鎮文化建設在全國范圍迅速開展。
(三)新時期農村公共文化空間——從“鄉鎮綜合文化站”到“基層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
2005年開始,中辦、國辦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文化建設的意見》《“十一五”全國鄉鎮綜合文化站建設規劃》,明確了鄉鎮綜合文化站屬于公共文化服務基礎設施建設范圍。“十一五”“十二五”期間,《鄉鎮綜合文化站管理辦法》《鄉鎮綜合文化站建設標準》(建標160-2012)出臺。2015年10月,國辦印發《關于推進基層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建設的指導意見》,提出“到2020年,全國范圍的鄉鎮(街道)和村(社區)普遍建成集宣傳文化、黨員教育、科學普及、普法教育、體育健身等功能于一體,資源充足、設備齊全、服務規范、保障有力、群眾滿意度高的基層綜合性公共文化設施和場所”。
從“鄉鎮文化站”到“基層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鄉村文化建設的層級由鄉鎮(街道)進一步下放到行政村(社區),體現了鄉村振興戰略下鄉村,公共文化服務的落地生根,打通了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最后一公里”。
二、鄉村文化的內涵分析
鄉村文化是指在一定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下,村民主體在生產、生活實踐中所形成的認識態度、道德觀念、制度規范、專用器具等有機綜合體。鄉村文化分為三個層次:一是物質層,指村民的生產生活中所需要的或相關的物質要素;二是制度(行為)層,指各歷史時期農村的各項政策制度及其增補改進情況,這些制度對村民具有強制的約束力或有效的規范性;三是精神(思想)層,指主體具有的思想意識、精神情感、道德準則、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等。一般說來,鄉村民俗館、陳列室、博物館等側重于物質要素(文物古跡、遺跡遺產、生產生活用具等)的保管,鄉村檔案室、書刊閱覽室、農家書屋等側重于制度行為要素(文件檔案、鄉規民約、族譜家訓等)的存儲,而村史室館、鄉村記憶館則更側重于對精神要素(思想觀念、人文精神、核心價值等)的提煉。三類場館在信息的組織精度和加工程度上依次遞增。鄉村振興戰略中所倡導建立的基層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是三個層次要素的整體體現、是多種空間場所的物理集聚。(如圖1所示)
目前的鄉村文化建設過多地關注物質要素及其依附場所的硬件投入,而對精神要素的挖掘不足,對村史場館地位和作用認知不深。精神層是村史文化的核心和靈魂,而制度文化是精神文化的基礎和載體,以鄉村文書檔案為主體的制度文化與鄉村精神文化相互包容滲透。
(一)鄉村歷史是鄉村文化的根
文化是歷史的傳承、積累和擴展,讓人們理解過去,設計未來。文化精神深藏在歷史記憶中,尊重歷史才能把握文化。任何文化的產生和發展都無法從根本上割斷與固有歷史之間的精神紐帶。鄉村文化的發展無一不依托于鄉村歷史,追根溯源方能喚起傳統文化精神。村史是鄉村文化的根,決定了鄉村文化生命力的興衰,決定了結出何種文化之果。
(二)檔案是鄉村歷史文化的觸點
農村檔案是農民、村民自治組織、村辦企業等主體在經濟建設、自治管理、農技發展中形成的,反映中國農村歷史變遷的原始的歷史記錄,是村史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它不僅在農村社會管理中發揮著重要的憑證和參考價值,在鄉村文化中,它更具有獨一無二的“歷史記憶”和“文化休閑”價值。如果說歷史是文化之根,那么檔案就是根與土壤的觸點。鑒于檔案與歷史的親緣關系,離開檔案談歷史,就如同撇開歷史談文化,乃無稽之談。鄉村檔案相對系統地體現了鄉村歷史發展的軌跡,展現了鄉村歷史文化原汁原味的“真實”內涵。
(三)鄉村文化振興有賴于鄉村記憶的喚醒
鄉村記憶激發了文化情愫和鄉村情懷,匯聚了鄉規民約、族譜家訓等道德資源,儲存了遺址遺跡、宗族祠堂、田野文物等歷史見證,傳承了鄉村文脈,讓廣大村民在精神上有歸屬感。檔案能夠喚起對故土家園的眷戀和追憶,喚醒對祖輩及自我的深刻認知。以檔案資源為依托構建鄉村記憶,建設村史檔案文化場館,能夠穩固鄉村文化的根基,激發鄉村振興的價值動機,促進鄉村文化自信的恢復,推動鄉村振興精神支柱的樹立。
三、村史檔案文化場館的價值取向
鄉村公共文化空間應集中體現鄉村文化內涵要素,拓展為以檔案資源為依托、充分融入檔案元素的村史檔案文化場館。其目標是喚醒鄉村記憶,增強村民的共同體意識,強化群體的同質感和連帶感,強化鄉村內聚力,形成良好的鄉村振興新秩序。
(一)主體:注重村民本位
村史檔案著力回答了“我(們)是誰”“我(們)從哪里來”等歷史根源性問題,了解村史、研究村史是村民樸素的“自我意識”表現。村史檔案文化場館應順應村史文化發展的“自我本位規律”,使村民真切感受“自我與鄉村”的聯系,產生對本土文化的認同及自信,繼而踐行自我文化管理。
1.滿足村民自身的記憶需求
鄉村歷史記憶的構建和發展具有四個主要特征:“自書寫”(農民自身及其祖輩創造村史)、“自關注”(關注自我、祖輩及熟人相關的檔案史料)、“自傳承”(村史記憶依賴于農民自身的代代傳承)、“自媒體”(借助自媒體進行村史文化的宣傳擴散)。因此,村史文化要植入村民的真情實感,關注貼近“鄉土”的,看得見、摸得著的身邊人、身邊事;保存的鄉村記憶和農耕文化遺產應該是順應自然和土地的,是為了生存和生活的,是此時此地人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的投影。
2.激發主體的能動性
村史檔案文化場館建設中,政府部門是指揮者、鄉村干部是推動者、村民是使用者、專家學者是服務者、建設單位是整合者,應明晰備主體的角色、地位、職責,充分發揮各自優勢。其中,村民是創造鄉村歷史和譜寫鄉村未來的主角,是場館直接的使用者和受惠者,是評判村史文化建設成效的直接標尺。因此,應充分調動村民參與、發展、創新、評價村史文化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培育農民的公共精神與責任意識,最終提升文化的自信心與歸屬感。
3.遵循主客共享理念
鄉村公共文化空間,除了充分考慮本地居民的歷史記憶、教育傳承需求,還應滿足外來旅游者的文化休閑、專家學者的科研創作需求,即“主客共享”。應充分實現集約高效利用和整體功能提升,使同一建筑融合多種功能,“一堂(館)多用”,使之全時性使用,如在祠堂中增加村史館、村民議事堂的功能,在村史館中增加文藝創作與交流區、閱讀休閑區、文化體驗區,增強實踐性、互動性、趣味性、體驗性。
(二)客體:尊重鄉村“微觀歷史”
村史檔案文化場館的客體是鄉村歷史文化遺產(記憶),個體鄉村的微歷史豐滿著國家鄉村記憶,完善了社會大歷史。主體通過微觀歷史事實,建立超越歷史真實性的文化認知。
1.凸顯原始檔案
從存在形態來看,鄉村記憶大體可以分為四類:器物遺跡記憶、文獻記載記憶、口頭傳承記憶、體化實踐記憶。調研發現,了解村史之人逐漸離世,許多遺跡遺存正在消失,原始文獻遭遇損毀,村史記憶不得不以加工過的藝術作品或編輯過的文字材料予以留存,其歷史代人感、沉浸感大打折扣。檔案作為鄉村歷史的原始記錄,是鄉村社會發展的第一手文獻,其憑證價值為其他文獻資料無法比擬,更能給人帶來畫面感、震撼感,使人零距離觸摸歷史、走進歷史、穿越歷史。以充足的原生史實作為構建鄉村記憶的基礎,可以避免再造村落歷史、再造文化傳統的鬧劇。但多數鄉村有檔可查的歷史不過數十年,且長期以來農村檔案的文化價值被忽視。2013年,住建部、文化部、財政部等部門發布《關于做好中國傳統村落保護發展工作的通知》,與中國傳統村落保護與發展研究中心幾乎同時開始了傳統村落立檔調查。2016年,由馮驥才主編的《20個古村落的家底——中國傳統村落檔案優選》出版,以照片的形式展示了傳統村落物質的、非物質的文化遺產。這種用檔案管理方法對農耕文化遺產實施保護的做法,從側面印證了檔案在構建鄉村記憶中的獨特地位,為農耕文化遺產“建檔立案”對留住“鄉愁”具有重要意義。
2.藏品的大眾化
村史檔案文化場館所留存的“農耕文化遺產”中的“遺產”概念應該是廣義的,其價值內涵不再局限于“歷史、藝術、科學”價值,呈現出“記憶、休閑”價值的擴充和延伸。村史文化場館的藏品聚焦于普通農民的農業生產和鄉村生活,反映大眾的、草根的鄉土記憶,滿足民眾日常文化休閑需求,如傳統城市博物館不會收藏的生產生活用具:鋤頭、犁鏵、鐵鍋、鐵鍬,或者因物理尺寸限制無法收藏的物品:水車、脫谷機等。
3.歷史敘事的通俗性
鑒于村民的文化教育層次相對較低,同時考慮到場館的道德教育和文化休閑功能,載體上更傾向于采用圖示、照片、聲像等,追求直觀感、畫面感、故事感。簡說歷史、圖說歷史、場景還原歷史,在不違背歷史真實性的前提下,用通俗的、流行的語言敘述歷史,用故事串聯歷史,綜合運用現代化展示手法,用村民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去還原歷史。
(三)相對價值性
1.與其他鄉村文化場所的協同性、共生性
當覆蓋全社會的文化服務體系發展到鄉鎮、村層級時,其相應的對接平臺已經不再是各自分離的圖書館(室)、檔案館(室)、史志單位等,而是傾向于整合性、一體化的鄉鎮文化站、基層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不須刻意追求備專業學科理論、理念、技術和方法在實踐中的獨立性、分割性,鄉村各文化場館之間也并非競爭性和替代性的關系,而是互補互促、協同共生的關系。村史檔案文化場館應與政府辦公場所保持相對獨立性,與其他公共文化場所保持空間集聚性,呈現百態齊聚的文化斗艷態勢。
2.與其他鄉村的差異化、特色性
中國鄉村歷史發展的主線一致,但每個村落的發展脈絡絕無雷同,應避免陷入“千村一面”的誤區。要尊重各村莊獨特的歷史和個性,挖掘出蘊藏于本土的人、事、物。主要體現三方面的特色:一是原生史料特色。善于“在顯微鏡下看脈絡”,講好鄉村故事、展現鄉村靈魂和內核。尤其傳統古村落、歷史文化名村是農耕文明和鄉愁的主要承載,更應遵循“一村一魂”“一村一展”的特色化發展原則。二是本土建筑特色。由最了解本地的人設計,用本地材料、本地技藝打造真正屬于本村的公共文化空間。三是傳播媒介特色。倡導“本土特色”傳播形式,如原住民“用方言講出來”,用當地特有的藝術形式“唱出來、演出來、畫出來”。
“十三五”期間,村級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如雨后春筍般快速發展。只有明晰村史與文化、村史與檔案之關系,把握村史檔案文化場館的核心價值取向,才能把握傳承優秀農耕文化遺產的正確方向,才能正確指導村級綜合性公共文化中心建設實踐。將檔案元素充分融入村史文化,將村史作為鄉村基礎文化教育的必修課,將村史研究作為文化基礎工程項目之一,將村史檔案文化場館建成鄉村精神文化“糧倉”,能夠穩固鄉村文化建設的內核和根基,為鄉村振興提供內生動力和精神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