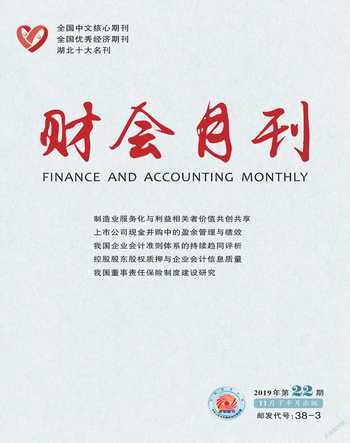空間異質性、城市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
汪朝陽



【摘要】基于環境規制的視角,采用我國220個城市2011~2016年面板數據,利用門檻回歸方法考察不同環境規制強度下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結果表明: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但這種正向影響具有環境規制三重門檻效應;在較低的環境規制強度下,金融發展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有限,只有當環境規制強度超過特定水平時,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正向促進作用才能達到最大,然而這種效果并不會持續,過于嚴厲的環境規制反而會弱化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我國整體上還未達到環境規制的最優,短期內通過進一步加強環境規制,能釋放出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正向效果,從長期來看,不能忽視環境規制的“適度性”問題;在環境規制下,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表現出顯著的空間異質性,東、中、西部城市分別表現為正向U型、正向W型和正向倒N型的非線性規律。這些結論為在不同空間區域實施差異化、動態化環境規制政策,進而為有效地利用金融發展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提供了理論依據。
【關鍵詞】金融發展;環境規制;產業結構升級;門檻效應
【中圖分類號】F83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0994(2019)22-0134-8
【基金項目】湖北省技術創新專項(軟科學研究類)“湖北省低碳技術創新環境評價研究”(項目編號:2018ADC143)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在經濟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根據國際國幣基金組織(IMF)發布的統計資料,2017年國內生產總值排世界前三位的國家分別為美國、中國和日本,GDP分別為194854億美元、120146億美元和48732億美元。同時,2018年6月英國石油公司發布的《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8》顯示,2017年美國消耗的一次能源總量為2234.9百萬噸石油當量(Mtoe),占世界能源消耗總量的16.5%;中國為3132.2Mtoe、日本為56.4Mtoe,占世界能源消耗總量的比重分別為23.2%和3.4%。2017年,從單位GDP的能源消耗來看,中國分別是美國的2.27倍、日本的2.78倍,高能耗往往伴隨著高污染。由此可見,我國經濟高速增長建立在粗放低效的、以環境和能源為代價的生產模式之上。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和社會各界也充分認識到這種模式的不可持續性,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預示著政府將會實施更加嚴厲的環境規制。在更加嚴厲的環境規制下,探求經濟增長和環境保護的平衡點,促進增長模式從粗放型的規模增長向集約型的效率增長轉變必將是學術界討論的熱點問題。
產業結構升級不僅是實現集約式效率增長的有效工具,也是協調經濟可持續發展與環境保護的根本途徑[1]。金融發展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在產業結構升級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針對其作用機理國內外學者做了大量研究。本文認為,環境規制是影響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因素,在更加嚴厲的環境規制背景下,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正向作用是否能夠持續?如果能夠持續,其正向作用是在增強還是削弱?同時,在區域層面是否存在空間異質性?針對上述問題進行探究,無疑對“新常態”下城市環境保護、金融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等方面工作的推進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一、文獻綜述
在不同環境規制強度下,有關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升級的研究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展開。
(一)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升級的相關研究
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單向關系研究中,Gold? smith[2]驗證了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錢水土等[3]運用兩步GMM系統估計方法檢驗了金融發展、技術進步與產業升級三者之間的關系,發現金融發展對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都具有正向的促進作用。也有學者研究認為,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存在非線性關系,易信等[4]運用跨國面板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發現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轉型的正向影響隨著產業發展階段的變化呈倒U型變化。邵漢華等[5]認為金融結構市場化對產業結構的升級效應會隨著經濟發展水平、技術進步水平與市場化水平的變化而變化,在高、低區制之間進行平滑轉換。還有一些學者則認為金融規模、金融結構與金融效率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存在差異性,如史恩義等[6]利用中西部17個省市動態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發現:金融發展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西部地區的吸收能力,在金融規模和金融結構的共同作用下,中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對地區產業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明顯。王春麗等[7]的研究表明,在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過程中,金融發展總量的增長具有明顯的推動效果,金融效率的提高卻沒有表現出積極的促進作用。
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升級互動關系研究中,鄧光亞等[8]實證研究發現,中部地區產業結構調整與金融發展存在著長期的均衡關系,但是兩者之間并未實現互動發展。王立國等[9]研究發現,金融發展規模擴大、結構合理化對產業結構升級具有積極促進作用;產業結構升級并沒有對金融發展產生引致需求,即互動關系并未形成。徐衛華等[10]運用耦合模型和耦合協調模型研究發現,金融深化、科技創新與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均未形成內生互動發展機制,但是金融深化、科技創新耦合系統與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形成了內生互動發展機制。
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高級化和合理化影響研究中,王定祥等[11]發現1952 ~ 2010年間,我國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的促進作用具有明顯的長期性和時滯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發展促進了產業結構高級化,但抑制了產業結構合理化。羅榮華等[12]發現金融發展規模會降低產業結構合理化程度,而金融發展效率的提高和證券市場的發展有利于提高產業結構合理化程度。同時,金融發展規模會提高產業結構高級化程度,而金融發展效率的提高和證券市場的發展卻會降低產業結構高級化化程度。
(二)環境規制與產業結構升級的相關研究
環境規制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遵循成本假說”,環境規制會增加企業的成本負擔,使企業的采購、生產、管理和銷售等環節的操作難度加大,不利于產業發展和產業績效提升。二是“波特假說”,環境規制通過壁壘效應、轉移效應、創新補償效應和替代效應促進產業結構升級[13]。
在環境規制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非線性關系研究方面,孫坤鑫等[14]研究發現,環境規制對產業結構合理化和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均呈現U型曲線效果。阮陸寧等[15]研究發現,環境規制強度和產業結構升級呈U型關系,當環境規制強度較小時,會抑制產業升級,當環境規制強度越過門檻值且不斷增大時,產業結構水平持續上升。胡建輝[16]基于環境規制分類視角進行研究,發現行政化環境規制對產業結構升級表現出顯著正向促進作用,市場化環境規制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顯著且存在基于行政化環境規制的“雙門檻效應”。
在環境規制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機制(或機理)研究方面,梅國平等[17]研究發現,環境規制通過進入壁壘、技術創新、國際貿易等方式影響產業結構變遷機制,由此提出了環境規制促進產業結構變遷的外延式和內涵式發展路徑。肖興志等[18]研究發現,我國總體環境規制強度對產業升級的方向和路徑產生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中西部地區環境規制強度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并不顯著,東部地區環境規制強度的提高能夠顯著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李娜等[19]研究發現,開放初期,擴大開放與環境規制對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作用不顯著;長期持續的擴大開放和環境規制對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調整作用顯著,且開放程度越高,環境規制的調節作用越明顯。程中華等[21]研究發現,環境規制顯著促進了城市產業結構升級,但這種促進效應受城市經濟發展階段的限制。鄭加梅[22]認為,環境規制對產業結構的調整作用不僅體現在企業優勝劣汰、建立隱形綠色壁壘以及發揮清潔型產業的規模效應方面,而且體現在通過引導對外貿易升級對產業結構調整發揮積極的間接效應方面。時樂樂等[22]發現,高強度環境規制對技術創新具有倒逼作用,有助于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環境規制依賴于產業技術創新水平的高低而對產業結構升級產生不同的影響。
綜上所述,國內外學者對環境規制、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進行了大量研究,但多集中在環境規制與產業結構升級或者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升級兩兩之間的關系上,鮮有學者研究在環境規制約束下,金融發展是如何影響產業結構升級的。因此,本文將環境規制納入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關聯性研究,具體來講就是把環境規制強度作為門檻變量,運用門檻面板模型研究在不同環境規制強度下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并分地區進行空間異質性分析,探究在環境規制約束下,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從而更加科學合理地反映彼此之間的關系。
二、內在機理及研究設計
(一)內在機理
合理的環境規制能夠通過對融資成本、信息傳遞和產業集聚產生影響,促進或刺激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從而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具體而言,在合理環境規制政策背景下,金融的融資功能將會為達到環保標準的企業或項目提供低成本的融資,激勵企業進行技術改造,企業亦傾向于采用低碳綠色的生產技術。然而未達到環保標準的企業將進入金融系統“黑名單”,通過信息傳遞效應,股票價格下跌,市場價值明顯下降,倒逼企業進行有效的環境管理。同時金融的產業集聚效應會吸引人才向金融集聚地匯集,填補人才空缺,資金也會流向低污染的高新技術產業,從而促進產業結構升級[23,24]。
這種影響力是隨著環境規制強度的增強而不斷提升,還是存在適度性的問題,是否存在一個最優區間呢?其可能的解釋是:當環境規制強度較低時,融資約束、信息傳遞和產業集聚三大效應會發揮一定程度的作用,導致環境規制對企業技術創新的積極影響較為有限,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亦不會太強。較高的環境規制強度下,金融系統會規定更加嚴格的融資準入門檻,“三大效應”會進一步發揮影響作用,使得符合環保標準的新企業更容易建立,以激勵新建企業采用低碳技術和清潔生產工藝;同時會倒逼未達標的已有企業進行治污技術創新和生產技術創新,部分轉型不成功的企業,由于無法適應這一快速變化而退出市場,從而促進產業結構升級。過高的環境規制強度會導致金融機構融資的環保標準進一步提高,“三大效應”的作用會有所弱化,甚至會有“好”的企業由于無法適應這種新變化,轉型不成功,被“錯殺”退出市場,環境規制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也會因此減弱,從而出現一些潛在的創業者因過高的企業建立成本和營運成本望而卻步,不愿建立新企業。
(二)模型設定
本文計量模型選用Hansen[25]提出的面板門檻模型來分析在不同環境規制強度下,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Hansen給出的基本方程為:
給定任意γ,可以估計出式(1)中的各變量系數,同時可以求出此時γ所對應的殘差平方和RSS。不同的γ將得到多個殘差平方和RSS,然后對RSS進行排序,最小RSS對應的γ值就是門檻值。在找出門檻值的情況下,要針對門檻效應進行兩方面的檢驗:一方面要看是否存在門檻效應,如果存在可以確定門檻估計值;另一方面要看估計值與真實值是否相等,Hansen分別構建F統計量和似然比統計量LR進行了上述兩方面的檢驗,本文不再贅述。
根據研究需要本文引入經濟發展水平、固定資產投資強度、政府調控強度和人力資本以及城市發展的信息化水平作為控制變量,模型(1)可以改寫成:
式(3)中CV表示各個控制變量,α表示各控制變量對應的系數,考慮模型可能會有多個門檻,我們可以對模型(3)進行拓展,本文不再詳述[26-28]。(三)變量說明及數據來源
1.被解釋變量:產業結構升級(INS)。國內比較有代表性的衡量產業結構的方法有:周昌林等[29]采用的產業結構水平指標、徐德云[30]采用的產業結構升級指標、干春暉等[31]基于泰爾指數的產業結構合理化指標,以及黃亮雄等[32]從三個維度提出的產業結構變動幅度指數、高級化生產率指數、高級化復雜度指數和相似度指數。本文采用第三產業與第二產業增加值之比表示產業結構升級指數。
2.解釋變量:金融發展水平(FIN)。對金融發展水平的度量現有文獻中常見的做法是從三個角度進行度量:金融規模、金融結構和金融效率。鑒于數據可得性,本文選取金融規模來衡量各城市金融發展水平,具體用金融機構年末貸款余額與該城市的地方GDP之比來衡量。
3.門檻變量:環境規制(ER)。張成、陸旸等[33]將國內外環境規制的衡量指標歸納為六種,這里不再詳述。基于數據可得性的考慮,我們選取SO2去除率來表示環境規制,SO2去除率越高說明環境規制強度越大。
4.控制變量。為了提高模型的準確性,本文加入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基礎設施建設水平、政府干預力度、人力資本情況以及城市信息化水平等指標作為控制變量。經濟發展水平(PGDP)用地區人均GDP衡量,以2011年為基期進行平減,單位為萬元;基礎設施建設水平(ROAD)用市轄區年末實有城市道路面積衡量,單位為萬平方米;政府調控強度(GOV)用政府財政支出占地區GDP的比重衡量;人力資本(HR)用每萬人在校大學生人數衡量,單位為人;信息化水平(INTERNET)用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數衡量,單位為萬戶。
5.數據來源。本文數據均來自2012 ~ 2017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
三、實證分析
(一)基于全國層面的分析
在構建門檻面板回歸模型之前,先估計一個線性的普通面板回歸模型,使用Hausman檢驗判定是選取固定效應模型還是隨機效應模型。Hausman檢驗中卡方統計量為20.95,伴隨概率為0.0003,表明固定效應模型優于隨機效應模型,因此采用固定效應模型檢驗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同時為了消除異方差影響采用穩健型標準誤檢驗,結果見表1。
由穩健型標準誤的固定效應面板模型估計結果可知,金融發展水平的系數為0.1376,并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了檢驗,說明金融發展顯著促進了產業結構升級。金融發展通過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的作用渠道改變資金存量和資金流量,通過資金形成、資金導向、信用催化、風險防范和補償機制等促進產業結構的改善和產業素質與效率的提高,進而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34]。
本文采用Hansen門檻面板模型,設置搜索樣本最小值為50個,采用bootstrap方法進行400次重復。表2給出了通過全國層面不含控制變量和含控制變量的門檻效應檢驗后得到的F值和P值。由表2可知,在不考慮控制變量的情況下,把環境規制作為門檻變量,金融發展作為解釋變量,產業升級作為被解釋變量,單一門檻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雙重門檻和三重門檻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說明在不同的環境規制強度下,我國城市金融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升級之間存在顯著的三重門檻效應。在考慮控制變量的條件下,無論是單一門檻、雙重門檻還是三重門檻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了檢驗。檢驗結果表明,以環境規制為門檻變量,分析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的關系采用三重門檻模型進行研究是科學的。
比較普通回歸模型和門檻面板回歸模型的估計結果發現,政府調控強度、基礎設施建設水平、信息化水平和人力資本均對產業結構升級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顯著性水平和影響力的大小存在一定差異性。而經濟發展水平對產業結構升級雖然具有促進作用但并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具體來看,政府調控強度的系數顯著為正,表明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將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基礎設施建設水平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增加基礎設施建設投入有利于產業結構升級。信息化水平的系數也顯著為正,表明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將促進產業結構升級。人力資本的系數也為正,雖然通過了顯著性水平檢驗,但其數值很小,原因可能是人力資本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匹配度不高,人力資本并沒有轉化成產業結構升級的真實動力。比較各變量回歸系數的大小,不難發現政府調控強度的系數最大,說明政府調控強度對產業結構升級的積極影響最大。金融發展水平對產業結構升級的積極作用雖然小于政府調控強度,卻大于基礎設施建設水平、信息化水平以及人力資本情況,進一步說明金融發展對我國各城市產業結構升級已經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現階段如欲提升產業結構水平應尤為重視金融發展的作用。
由不含控制變量和含有控制變量的門檻面板回歸模型可知,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的影響會因為環境規制強度的不同而表現出明顯的差異。被三個門檻值劃分的四個區間,雖然各個區間估計系數存在一定差異,但在環境規制約束下,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的影響的動態特征存在一致性,即環境規制正向調節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無論是在考慮控制變量的模型還是未考慮控制變量的模型中,隨著環境規制強度的不斷增加,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均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特征,符合正向倒U型非線性規律。由于不含控制變量的模型有較強的局限性,這里以含有控制變量的模型為基礎展開分析。
在含有控制變量的模型中,環境規制強度的三個門檻值分別為0.4179、0.7830和0.9219,被三個門檻值劃分的四個區間具體表現為:當環境規制強度低于第一個門檻值0.4179時,系數為0.0769,通過了1%顯著性水平的檢驗,表明在環境規制強度較低時,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有一定促進作用但其正向作用有限。當環境規制強度介于0.4179~0.7830之間時,其影響力增加到0.1271,通過了1%顯著性強度的檢驗,表明在該區間內,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正向影響力得到一定程度增強。當環境規制強度介于0.7830 ~ 0.9219之間時,其影響力增大到0.1988,該階段其積極作用最為明顯,說明金融發展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時存在最優的環境規制區間[0.7830,0.9219];當環境規制強度超過0.9219時,其系數估計值仍然顯著為正,但其積極影響明顯減弱,說明環境規制強度超過一定水平后,會在一定程度上弱化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這一影響力(系數為0.1181)還是顯著大于第一門檻區間的影響力(系數為0.0769),亦即適度的環境規制更有利于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發揮。可見,在較低的環境規制強度下,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有限,只有當環境規制強度跨越門檻值時,金融發展才會最大限度地促進產業結構升級。這并不能說明環境規制強度越大越好,環境規制強度也應適度,當環境規制強度過高時,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力會出現明顯弱化的情況。

經計算,2011 ~ 2016年全國220個城市環境規制的均值為0.5357,介于第一個門檻值和第二個門檻值之間,沒有進入最優門檻區間[0.7830,0.9219],在現階段應加大環境規制強度,可以進一步激發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積極作用。
(二)基于區域層面的分析
我國東、中、西部三大區域,在環境規制強度、金融發展水平、產業結構水平以及基礎設施建設水平、人力資本、信息化水平等方面均存在一定差異,在環境規制約束下,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可能會存在一定的空間異質性。按照東、中、西部把所研究的220個城市進行分組,東、中和西部地區城市個數分別為70、90和60個,其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單一門檻、雙重門檻和三重門檻檢驗結果以及門檻值如表4所示。為了更加直觀地刻畫在不同的環境規制強度下,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空間異質性,根據表3和表4的回歸結果,筆者繪制了一個反映不同環境規制強度下,東、中、西部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升級的簡易關系圖,見圖2。圖2中橫坐標表示金融發展,縱坐標表示產業結構升級,希臘數字表示根據不同的環境規制強度按門檻效應劃分的區間,雙重、三重門檻分別把環境規制強度從小到大劃分為三和四個區間,直線的斜率表示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影響力大小。

由表4和圖2可知:第一,在環境規制約束下,東部地區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呈現顯著的正U型非線性關系。即隨著環境規制強度的增加,地區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的促進作用越來越大,即東部地區應繼續加大環境規制強度以進一步發揮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第二,在環境規制約束下,中部地區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呈現正W型的非線性關系,即環境規制強度加大有利于進一步發揮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積極作用。環境規制強度在0.4018~0.5018之間時,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的正向作用最大,為0.1405;當環境規制強度超過0.5018時,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的正向作用下降為0.0261,也就是說環境規制強度超過0.5018時,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弱化;當環境規制強度繼續增加至超過0.7184時,其正向作用力又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加強,由0.0261增加到0.0615,但并沒有達到0.1405的水平,由此說明只有將環境規制保持在適度水平,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才會呈現最優狀態。第三,在環境規制約束下,西部地區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呈現倒N型非線性規律。在環境規制強度未達到0.8761前,城市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越來越大;當環境規制強度超過0.8761后,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積極作用有所弱化。這說明在金融發展促進產業機構升級的過程中,相較于中、西部地區,在東部地區實施嚴格的環境規制政策更有利于產業結構升級。中部地區相對于西部地區而言,其實施嚴格的環境規制政策更有利于產業結構升級。綜上所述,東、中、西部三大區域的最優環境規制強度呈現依次下降的規律。可能的解釋是:由于各區域經濟、文化、教育程度等諸多方面的差異導致“環保意識”不同,這種不同會影響金融發展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效果。具體而言,如果企業經營管理者有更強的“環保意識”就會主動進行生產工藝改造,快速達到政府規定的環境標準,提高產品的綠色化水平,促進產業結構升級,而“環保意識”不強的企業經營管理者在這方面會持相對消極的態度,主動作為可能性不大。同時,對于消費者而言,“環保意識”強的消費者對綠色產品的消費需求相對較大,會倒逼企業進行生產工藝的改進,從而促進產業結構升級。
四、穩健性檢驗
為了確保實證結果的可靠性,本文進一步從1320個研究樣本中隨機選出60%(1056個)進行穩健性檢驗,其門檻值及顯著性水平檢驗結果如表5所示。由表5可知,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接受三重門檻檢驗,環境規制變量三個門檻值分別為0.4013、0.7814和0.8503,與全樣本時的三個門檻值非常接近。三個門檻值把環境規制劃分為四個區間,這四個區間金融發展的系數分別為0.0769、0.1271、0.1988和0.1182,并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檢驗,也是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正U型特征。與表2結果進行對比,不難發現系數值與全樣本時十分接近,可見,本研究結論具有穩健性。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采用非線性門檻回歸模型,實證研究了在環境規制約束下,金融發展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異質性,主要結論如下:第一,在2011~2016年的考察期內,我國各城市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第二,在環境規制約束下,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具有正向的顯著三重門檻效應,即在環境規制強度較低的情況下,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有限,只有當環境規制強度超過一定值后,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正向效應才會最大程度地釋放,但并不是說環境規制強度越大越好,環境規制也有“度”的限制,當環境規制強度超過某個值后,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會出現一定程度的弱化;第三,在本文研究的220個城市中,其環境規制的平均值還未邁過最優區間的下限,說明環境規制強度還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第四,在環境規制約束下,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存在空間異質性,即東、中、西部城市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分別呈現出正U型、正W型和倒N型的特點。
不同區域在調整產業結構的過程中,應該將金融業高質量發展與城市綠色發展相互協調。具體政策含義如下:第一,目前我國整體上環境規制強度還有一定的提升空間,從短期來看,提升環境規制強度有利于發揮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但不能一味提高環境規制強度,一旦超過一個“度”,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正向影響將出現弱化的情況;第二,在通過金融發展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時,應充分考慮各城市的環境規制強度,即依據不同的環境規制強度制定不同的金融發展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的政策。
主要參考文獻:
[1]陳崢,高紅貴..環境規制約束下技術進步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研究——基于自主研發和技術引進的角度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16(12):95~ 100..
[2] Glodsmith R..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9:N/A..
[3]錢水土,周永濤..金融發展、技術進步與產業升級[J]..統計研究,2011(1):68~74..
[4]易信,劉鳳良..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轉型——理論及基于跨國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8(6):21~39..
[5]邵漢華,汪元盛..金融結構與產業結構的非線性轉換效應——基于PSTR模型的實證檢驗[J]..云南財經大學學報,2018(6):58~68..
[6]史恩義,王娜..金融發展、產業轉移與中西部產業升級[J]..南開經濟研究,2018(6):3~19..
[7]王春麗,宋連方..金融發展影響產業結構優化的實證研究[J]..財經問題研究,2011(6):51~56..
[8]鄧光亞,唐天偉..中部區域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調整互動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實證分析[J]..經濟經緯,2010(5):17~21..
[9]王立國,趙婉妤..我國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升級研究[J]..財經問題研究,2015(1):22~29..
[10]徐衛華,何宜慶,鐘慧安..金融深化、科技創新與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基于我國30個省市1997~2014年面板數據分析[J]..金融與經濟,2017(3):13~19..
[11]王定祥,吳代紅,王小華..中國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優化的實證研究——基于金融資本視角[J]..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5):1~6..
[12]羅榮華,門明,何珺子..金融發展在促進我國產業結構調整中的效果研究——基于我國30個省級面板數據[J]..經濟問題探索,2014(8):84~91..
[13]Porter M. E.,Linde V. D.. Toward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competitiveness rela? tionship[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5(4):97~118..
[14]孫坤鑫,鐘茂初..環境規制、產業結構優化與城市空氣質量[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7(6):63~72..
[15]阮陸寧,曾暢,熊玉瑩..環境規制能否有效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基于長江經濟帶的GMM分析[J]..江西社會科學,2017(5):104~111..
[16]胡建輝..高強度環境規制能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嗎?——基于環境規制分類視角的研究[J]..環境經濟研究,2016(2):76~92..
[17]梅國平,龔海林..環境規制對產業結構變遷的影響機制研究[J]..經濟經緯,2013(2):72~76..
[18]肖興志,李少林..環境規制對產業升級路徑的動態影響研究[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13(6):102~112..
[19]李娜,伍世代,代中強,王強..擴大開放與環境規制對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J]..經濟地理, 2016(11):109~115..
[20]程中華,李廉水,劉軍..環境規制與產業結構升級——基于中國城市動態空間面板模型的分析[J]..中國科技論壇,2017(2):66~72..
[21]鄭加梅..環境規制產業結構調整效應與作用機制分析[J]..財貿研究,2018(3):21~29..
[22]時樂樂,趙軍..環境規制、技術創新與產業結構升級[J]..科研管理,2018(1):119~125..
[23]朱歡..金融發展會加劇環境污染嗎?基于Hansen門檻模型的檢驗[J]..預測,2018(3):56~61..
[24]李凱風,王捷..金融集聚、產業結構與環境污染——基于中國省域空間計量分析[J]..工業技術經濟,2017(3):3~12..
[25] Bruce E. Hansen. Threshold effects in nondynamic panels:Estimation,testing,and inference[J]..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9(93):345~368..
[26]趙春燕..人口老年化對區域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基于門檻規模模型的研究[J]..人口研究,2018(5):78~89..
[27]韓先鋒,惠寧,宋文飛..OFDI逆向創新溢出效應提升的新視角——基于環境規制的實證檢驗[J]..國際貿易問題,2018(4):103~116..
[28]陳崢,高紅貴..環境規制約束下技術進步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研究——基于自主研發和技術引進的角度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16(12):95~ 100..
[29]周昌林,魏建良..產業結構水平測度模型與實證分析[J]..上海經濟研究,2007(6):15~21..
[30]徐德云..產業結構升級形態決定、測度的一個理論解釋及驗證[J]..財政研究,2008(1):46~49..
[31]干春暉,鄭若谷,余典范..中國產業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和波動的影響[J]..經濟研究,2011(5):4~16..
[32]黃亮雄,安苑,劉淑琳..中國的產業結構調整:基于三個維度的測算[J]..中國工業經濟,2013(10):70~82..
[33]張成,陸旸,郭路,于同申..環境規制強度和生產技術進步[J]..經濟研究,2011(2):113~124..
[34]汪浩瀚,潘源..金融發展對產業升級影響的非線性效應——基于京津冀和長三角地區城市群的比較分析[J]..經濟地理,2018(9):59~66..
作者單位:江漢大學商學院,武漢43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