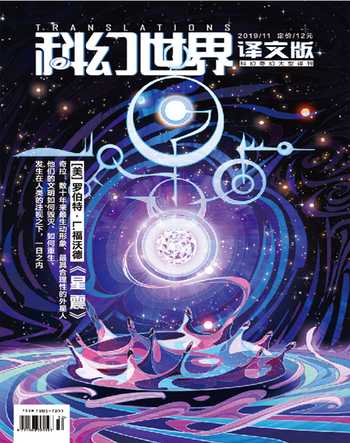樂意的身,勉強的心
[美]瑪麗?韋伯特 奚家驊

我只聽說過那次造訪,并沒有親眼見到。目擊者大部分是“心”,還包括一個在陰暗面心池邊緣負責照看育兒所的“腦”。當時有兩個生物,和“身”差不多大,但卻像小樹苗般柔滑。他們在陰暗面的南岸留下了一些藝術作品,一直到育兒所。其中一個生物繞著屋子,弄亂了部分世界地圖并惹惱了腦社區。之后,伴著日落,這些外來者離去了。
這些藝術作品就像那些外來者一樣,有著非自然的順滑感。它不像我們這些“身”用手指或者腳掌創作出的作品,是一個形似腳印的柔和線條,但底部有圖案,組成一條條小溝,積水之后看起來十分舒服。我很欣賞這些作品,卻無法理解它們所表達的意義,只是單純地被眼前的形狀吸引了。它們讓我心情愉悅。
這些藝術作品順著林間小路次遞而上。我一路尋去,在到達半山腰那處泥巴硬得像皮膚一樣的地方之前,不得不停下來休息一會兒。我可以看見這些外來者的作品慢慢變得模糊,只能在高處多沙的地面上看到一點點,更遠的地方就看不見了。也許順著這些印記能找到外來者們,就像肺們為找到彼此而沿途留下的化學信息?
我爬回陰暗面的岸邊,接著一直游到深水區,肺們喜歡在那兒對著太陽曬它們羽毛般的鰭。
大多數肺都游走了,它們都是些害羞的家伙。只有一個肺待在原地沒動,在水面慵懶地劃出漣漪,剛好夠讓自己浮起來。
“我正在找一個肺。”我說。
他劃了劃他的纖毛,接著我接收到了他散發出的、用來表達想法的化學信息。他似乎并不驚訝,而且還很樂意。我朝他游近,然后打開我的胸腔。肺這次散發出的信息帶著疑問——作為一個可運作的身體而言我還太年輕了,而且我好像還有沒有完整地研究過世界地圖。“我將要開始一場冒險。”我對他說。
他游進來的時候弄得我癢癢的,要保持不動可是最難的部分。
肺覺察到我并沒有心,立刻散發出滿是擔憂與緊迫的信息。
我說:“我覺得先找一個肺比較好。”
肺覺得我有點傻,他進駐過更聰明的身。
我帶著他一起游回心池。陰暗面里的大家對出去冒險都沒啥興趣,他們都忙于處理泥巴地上被外來者入侵后留下的深刻印記。
肺感覺到了新的化學信息,也許正是外來者留下的。是一股澀澀的味道,像是花,卻算不上芳香。陌生,而且也沒有生命的氣息。
我們走到光明面心池,這里散發出和陰暗面心池相似的信息素,而等我們說出自己的計劃之后,也遭到了相同的抵觸。一個名叫“他沉得慢升得快”的家伙建議我們先去找個腦。心們相信腦能幫助他們搞清楚,是依然待在原地還是遷居別處更安全。他們正在考慮遷往奧克耐克。
我們城市的腦們占據著高處的熱池子,那里的水富含硫黃且濃厚黏稠。沒有心的陪伴讓這趟旅途十分辛苦,但至少我還有個肺。前往最近腦池的路上,肺都在為疼痛而抱怨。這個地方叫作“和平之峰”,更準確些是“和平之峰 7a”。這里住著三個腦,但都在為他們第一個孩子的出生而操勞。他們把我們推向7b,說那里的住戶不像他們這么有家庭責任感。
“和平之峰7b”里住著四個腦。其中有一個十分年輕,想立即跟我一起走,但肺不希望和一個年輕的腦同行。這個小家伙的三名家長名叫“節制”、“教會”和“慷慨”。(這孩子還在為自己命名日的臨近而擔心,但毫無疑問他的家人會選出最符合他性情的名字)。腦們彼此間放出明亮的閃光,進行了一番討論。不顧小家伙的強烈反對,他們決定讓“節制”跟我們走。
腦們的家長制根深蒂固,滲透進他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身體們不知道幼芽是從誰的種子萌發出來的,所以我們都沒有父母且同時又都是父母。相較之下,我們的處世之道顯得更通情達理。
肺預留了連接的位置,“節制”輕車熟路,很快就加入了我們。“噢,我可不像有些腦那么專橫。”她說著,往下朝肺探出她的觸須。她輕柔地撫弄著肺,直到化學信息反映出他慢慢平靜了下來。
“節制”繼續扭動了一會兒,這讓我感到作嘔,但接著我的視線變清晰了,并意識到如果再不找到一顆心,我們三個離水域這么遠都將面臨窒息的危險。
我把一只手泡在腦池溫熱且富含養分的池水里,確保在我們啟程回心池前肺和“節制”都有充分浸濕。
“愛在浪頭搖”其實并不需要參與這場冒險,但當她看見我們蹣跚著走完最后幾步,終于到達水池的時候,她還是游向了我們。
當她加入我們并自我介紹時,肺的呼吸變得更容易了。我們大家都向她表示了感謝。
“總得有人來幫忙。”她說,“而我是離得最近的。”
“一顆務實的心,正是我喜歡的,”“節制”說道,“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或許我們走之前可以把世界地圖修好?”
“愛在浪頭搖”說:“這件事可以再等等,那些外來者可能很危險,而且他們也許正在行進。我們得趕緊行動。”
“看著地圖不再精確,實在讓我心煩意亂。”“節制”說道。
“這只需要一小會兒。”我說。去地圖那里的大部分路程我都在水里游泳,比走路更快。我迅速將地圖上被弄亂了的棍子放回原位。有一根斷成了兩截,但“節制”覺得直接拼成一個長條就行。
再說,我們可是在趕時間。
我準備游向雜草叢生的水岸,那里是胃們進食的地方,但被身體里的其他部位投票否決了。“這可不是帶著心寶寶去伊納托,”“節制”說,“我們沒有胃也行。”
一個胃抬起了她的鼻子,我似乎從她的眼神里看到了渴望,但不行,我們根本不清楚那些外來者還在不在這附近——可能已經永遠離開了!實在不能浪費時間了。
有了心和肺的陪伴,前往樹林的上山路便不再覺得陡峭了。很快我的腳就陷進了沙地,腳底傳來又涼又軟的觸感。我們所處的位置足夠高,向下眺望可以將世界盡收眼底:從池水淺而遠的伊納托,到卡拉布尼克的那片咸海,那里的心游弋在海水中,卻無法與我們的心交配。
路上有適合用來制作世界地圖的小木棍。我經過的時候把它們放在一邊,不禁想知道那些外來者是否去過其他城市了。在高處行走的感覺很棒。我們現在能夠理解為什么身、心、肺和腦需要聯合起來一道上路了。冒險的火花在肺的分泌物中激昂澎湃。
“節制”提醒我停下腳步朝下看。“不是那兒,朝落日那邊轉一點,那個方向。”
更多的外來者的藝術品印在一條狹窄的側徑上,通向更遠的地方。前往奧克耐克的主路就在我們面前,寬廣、清晰又平坦。而這條小徑則彎彎曲曲地繞進了樹林,地上則布滿下雨時水流的路線。
從這條小徑往上走不大可能找到任何水塘、濕地或是池子。恐怕從來沒誰想過要走這條路。
爬坡很艱難,耗費了我很多精力。我必須時刻注意自己該在哪兒落腳。心和肺一直都在耐心工作,而腦給了我很多幫助,一直在幫我注意尋找最佳的攀登路線。
這條山路似乎永遠不會到頭。我回頭看了看,距離遠得令我害怕,但當我意識到,我們已經走過一大半的路程,很快就能到達山頂時,我松了口氣。前方的天空在樹梢間已經清晰可見,是一片毫無遮攔的空白,就像身處水塘中央往上看的時候那樣。肺非常興奮。“愛在浪頭搖”開始擔心和我們一起來會不會成為一個致命錯誤。“離開水這么遠從來不會有什么好結果。”她說。
地面的坡度稍微變緩后,我突然能看到遠處了——我還期待著這個峰頂就像腦們占據的高處,有宜居的溫泉——但并沒有。我們緩緩而上,出現在眼前的是一片寬敞的平地。前方不遠處有些奇怪的小丘,像那些外來者一樣光滑潔白。
“帳篷。”“節制”這么稱呼它們。在沒找到更好的辦法前,腦們曾用拉伸開的胃的表皮制作帳篷。“節制”提出了好幾種對這些帳篷的制作材料的猜想,她覺得這些外來者也許會互相剝對方的皮。
“我們回去吧,”“愛在浪頭搖”說,“在他們來抓我們之前。”
“我們得了解更多點,”“節制”說,“這些東西看起來是最近才制作的。也許……我們可以找個背光處,躲在那些葉面油滑的灌木叢后面?”
肺開始害怕了。
我抬腿朝前走了一步。
“你在干什么?”“節制”問道。
我又朝前走了一步。
“愛在浪頭搖”開始在我胸膛里顫抖。肺散發出安慰她的化學信息,我的肋骨因此變得麻麻的,但她還是一直在發抖。我仍然往前走去。這正是一個身子所能做的。
來不及說話討論了。外來者現在正朝我們走來。
“好吧。”“節制”說,盡管她竭力裝出語調平靜,卻依然掩蓋不住聲音中流露出的焦慮。“首先要做的是去了解他們有沒有腦。”
肺認為這正是腦會說的話。
“呃,他們肯定有肺,”“愛在浪頭搖”說,“他們能離開水運動。”
“我們也知道他們有身子。”我說,我決定用身的語言來和他們交流。我伸出一只手,我面前的那個外來者也伸出他的手。那只手和他身上其他部分一樣白,但有著用關節連接的粗短手指。我的三個卷須狀的手指觸碰了對方的五個手指,我用我最小的卷須纏繞著它們。外來者的手指隨著回應而彎曲,意在問候。
外來者上部有兩個亮晶晶的東西,就像兩個小水塘,里面似乎有一條魚,就跟心游曳在池子里一樣。也許那是腦?一個閥門動了,將空氣壓縮成聲波,就像心說話的方式一樣。我倒吸了一口氣。“他們有兩種語言!你能明白嗎,‘愛在浪頭搖?”
“節制”愣住了,被震驚到無法運作。肺因這些外來者缺乏化學信息而感到沮喪,他們的表面被包裹著,找不到毛孔。
“歡迎來到尼卡特城。”“愛在浪頭搖”說。
現在請從你的視角來告訴我們,你是怎么看我們的,以及為何你的名字既是身體語言(十指指向胸口),又是一句口頭的“薩曼莎”。穿著防護服的你一定很孤單,無法了解自己的胃在想什么。另外,我們還想請你解釋一下,當你知道我們的心、肺和大腦都是獨立的個體時,你為什么會問我們的心是否在引導我們?我只能說,心是不情愿的。而我總是希望能找到一個充滿激情的肺,因為肺們能品味化學信息,敏銳地感受世界上的一切。
【責任編輯:吳玲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