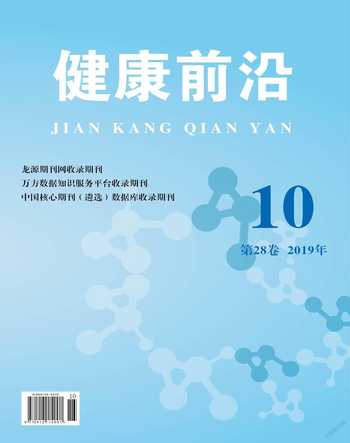中醫治療乙肝研究思想
董亞娟
摘要:乙型肝炎起病隱匿,容易復發,每遷延成慢性,并有進一步發展成肝硬化、肝癌的趨勢。抗病毒治療、免疫治療、保肝降酶是目前西醫治療乙型肝炎的主要手段,但迄今尚無理想的治療乙肝的藥物。我們運用中醫辨證論治法治療乙型病毒性肝炎取得了顯著臨床效果,茲結合臨床實際,談談乙型肝炎的中醫辨治思路與方法,以與同道共磋。
關鍵詞:乙型肝炎;中醫病因;中醫病機;中醫治法;
1疫毒感染是主要致病因素
疫毒是指較六淫病邪損害更強,具有強烈傳染性的一類病邪,在古代文獻中,又稱為時氣、非時之氣、異氣、癘氣、雜氣、毒氣等,其所致疾病一般稱為溫病、溫疫等。疫毒致病的最大特征是傳染性強,易于發生流行。故曰:邪之所著,有天受,有傳染,所感雖殊,其病則一,此氣之來,無論老少強弱,觸之者即病(溫疫論)。中醫學還認識到疫毒并非一種,而是一病一氣,如吳又可在瘟疫論中就指出:為病各種,是知其氣不一也,雜氣為病,一氣自成一病,有某氣專入某臟腑經絡,專發為某病,故眾人之病相同。這種一氣自成一病和一病自有一氣的觀點,與現代醫學認為每種傳染病皆有其特異性病原體驚人相似。
2疫毒濕熱瘀郁、肝脾腎失養是主要病理環節
金匱要略臟腑經絡先后病云: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說明肝病易于傳脾,乙肝也不例外。肝主疏泄,體陰而用陽,喜條達而惡抑郁。肝木疏土,助其運化,脾土營木,利其疏泄。導致乙肝的疫毒之邪具有偏嗜肝臟特性,疫毒無論是從血液入肝,還是從消化道侵入肝臟,結果都是導致肝郁氣滯,乘犯脾胃,影響脾胃運化功能,水谷津液不歸正化,變生內濕。因此乙肝患者除可見有脅肋脹痛、噫氣、性情急躁等肝郁不達癥狀外,每易出現脘腹脹悶、厭食油膩、惡心嘔吐、口淡乏味、便溏泄瀉、舌苔厚膩等脾虛濕盛癥狀。
3清化調養是治療大法
3.1解毒逐邪法
余霖在疫疹一得中云:疫乃無形之毒,吳又可在溫疫論中明確提出:客邪貴乎早逐邪不去則病不愈。乙肝為感染疫毒所致,若正不能驅邪外出,導致邪氣滯留,則乙肝遷延慢性化,若經治療正能驅毒外出,則疾病向愈。疫毒感染是乙肝發病的主導因素,并且貫穿疾病的全過程。故在治療過程中須伍以解毒逐邪藥物。由于毒邪本具火熱之性,病久肝氣郁可化獲,濕邪蘊久生熱,因此解毒逐邪藥多以清熱解毒藥物為主,如垂盆草、虎杖、山梔、大黃、苦參、黃芩、半枝蓮、半邊蓮、大青葉、雞骨草、龍膽草、草河車、白花蛇舌草、敗醬草、水飛薊、連翹、蒲公英、野菊花、天葵子、升麻、玄參等。必要時亦可適當運用全蝎、蜂房等藥物以毒攻毒。
3.2疏肝解郁法
肝為將軍之官,主疏泄,性喜條達而惡抑郁,為藏血之臟,體陰而用陽,是人體氣機運行暢達的標志。疫毒偏嗜于肝,導致肝臟疏泄功能失司,因此治療乙肝每須應用疏肝解郁藥物,以宗內經木郁達之之旨。治療乙肝常用疏肝解郁藥物,以柴胡疏肝散為基本方,藥如柴胡、香附、枳殼、枳實、玄胡、川楝子、青皮、橘核、陳皮、谷芽、麥芽、八月札、佛手、合歡皮等。其中,柴胡最為常用,一則柴胡入肝經,取引經之意(宜醋炒后用,以酸味入肝故也),二則柴胡能疏肝解郁,切中乙肝肝氣郁結之機。
3.3健脾化濕法
乙肝病毒侵襲肝臟后,導致肝之疏泄功能失司,木旺則乘脾土,導致脾運功能受損。正如血證論中所說:木之性主于疏泄,食氣入胃,全賴肝木之氣以疏泄之,而水谷乃化;設肝之清陽不升,則不能疏泄水谷,滲泄中滿,在所不免。另外,治療乙肝的清熱解毒藥物,性多寒涼,久用有苦寒敗胃之虞,因此治療同時須用健脾化濕藥物。因此,肝病運用健脾化濕藥物,尚有提高人體免疫力,增強病毒清除能力作用,誠如陳正復在幼幼集成中所云:脾土強者,足以捍御濕熱,必不生黃,惟其脾虛不運,所以濕熱從之。常用健脾化濕藥物有:黨參、太子參、茯苓、甘草、黃精、蒼術、白術、鳳尾草、土茯苓、薏苡仁、扁豆、藿香、佩蘭等。
3.4活血化瘀法
乙型肝炎遷延不愈,形成慢性化,勢必久病入血。肝為藏血之臟,濕熱久罹,氣滯血瘀,邪毒從氣分進入血分,濕熱與血互結,表現出肝郁血瘀之證,血熱與血瘀并見,癥見脅肋刺痛、脅下有塊、肌膚甲錯、身目黃而晦暗、面色黯紅、顴布赤絲血縷,手掌魚際紅赤,舌質多紫,或見齒衄鼻衄等。常用的活血化瘀藥物有赤芍、丹參、景天三七、當歸、茜草根、莪術、姜黃、郁金、延胡索、澤蘭、水紅花子等。其中,丹參、景天三七一般用于肝纖維化、肝硬化的防治;面黃不華、肝血虧虛者,用當歸、茜草根、雞血藤等養血活血;肝硬化時,每須用莪術等活血化瘀散結之品,如肝硬化伴見肩臂疼痛麻木者,則要用姜黃取代莪術,如肝硬化伴見膽紅素增高者,則用郁金易莪術;肝炎肝硬化,發生腹水時,則用澤蘭、水紅花子活血化瘀、利水消腫。
3.5補益肝腎法
慢性乙型肝炎,濕熱疫毒之邪蘊結不去,耗傷肝陰,或邪從火化,陰津被灼,亦可因脾運被遏,而陰血化生無源,導致肝之陰血虧虛,久則因肝腎同源累及腎陰亦虛,而表現為肝腎陰虛之證。此時治療應用滋養肝腎的藥物,以滋水涵木,木得滋榮,自能柔順條達,疾病易愈。方可效一貫煎加減,藥用生地、熟地、山茱萸、金釵石斛、貫眾、北沙參、麥冬、枸杞子、阿膠、百合、鱉甲、牡蠣等。其中,鱉甲主心腹癥瘕塊積、寒熱(本經),去血氣,破癥積,惡血(大明),因此鱉甲為消癥、散瘀、益陰之佳品,誠為預防肝硬化、肝癌之良藥。鄧鐵濤教授亦認為治療慢性肝病,不但要從脾治,而且要從腎治,盡早使用滋補肝腎之品,務在先安未受邪之地。
陰陽互根,陰病及陽,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晚期亦可出現腎陽不足之證,此時治療應用溫補腎陽之品,常用藥物有:肉桂、肉蓯蓉、仙靈脾、炮附子、鹿角片等。現代醫學實驗研究和臨床研究已證實,此類溫陽藥物有明顯的免疫調節作用,能明顯提高免疫抑制狀態下的機體體液免疫和細胞免疫力,對特異性和非特異性免疫都有明顯的增強作用。再者,腎為人體陽氣之根本,在腎陽溫煦鼓舞下,肝陽得以疏泄氣血,脾陽得以斡旋上下。若腎陽不足,則肝陽難以升發,疫毒之邪內陷,導致病情遷延不愈,因此適當運用溫補助陽通陽的藥物,可助解毒透毒,是促使乙肝病毒指標轉陰值得嘗試的重要方法。
參考文獻:
[1]郝志健.脾養肝、解毒活血為主治療慢性乙型肝炎理論研究.山東中醫藥大學學報.2003;27(1):58.
[2]韓亞娟.HBV血清標志物3種模式患者多種補體水平比較.中西醫結合肝病雜志.1996;9(4):30.
[3]伍春蓉.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中醫辨證分型與肝臟病理關系探討.湖北中醫雜志.1987;9(2):13.
[4]肖會泉.鄧鐵濤治療慢性乙型肝炎經驗.實用中醫雜志2000;16(1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