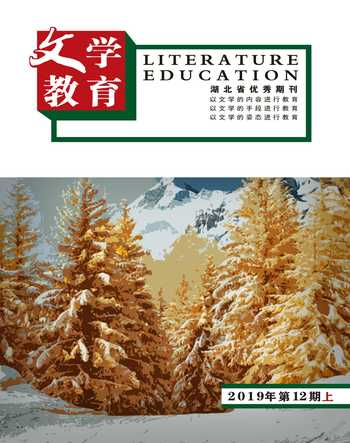《妻妾成群》中梅珊命運悲劇性探析
內容摘要:蘇童在其成名作《妻妾成群》中,成功塑造了梅珊這一個敢愛敢恨,具有反叛意識的女性形象。她是陳家的三姨太,卻是這深宅大院中孤獨體的存在,為追求自然欲望反抗封建道德常規,直至走向毀滅。借助馬斯洛需求理論中的缺失需要來解讀梅珊命運悲劇,并指出梅珊內心不同層次的需求與其所生活的時代背景是促使她一步步走向滅亡道路的原因。而在梅珊的身上體現出的宿命輪回與鏡像折射的特點,不僅是她個人悲劇命運的構建,同時也折射出那個時代下女性的悲劇命運。
關鍵詞:梅珊 孤獨 悲劇 宿命 鏡像
“王干將蘇童小說的人物分為三大類:昨日的頑童、還鄉者、紅粉。”[1]而引起人們極大興趣的是最后一類人物,在《妻妾成群》這部作品中,蘇童成功地塑造了在“一夫多妻”的封建大家庭中,四個個性鮮明的妻妾形象。其中,三太太梅珊的身上就凸顯著與眾不同的一面。她是一個享樂主義者,為了追求自身的快樂,敢于向男權進行對抗,這種反抗意識在她的身上萌芽并滋長直至毀滅。
一.梅珊命運悲劇的形象塑造
1.孤獨者
梅珊雖有傾國傾城的相貌以及會唱戲的本領受到陳佐千的喜愛,娶回家當了三房太太,但在這個家中她沒辦法改變自己身為妾的身份,改變自己受支配的地位,她是這個庭院中的孤獨者,而這樣的孤獨主要從她身體、內心和行為這三個方面體現。
首先是身體上的孤獨,身體上的孤獨主要表現在性欲得不到滿足。她曾毫不掩飾自己的欲望對頌蓮說:“他只要超過五天不上我那里,我就找個伴,我沒法過活寡的日子。”[2]27梅珊是位年輕的女人,有著正常的生理需求,但是每天卻只能守著陳佐千這個老男人,還要與其他人分享和爭寵,至于留于哪個房,都是憑他的喜好與心情。再加上陳佐千的年事已高,他的身上開始出現不可避免的男性“悲劇”,這樣的他更加不能滿足梅珊身體上的需求。
其次體現在內心上。身體上得不到滿足,也導致了內心里的空虛。在這個“一夫多妻”封建大家庭中,并沒有所謂的姊妹之親,丈夫之愛,有的只是明爭暗斗的爭寵。陳佐千妻妾成群,他可以如同一個帝王,每天坐等著他的“嬪妃們”使出渾身解數來取悅他,在頌蓮那邊受氣,就來梅珊的房間尋求“安慰”。陳佐千作為陳家絕對的權利象征,只是把他的女人們當成泄欲與生孩子的工具。在這個陳家,面對丈夫的“冷落”,面對無人談心的局面,梅珊的內心是孤獨的。
最后體現在行為上。蘇童對梅珊有三次唱戲的描寫,第一次梅珊唱得那么凄涼婉轉,她的身影是那么的濕潤而憂傷。第二次的梅珊舞動的身影又像是一個俏麗的鬼魅訴說著“形吊影影吊形我加倍傷情”[2]35的感傷。第三次則是嘆自己“紅顏薄命前生就,孤眠不抵半床寒”[2]49的幽怨。梅珊看似在唱戲文,其實是在唱自己,是在訴說自己的孤獨,哀泣自己的處境。梅珊還迷麻將,用麻將來打發自己的孤獨時光,同時也借著打麻將來約會自己的情人,緩解身體的孤獨。
從梅珊的身上,我們能感受到濃濃的孤獨感。身體與內心的孤獨,梅珊無處釋放,只能通過唱戲和打麻將宣泄出來。梅珊用唱戲和打麻將的行為,通過戲聲和肉欲來傾訴自己孤獨。
2.放縱者
《妻妾成群》中發生的所有事情都是在陳家大院里進行的。這個看似富麗堂皇的庭院,其實是一個吃人的牢籠。大院構成了一個比較封閉的空間,四面高墻限制了女人們向外自由活動,也禁錮著人們的思想。
在陳家大院里,沒有人是不被壓抑著的,他們的內心隱藏著難以言喻的痛苦。原配毓如過著有名無實的生活,忍受丈夫的一次次娶妻的痛苦,只能用吃齋念佛尋求最后的精神寄托。卓云雖笑臉迎人,心理卻總盤算著鏟除丈夫身邊的女人。頌蓮年級輕輕便陷入大家庭爭寵的旋渦中。
文中似乎有這么一個人置身于事外,那就是梅珊。她會在新婚之夜的時候裝病騙走陳佐千;一句“老娘不愿意!”[2]12拒絕為陳佐千唱戲;雇打手打卓云的孩子為自己的孩子出氣。通讀全文,我們感受到梅珊是活得那么自我,那么瀟灑自如,似乎看不出她的痛苦。但其實并不然,“生存在陰郁、窒息的環境中為了自我生命的自由, 他們進行了無數次逃亡與找尋的嘗試。”[3]梅珊的逃亡與嘗試就是試圖用放縱的方式來改變她的生活狀況。梅珊是戲子出身,社會身份低下,雖然她高傲,但她卻沒有毓如與頌蓮的底氣。她擁有的唯一資本就是那張傾國傾城的臉,讓陳佐千臣服于她的美貌,通過駕馭陳佐千來駕馭其他人來改變自己的地位。雖然陳佐千對她“又怕又恨又想要”[2]27,但是陳佐千也不會允許梅珊爬到他的頭上,他對梅珊的寵愛只是一時的新鮮感。因此梅珊找了比陳佐千更年輕、更有活力的醫生作為陳佐千的替代品。她肆無忌憚地偷情,甚至大膽到敢當著頌蓮的面在麻將桌下交纏著雙腿。梅珊的張狂放縱無疑是在飛蛾撲火,但這樣的放縱也帶有著些許反抗的意味在其中,她讓我們看到了在那個年代女性想要追求自身需要而奮力反抗的精神。
自古以來都說“婊子無情,戲子無義”,梅珊也是一個戲子,卻是一個性情中人。對于梅珊的刻畫,作者所用的筆墨并不多。對于梅珊情感方面的表達,作者有別于頌蓮的心理描寫,而是采用戲文來加以強化。通過戲文來表達她的孤獨,表達她的不滿,將梅珊這個孤獨寂寞卻又敢愛敢恨的女性形象栩栩托出,只可惜她最后的死不能像杜十娘那樣死得清清朗朗。
二.梅珊的悲劇根源
1.自我需求的缺失
需求層次理論不僅揭示出人性的內涵及其實現的必由之路,而且闡明了人應有的價值選擇。需要層次理論的提出者是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他認為“人是一種不斷需求的動物,每一種基本需要的滿足都會引發‘更高’的需要,支配下一個意識階段”[4]4。梅珊就是在這樣自我需求的追逐中逐漸走向毀滅。
“生理需要是人對食物、水、空氣、睡眠、性等的需要,是人最基本、最強烈的需要,是其他一切需要產生的基礎”[4]52。梅珊從一個受人消遣的戲子變成陳家的三太太,地位上的上升也意味著物質上的滿足。“畫了眉毛,涂了嫣麗的美人牌口紅,一件華貴的裘皮大衣搭在膝上。”[2]27這是小說中一處對梅珊外在形象的描寫。文中還講到了梅珊點煙、打麻將等一些娛樂生活,可以看出,梅珊已經脫離了那種居無定所的漂泊生活,過上了養尊處優的日子。由此可見,梅珊在生理需求方面是可以得到滿足的。
梅珊因為生理需求得到了滿足,所以產生更高一級的需要——安全需要。但在陳家,四個女人是永遠學不會和諧相處的,她們更擅長于刺傷自己的同胞來爭奪男人,獲取家庭地位,“像四棵枯萎的紫藤在稀薄的空氣中互相絞殺,為了爭奪她們的泥土和空氣。”[5]62前期的梅珊是沒有安全需要的,她剛進入陳家就成了卓云的眼中釘,她在懷孕期間卓云曾在她的安胎藥里放墮胎藥,差點害得梅珊一尸兩命。到了后期,梅珊生了一子,再加上頌蓮入門,陳佐千常常留宿于頌蓮那房,卓云的目標開始從梅珊轉移到頌蓮身上,梅珊的人身安全得到了暫時的保障,安全需求得到暫時的滿足。
從戲子變成三太太,梅珊的生理需要滿足了;頌蓮的到來,梅珊的安全需要也得到了滿足,兩者的相對滿足促使了梅珊歸屬與愛的產生。處于這一需要階層的人,“把友好和愛看得非常可貴,希望能擁有幸福美滿的家庭,渴望得到同伴的認同。”[4]55在梅珊的心里,對歸屬與愛的需求更多是在于對陳佐千愛的需求,并成為她的“優勢需求”。但陳佐千對于梅珊,只是把她當作消遣的工具,并沒有半點真心可言。梅珊從陳佐千的身上得不到“優勢需求”的滿足,漸漸地她對這種不穩定的愛轉變成了性欲上的滿足,她在外面與醫生茍且,在醫生的身上找尋身體與精神上的慰藉,變成一個享樂的主義者。
2.二元對立規則下的毀滅
小說的背景是在“五四”運動剛過后,新舊思想相互相碰的時期。這個時期雖然有新思想的沖擊,倡導男女平等,但是封建思想依舊站領主導,男尊女卑的思想依舊深入人心。
曾作為一名戲子的梅珊,身份更是低賤。因此,梅珊想到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就是嫁給陳佐千,成為陳家的三姨太。看似梅珊是飛上枝頭當鳳凰了,但其實梅珊只不過是從封建社會的邊緣轉到了封建家庭的邊緣,而最終她也在這個邊緣中走向了滅亡。“家國同構均以血親--宗法關系來統領,存在著嚴格的家長制。”[6]陳佐千是大家長,他控制著陳府的一切,他可以有三妻四妾,但女性則必須要三從四德,作為這個家庭的主導,他是女人生活的全部。當他得知梅珊背著他偷情的時候,他毫不猶豫地將梅珊投入那口象征著家法的古井里。“在這個二元對立的規則中,假如她不在他指定的一端位置上,那么就沒有她的位置。假如她不想成為他,仍想成為她是她自己,那她就會被粉碎。”[6]梅珊想要追求自己的內在需要,她想成為自己,這正是陳佐千所不允許的。
梅珊為了滿足自身的需求,在這個充滿爾虞我詐的家庭中不斷掙扎,卻連最基本的低級需求都無法滿足是可悲的。蘇童將梅珊置于封建的老宅里,讓梅珊在這樣男女規則失衡下生存,讓她遭受女性之間的相互殘害,讓她為了所謂的利弊在男權社會中迷失自我。蘇童關注女性的人性,將人性與命運結合在一起,還原了封建舊式家族女性矛盾而又悲慘的生存境遇。
三.梅珊命運悲劇的構建
1.宿命論:回環結構式輪回
蘇童喜歡構建一個虛構的世界,在這里面,時間成為了背景,“作者更加關心的是事物的循環往復,更加關注的是命運的循環安排”。[7]《妻妾成群》也是作者虛構的一個故事,在陳家大院里,事物在循環往復,陳家的大院那些女人身上不斷上演著宿命輪回的命運,她們的生命顯得那么不堪一擊。
蘇童在對梅珊命運的構建上帶有著濃濃的宿命的意味。《妻妾成群》的故事是從四太太頌蓮被抬進陳家時說起,作者以她為第一視角講述她在陳家大院里的所見所聞。她看到梅珊因偷情被投井而死,她自己又在井邊發瘋,文章的最后陳佐千娶了第五位太太文竹,陳家大院里的女人的宿命在不斷輪回,而這樣輪回,蘇童用一個意象“井”來體現。“井”作為一個古典意象在《妻妾成群》中多次出現,并與書中女人們的命運相互交織。童慶炳先生在《文藝理論教程》曾對“意象”做了如此解釋:“意象是用來表達哲理觀念的,是具有象征性和荒誕性的,是一種藝術典型。”[8]這口井是陳家家法的象征,同時也是死亡的代名詞,這口井折射著人物的特殊情緒,暗示著人物命運歸宿。雁兒走后老女傭宋媽來伺候頌蓮,宋媽的出現揭開了這口死人井的神秘面紗,前代姨太太因為與他人私通而被投入井中。這口井是陳家女性偷男人的葬身之地,是陳家不容侵犯的規矩。梅珊因耐不住寂寞,與醫生私通,她的死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她的結局定會與前代的姨太太一樣。頌蓮與梅珊一樣都是空虛寂寞的女人,當她看到梅珊與醫生的曖昧之情后心中也燃起了一種欲望之火,最后她看見梅珊的死亡過程,結局她在井邊瘋了。梅珊走了前代姨太太的老路,頌蓮走了梅珊了路,文竹的到來,這口井成為了后院女人宿命的輪回。
在蘇童運塑造的回環的世界里,我們看到的是不可抗逆的命運安排,是宿命的指引,無論是前代姨太太、梅珊還是頌蓮、文竹,只要是生活在這個男權社會為背景下的女性,她們的命運早已經被安排好了,蘇童在事情的循環和角色的輪回中敘述著命運的悲歡。
2.鏡中像:梅珊的鏡像解讀
“鏡像”一詞是拉康提出的指自我構建與本質以及自我認同的形成過程。在《妻妾成群》中,梅珊作為頌蓮的參照物,在各方面對頌蓮都產生了影響,讓頌蓮在不斷認同與確認中尋求自己的身份。作為頌蓮的鏡中像,通過對梅珊的鏡像解讀,解讀梅珊作為頌蓮內心參照物的構建,讓梅珊的悲劇命運的張力得以充分凸顯。
梅珊與頌蓮兩個在《妻妾成群》中都是年輕貌美的女人,但在陳佐千的眼中,頌蓮與梅珊卻并沒有什么區別,一個是“婊子”,一個是“戲子”。作為同樣在男權社會下得不到愛情的孤獨空虛的女人,頌蓮在與梅珊的相處中,頌蓮總是不自覺中認同梅珊。就如黃田心在《表象與本相<妻妾成群>中頌蓮、梅珊形象解讀》中說道:“梅珊與頌蓮是合二為一的整體,頌蓮只是一個表象,梅珊才是頌蓮的本相”。[9]也就是說,作者在寫頌蓮的時候,更是在寫另一個梅珊,他把頌蓮當成梅珊的表象來寫,梅珊作為主體,而頌蓮作為客體不斷受到主體的影響。
在與梅珊的相處過程中,頌蓮不自覺地按照對方想讓自己變成的樣子來塑造自己,也包括建構自己的欲望。“梅珊是頌蓮的情欲鏡像,是另一個被藏匿被壓制的頌蓮。”[10]梅珊毫不掩飾自己的欲望,她與醫生的偷情讓頌蓮開始對飛浦有了情欲的幻想。當她看到梅珊能夠過上“為所欲為”的生活,她的內心也是充滿著向往。當她摸著陳佐千精瘦的身體時,她的腦海中也在想著“飛浦躺在被子里會是什么樣子?”[2]34
拉康的鏡像理論說道:“主體的欲望竟然是不存在的,是一個空無。”[11]因此梅珊被投井而死,主體的消失,作為鏡像的客體頌蓮就猶如失去了靈魂一般,失去了本真的自我,只能圍繞在井邊發瘋,不停地說著“我不跳,我不跳……”[2]51。
蘇童讓梅珊與頌蓮逐漸認同對方,并通過井這個意象將兩個人的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這口井的含義預示著梅珊的死亡,同時這口井也是兩人悲劇命運的折射,梅珊的死亡,如同帶走了頌蓮的靈魂,一個身死,一個精亡,兩人一同葬送在這個象征著宗法的井里。揭示了當時女性生存狀態,無論是順從還是反抗,命運都是悲劇的。
四.結論
綜上所述,梅珊在這篇小說中雖然是一個配角,但她個性鮮明,是一個敢做敢愛、具有反抗精神的人。從低賤的身份一躍成為高貴的陳府三太太,在富足的物質生活面前卻依舊受到自身需求的驅動。在這個充滿著男權意識的社會中,這位享樂主義飛蛾撲火式的做法最終也令她走向毀滅的道路。作者筆下的梅珊是這一時期的女性代表,反映了中國傳統女性在封建家庭壓制下的宿命,在這個充滿著人性扭曲的高墻深院里,女性生存的悲慘,被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較為真實地還原了在那個時代生存的女性悲慘的命運。
參考文獻
[1]尹慧蘭.論蘇童小說女性形象塑造的描寫藝術[D].湖南師范大學,2009.
[2]蘇童.妻妾成群[M].上海文藝出版社,2004.
[3]張叢皞,韓文淑.孤獨的言說與無望的救贖——對蘇童小說的一種解讀[J].渤海大學學報(哲學 社會科學版),2005(04):12-15.
[4]亞伯拉罕·馬斯洛.動機和人格[M].許金聲,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55.
[5]韋伊.蘇童小說的空間敘事[D].華僑大學,2018.
[6]林丹婭.《當代中國女性文學史論》[M].廈門大學出版社,2003.
[7]劉小宇.論蘇童小說中的宿命觀[D].東北師范大學,2017.
[8]童慶炳.《文藝理論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9]黃田心.表象與本相<妻妾成群>中頌蓮梅珊形象解讀[J].文藝生活,2012.
[10]李昕.蘇童小說《妻妾成群》中符號的修辭闡釋[D].福建師范大學,2011.
[11][法]拉康:《拉康選集》[M].褚孝泉譯,上海三聯書店,2001.
(作者介紹:嚴燕冰,仰恩大學人文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生,研究方向:漢語言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