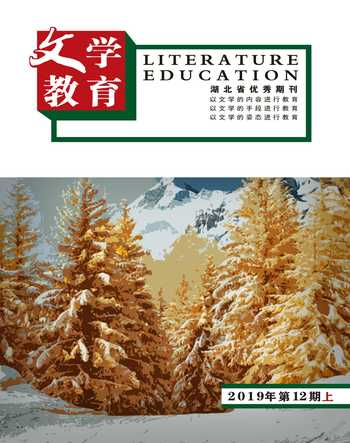從《西湖七月半》看張岱的社會理想
內容摘要:生活在明清易代之際的文人張岱,經歷過繁華與落寞從而對生活有了更加深刻的感知,通過《西湖七月半》一文,表達出對清雅之士的欣賞之情和對世俗喧囂的遠離之意,在感嘆社會變幻無常的同時,追求本真生活,率性而為,不要隨波逐流,喪失初衷,進而展現出對社會的通透理解和對人生的執著追求。
關鍵詞:《西湖七月半》 欣賞清雅 厭棄喧囂 通透
《西湖七月半》的作者張岱,字宗子,又字石公,號陶庵,又號蝶庵居士,晚號六休居士,浙江山陰人。其一生以1644年為界,前期生活在明末,出生于仕宦世家,富貴公子,生活優越,為人高傲,不同流俗;后期明亡,清兵入關,建立清王朝后,張岱拒絕為清順民,披發避居山中,布衣蔬食都難以為繼。
張岱一生落拓不羈,淡泊功名,具有廣泛的愛好和審美情趣。據其自為墓志銘中記載:“少為紈绔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 ,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
晚年雖窮困潦倒,布衣蔬食難以為繼,仍堅持筆耕不輟,安貧著書。在93歲那年病逝,著有《陶庵夢憶》、《西湖尋夢》、《瑯環文集》、《石匾書》等。
《西湖七月半》選自《陶庵夢憶》,生動地呈現了杭州人在傳統中元節逛西湖賞月的盛況,文章跳出描繪西湖美景的傳統框架,而著力寫游湖之人,從而將寫景、敘事、抒情完美結合、融為一爐。
接下來就對《西湖七月半》所蘊含的思想剖析一二。
一.欣賞清雅之士
文中將看七月半之人,作者以五類看之。其一,達官貴人:樓船簫鼓,峨冠盛筵,燈火優傒,聲光相亂,名為看月而實不見月者。一個“亂”字,充分表達了達官顯貴過著紙醉金迷的腐朽生活。一個“名”字,一個“實”字,指出了達官顯貴之名實不符、不會欣賞大自然的良辰美景。[1]其二,名門閨秀:攜及童孌,笑啼雜之,環坐露臺,左右盼望,身在月下而實不看月者。從作者對其哭著笑著鬧著,左顧右盼并不看月的動作描寫,鮮活地表現出此類人裝腔作勢、浮夸做作的丑態;其三,名妓閑僧:淺斟低唱,弱管輕絲,竹肉相發,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其四,市井之徒:不舟不車,不衫不幘,酒醉飯飽,呼群三五,躋入人叢,昭慶、斷橋,囂呼嘈雜,裝假醉,唱無腔曲,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實無一看者。這一類人出場,帶著喧囂、粗俗和痞態,毫無風雅可談;其五,清高雅士:小船輕幌,凈幾暖爐,茶鐺旋煮,素瓷靜遞,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樹下,或逃囂里湖,看月而人不見其看月之態,亦不作意看月者。
五類人雖然都月下游湖,但作者的褒貶之意溢于言表。其中名妓閑僧和清高雅士都是真正看月之人,但名妓閑僧不僅看月,意欲人看其看月,有刻意之嫌;清高雅士看月則更為風雅和純粹,遠喧囂,匿身影,從輕幌、凈幾、素瓷等字里行間明顯表達出作者對其賞月之態的欣賞之意。
不過容易忽視的是文中名為五類人,實則六類人,那就是作者之流。二鼓以后,游客盡散,吾輩與韻友、名妓同坐,東方將白,客方散去,而獨留吾輩縱舟且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此時,第五類賞月之人——清高雅士已然離去,第六類人就顯現出來了。作者分明認為,這些“韻友”雖然避俗就雅了,卻終于雅得不夠。這就是“吾輩”區別于第五種人之所在。[2]借十里荷花的純凈清香,實則烘托醉心于荷花之中的觀月之人,內心清明、恬淡內斂、氣質如荷,此才為真正的高雅,也正是作者之流的真正追求。
二.厭棄喧囂之俗
張岱生活在明末清初,是明清兩代的更迭之際,改朝換代,物是人非。從繁華富貴轉入環堵蕭然,前后生活狀態的巨大反差,不僅體現在物質方面,更重要是作者內心的波瀾。其文章大多表達對于往昔繁華景象的憶懷與追悔,反映出易代之際文人所普遍存在的留戀與傷感以及內心無法言說的掙扎。
其作品《陶庵夢憶》共八卷,寫成于明亡之后,內容大多是作者親身經歷過的雜事,以回憶的形式將種種現世之象呈現在人們面前。作者對于已過的喧囂前塵表達更多是厭棄和不屑,遣詞中寄予亡國之痛。
本文中作者不入世俗的冷淡、標榜風雅的孤高折射出厭棄喧囂世俗的真實本心和追求恬淡生活的社會理想,抒發滄桑之感,寄托興亡之嘆。
作者不入世俗,并不是標新立異,刻意為之。可從如下兩個方面進行分析:
第一,遵從本心,尚率性為之
明朝中葉后期,宦官專權,奸佞當道,黨爭酷烈;賢忠之士,遭貶逐、被刑戮;朝廷內憂外患,社會動蕩不安。與此同時,思想界涌現了一股反理學、叛禮教的思潮,主張童心本真,率性而行,這無疑是對傳統禮教的反叛,對程朱“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學的挑戰,這也正是《西湖七月半》的創作背景。
張岱在文章中對于五類人的劃分,明顯帶有標簽之意。前四類人賞月,并不是出自本意,只不過是隨波逐流、浮于形式,帶有不賞月即不入流的被動;真正的清高雅士就應遵從本心,率性而為,而非人云亦云,跟風從流,喪失初衷。
平日里,杭州人游西湖,巳出酉歸,避月如仇;是夕,逐隊爭出,多犒門軍酒錢。一入舟,速舟子急放斷橋,趕入盛會。從賞月時間前后對比,從觀月狀態的生動刻畫,作者的鄙薄之意躍然紙上。七月半游湖賞月,前四類人名為賞月,實不單純為賞月,重形式、隨潮流,盲目跟風而已,風頭一過,賞月之心也不復存在,避月如仇的心理充分顯現。這種刻意賞月的行為、隨同流俗的心理為作者所不齒。
其二,朝代更迭,傷變化無常
明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后一個由漢族建立的大一統的中原王朝,是繼漢唐之后的黃金時期,無外戚禍國、藩鎮重權,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然而即便如此,盛極一時的朝代旋即消失,1644年明朝覆滅,清朝取而代之,帶來的是作為明朝子民的扼腕痛惜和文人對于社會變化無常的無奈與慨嘆。所以再熱鬧的景象,也終不能夠長久,國破家亡之下新朝再繁華也不能激發易代之人的生活熱情。
這一點看,與生活在南北宋之交的李清照有惺惺相惜之感。李清照,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稱,婉約詞派代表。出生于書香門第,從小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為文學創作打下了堅實基礎;出嫁后與夫趙明誠共同致力于書畫金石的搜集整理。一生以南渡為界,分為前后兩期。前期,生活閑適悠然,詞作多寫閨怨離愁,詞風清麗柔媚;后期,生活顛沛流離,作品多表達懷舊悼亡之意,詞風凄婉哀怨。
李清照不僅是婉約派宗主,與蘇、辛并稱的歷史名筆,更是忠心不二的北宋臣子。金攻入東京之后擄走了宋欽宗和宋徽宗,北宋滅亡,康王趙構逃到南方,建立南宋。作為北宋臣子,李清照陷入了矛盾、糾結繼而堅定起來,詩句“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一反其婉約詞風,豪邁之情呼之欲出,雄壯之氣溢于言表。將易代之際文人的苦悶和內心的執著寄托于文字之中,更有對變化無常的社會和政治的無奈。所以,才會在《永遇樂·落日熔金》中寫出“來相召,香車寶馬,謝他酒朋詩侶。”為什么要謝客呢?一方面,內心苦悶,無心喜樂,也真的沒有辦法敞開心扉去游玩;另一方面,朝廷易代,國破家亡,物是人非,好景不長,此時出去玩樂之人絕非詞人知己,不去也罷。
所以,作者在看看月之人,既表達了對五類觀月之人的褒貶,又將自己的內心追求呈現了出來。
三.彰顯通透之意
西湖美景歷來為文人騷客所謳歌美贊的對象,“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無一不把西湖的美寫到極致,在民間“西湖明珠從天降,龍飛鳳舞到錢塘”的童謠,更是給西湖賦予了一種神秘、夢幻的色彩。
張岱僑居杭州四十余年,“水尾山頭無處不到”,熟稔西湖的山色湖光、春花秋月。[3]侵入骨髓的美景和信手拈來的熟悉,反而讓張岱跳出描寫西湖美景的框架,從另一個角度審視西湖,或者是借西湖思考人生。
不寫西湖美景,而將筆觸著力于游湖賞月之人,大有一種跳出五行外,不在三界中的味道。人人都愛西湖美景,作者卻避之而選擇寫人,變換視角重新審視,發現世界更加通透了。
轉換角度看問題,是建立在充分的熟悉和深刻的思考基礎之上的。張代經歷了易代避世,由從前的富貴安逸轉變為布衣蔬食都難以為繼的生活,恐怕對生活和周圍的人事早已經看破、看透,所以才能將游湖觀月之人從觀月之態分為五類,實在是自己內心感受的寫照和未來追求的折射。
這一點看,與北宋文豪蘇軾的《題西林壁》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蘇軾,歷經一生的宦海沉浮,將一生的功業歸為“黃州惠州儋州”,不是負氣的表現,而恰恰是看透、看通的表達。正是有了長達十一年的貶謫生活,才成就了蘇軾,也才塑造了真正的蘇東坡。
蘇軾由黃州貶赴汝州任團練副使時經過九江,游覽廬山。起初并不想再寫廬山詩,因為寫廬山之人太多,想到了大詩人李白的《望廬山瀑布》,認為已經將廬山之景寫到極致,無需再寫,但是親臨廬山之后最終還是動筆了,在廬山腳下西林寺的墻壁上寫下《題西林壁》。巧妙的是,蘇軾并沒有寫廬山美景,反而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這就帶上了深刻的人生思想了,只有站在一定的高度,親身經歷其中的變幻曲折,才能夠真正認得清、看得明。
換句話說,在《西湖七月半》中,作者張岱經歷了社會的動蕩和朝廷的更迭,看到了世間的變化無常,本就對生活有一種大徹大悟的認知,自然而然就會對世人有更加深刻的評價。故而,站在一定的高度上看看月之人,自然看出了超越于西湖美景之外的通透,那么對于世俗的冷淡,也正是內心世界的外化表現。
綜上所言,《西湖七月半》名為寫景,實則寫人。名為寫觀月之人,實則抒作者之意,清高不入俗、率性不刻意、看透不說破,張岱是也。
參考文獻
[1]張志善,《西湖七月半》講析,語文學刊,1983,(3):25
[2]翟秀、周綮,冷眼觀世態—談張岱的《西湖七月半》,語文學刊,1984,(1):24
[3]張博學,《西湖七月半》淺析,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00,(12):231
(作者介紹:王倩,齊齊哈爾工程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近代漢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