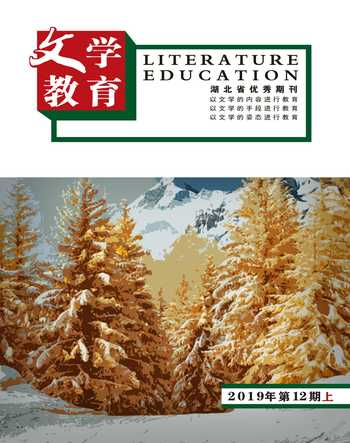論《綠山墻的安妮》中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
內容摘要:《綠山墻的安妮》是露西·莫德·蒙哥馬利創作的“安妮系列小說”中的第一部,也是其中流傳最廣的一部。《綠山墻的安妮》以加拿大愛德華王子島為背景,講述了一個生長在孤兒院的紅頭發女孩安妮,因為陰差陽錯,被馬修和瑪麗拉兄妹收養,在綠山墻農舍快樂成長的故事。《綠山墻的安妮》中彌漫著濃郁的自然氣息:自然景色、自然情感、自然和諧的兩性關系……作者的自然情懷與女性意識相結合,正暗合了生態女性主義的某些觀點,字里行間體現了作者自覺的生態意識。
關鍵詞:《綠山墻的安妮》 生態女性主義 自然 兩性關系
《綠山墻的安妮》講述了一個生長在孤兒院的紅頭發女孩安妮,因為陰差陽錯,被馬修和瑪麗拉兄妹收養,在綠山墻農舍快樂成長的故事。起初在綠山墻,安妮的生活是不順利的,因為是個女孩且性格古怪,一度處于要被退回孤兒院的尷尬境地。但這個似丑小鴨一般的女孩最終憑借著自身優秀的品格變成美麗的白天鵝。溫暖而感人的故事情節設置,使《綠山墻的安妮》成為一部世界經典的兒童文學著作并深受讀者喜歡。《綠山墻的安妮》中彌漫著濃郁自然氣息:自然景色、自然情感、自然和諧的兩性關系……作者的自然情懷與女性意識相結合,正暗合了生態女性主義的某些觀點,字里行間體現了作者自覺的生態意識。
一.安妮的自然情懷
“女性對自然界有一種認同感,以一種具體的、愛的行動與自然界相連,因此,女性更接近自然。”[2]女性與自然之間的親密聯系,自原始社會便存在著。原始社會時期的男性,更看重自然的實用性,自然對于他們而言是狩獵的場所,是展現他們男性陽剛個性的場所。而女性則不同,女性先天便擁有著良好的進一步與自然聯系的生理條件。女性擁有著同自然一般的孕育生命的能力,且擁有著關懷、同情、非暴力等特質。這種相較于男性豪放、不羈的性格特點而言,女性更加親近自然。
在《綠山墻的安妮》中,自然是安妮的朋友。安妮非但不畏懼自然,還把綠山墻的景物擬人化,把自然當作朋友。“綠山墻農舍實在是太美了……如果我出去玩了,就會和花草樹木還有小河交朋友。”[1]可愛的安妮還給她的朋友取了悅耳動聽的名字,如:把開滿鮮花的櫻桃樹叫做“白雪皇后”;把白樺樹圍成的場地叫做“悠閑的曠野”;把綠山墻果園向下延伸的小路叫做“情人小路”等。每取一個名字安妮會很高興地和身邊人分享,就好似同他人介紹朋友一般。
在小說中,自然會帶給安妮治愈的力量。安妮在與自然的相處中,同自然形成了緊密的聯系,在遇到困難時安妮會向自然傾訴,從自然中獲得治愈的力量。波伏娃曾指出:“一個孩子要是承擔過于沉重的勞動,就很可能成了一個早熟的奴隸,從而也注定了會過沒有快樂的生活。”[3]但是,安妮的精神非但沒有被沉重的生活負擔壓垮,相反她的性格越來越樂觀,其實這都是源于自然給予她的源源不斷的治愈力量。小說中,安妮因為要被退回孤兒院而感到傷心,但是這種悲傷感很快就被綠山墻農舍周圍的景物撫慰平息。“安妮醒來……她回憶起一個可怕的事實:他們并不要她,因為她不是個男孩……安妮凝視著窗外六月的早晨……她的眼睛在所有這些景物上停留很久……渾然忘卻了一切,腦子里只留下她四周的美好景物……”[1]
二.自覺的生態意識
文學的創作往往來自于生活,自然在蒙哥馬利成長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加拿大愛德華王子島是一個美麗的生態小島,島上有著濃濃的自然風光。在1874年11月30日,蒙哥馬利就出生在愛德華王子島北部的一個小鎮上。雖然生活在一個充滿詩情畫意的小島中,但是蒙哥馬利的童年生活并不完美。她兩歲時母親因肺結核不幸去世,在外從事商業的父親因無暇照顧她,小蒙哥馬利便被寄養在祖父母家中,同祖父母一起在一所老式的四周種滿綠色蘋果樹的農舍里生活。由于自小母愛缺乏,又與父親疏遠,祖父母又無法了解小蒙哥馬利內心的情感需求,年幼的她時常會感到孤獨,常常將強烈的情感需求寄托于精神世界和大自然。再加上蒙哥馬利的祖父是個熱愛自然,有著豐富詩意想象的人,蒙哥馬利曾經說過她的文學能力和文學品味是來自于她的祖父,所以自9歲會寫詩時起,她常常會將大自然的美麗記錄在她的日記當中。在牛津大學出版的露西·莫德·蒙哥馬利的日記中,蒙哥馬利對大自然充滿了喜愛之情。比如她會把愛德華王子島稱為加拿大最美的小島,并多次記錄她同家人在愛德華王子島田間快樂勞動的場景。蒙哥馬利的童年和青少年時期都是在愛德華王子島上度過的。當蒙哥馬利的父親再婚后,因為自小渴望父愛,想得到完整溫暖的家庭,她曾搬離愛德華王子島去與父親一同生活。可是熱愛自然的蒙哥馬利最終難以割舍小島的田園生活,還是選擇回到了愛德華王子島,回到了祖父母身邊。由此可見蒙哥馬利內心對自然的熱愛和依戀。
蒙哥馬利把對自然的情感帶入創作中,在小說中流露出作者自覺的生態意識。《綠山墻的安妮》在創作上帶有很強的親歷性,在作者的筆下以愛德華王子島為背景的《綠山墻的安妮》里有著漂亮的綠山墻農舍、清澈的小溪流、在枝頭唱歌的鳥兒以及多種多樣的花草樹木。“小溪的上游流經森林時,蜿蜒起伏……果園開著雪白花朵的櫻桃樹……溪邊山谷下搖曳生姿的修長白樺樹……窗口被葡萄藤染成了一片綠色”[1]美麗的自然景色使愛德華王子島充滿了生機和活力,多姿多彩,美如畫卷,令人向往。小說主人公安妮便在這處處充滿自然氣息的愛德華王子島上快樂的生活著。
從幼年時的依賴自然,到童年和青年時期的熱愛自然,再到后來的崇尚自然和依戀自然,自然對蒙哥馬利具有獨特的意義。蒙哥馬利在作品中對自然風景詩意的描寫、對家鄉簡樸生活的描繪,以及對生活在這片土地上勤勞、善良、淳樸的人民的喜愛無不體現著作者對自然田園風光的熱愛和向往。尤其是在那把自然視為生產材料的工業化時代,作者能夠主動地把對自然的熱愛融入作品當中,使作品充滿著一股濃濃的自然氣息,更加展現了作者平等和諧的自覺的生態意識。
三.女性主義生態景觀
1.人與自然
在19世紀后期,傳統的生產方式逐漸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變。自20世紀開始,人類同自然環境之間的相處方式發生了變化。由遠古時代人對自然的依賴變成工業革命時代計劃去征服自然。但是當人們為征服自然而感到驕傲的同時,自然帶給人類的處罰也隨之而至。臭氧層破壞、廢物處理、動物畜牧等等問題的出現引起了生態學的關注,一場關于環境保護的運動在世界中展開。人類中心論的環保主義者更加看重自然實用性,他們認為自然的價值取決于人類的需求和欲望。因此在機器革命的時代,人類機械化地將自然視為生產材料。對此生態女性主義者認為:“地球上的生命是一個相互聯系的網。”[2]生態女性主義是將女性主義與生態主義相結合所形成的思想流派。生態女性主義這一概念最早在20世紀70年代由法國女性主義者弗朗克斯·德·伊芙博尼率先提出,在20世紀80年代形成一種思潮,并在20世紀90年代得到快速發展。生態女性主義者主要從女性與自然之間的緊密聯系,批判了啟蒙時期所形成的價值等級觀念、二元思維方式和統治的邏輯。
蒙哥馬利在《綠山墻的安妮》中提倡人與自然建立平等和諧的關系。《綠山墻的安妮》創作于20世紀初期,這時蒙哥馬利生活的加拿大愛德華王子島正處于英國的殖民統治之下,長期的統治使資本主義在加拿大逐漸發展,現代文明開始潛移默化地改變了鄉村的世界觀念和生活方式。然而在機器生產時代下,作者在小說中依然選擇構建一個遠離戰火、與世隔絕的生態烏托邦,她筆下的愛德華王子島的人們,依然過著簡單質樸的田園生活。“自然地理環境是人類生存的基礎……它們除了能夠提供人類活動所必須的各種自然條件和……之外,還有一種非常重要的功能,即滿足人類生存的需要。”[5]愛德華王子島先天的自然環境不僅滿足著愛德華王子島島民的物質生存需要,還滿足著主人公安妮的精神生存需要。在《綠山墻的安妮》中,王子島的島民們都是忠實的衛道者,是忠誠的基督教教民。但是主人公安妮在自然中受到的關懷多于在宗教中受到的關懷。相較于信奉上帝,安妮仿佛更信奉自然。在瑪麗拉強烈地要求安妮跪下來禱告時,安妮還天真的對瑪麗拉表述了她的不解和不滿。她說:“如果我真的想禱告……我要一人出去……然后我抬頭仰望藍天……直望進那仿佛藍得無邊無際的可愛的藍天。”[1]在基督教思想中,自然被視為人類統治的對象,致使人與自然形成了分離的狀態。但在蒙哥馬利筆下的安妮的內心卻是流露著對自然的崇敬之情,這種情感不是瑪麗拉教給她的,而是安妮主觀情感的表達,她熱愛自然、崇尚自然,樂于與自然平等和諧相處。由此可見作者致力于提倡人與自然建立平等和諧的相處方式。
2.兩性關系
生態女性主義思想指出:“物種的幸存使我們看到重新理解人與自然關系的必要性,這是對自然--文化二元對立理論的挑戰。”[2]二元對立理論不但對自然造成傷害,還對女性造成了傷害。卡琳·J·沃倫認為女性已經被“自然化”,而自然也被“女性化”。譬如人們每每用“母牛”、“母狗”、“貓”等動物來形容婦女,把自然作為萬物的“母親”來敬奉時,就是把女性自然化了。而在基督教的思想下,男性被視為大自然的君主,男人有權力去支配大地上的一切生物。
換言之,男性與女性同處于二元對立的狀態。所謂的二元對立是指男性與女性處于分離的狀態,在分離的二者中男性往往會被賦予更高的價值和地位。在現實中,這種二者間的支配和屈從關系已經對婦女和自然構成了傷害。對此生態女性主義思想指出:“父權制社會的男性原則是侵略、擴張、對婦女的壓迫和對地球的掠奪,女性原則是仁愛、關心、保護和養育等,因此主張弘揚女性原則。”[2]弘揚女性原則不但可以幫助婦女和自然界,也可以幫助在父權制社會中犧牲了自己本性的男人。生態女性主義者一直在致力提倡建立一種男性與女性平等和諧友好相處的新型關系。
在《綠山墻的安妮》中,安妮打破性別屏障和男性友好和諧相處。波伏娃在《第二性》一書中寫道:“她是附屬的人,是同主要者相對立的次要者,他是主體,是絕對,而她則是他的他者。”[3]但在《綠山墻的安妮》中安妮不再是附屬者,作者借用安妮和馬修、安妮的吉爾伯特之間平等、友好交往的方式打破了傳統的男女間的不平等關系。在《綠山墻的安妮》中馬修不僅是安妮的養父,更是安妮的知己。他雖時常沉默寡言但卻是充滿愛心,馬修從來沒有用傳統的觀念去約束安妮,相反他尊重安妮,更樂于去和安妮交流和傾聽安妮內心的想法。在安妮抱怨幾何難學時,馬修會安慰她:“我想你哪方面都不錯……菲利普斯先生告訴我說你是學校里最聰明的學生……有些人說他并不是一個好教師,可我覺得他不錯。”[1]在安妮想吃醬蘋果時,雖然馬修不喜歡吃,但當安妮問他要不要時,他也并沒有拒絕,相反卻說:“哎喲,我不知道我要不要”[1],因為他知道安妮愛吃,他就會照顧她的想法。從馬修對安妮的態度可以看出,在綠山墻農舍,“女性從過去的客體轉變為主體……男性對女性的貶抑與規范已不復存在……兩性間的對話、理解取代了矛盾、沖突。”[6]與馬修的相處方式不同,安妮和吉爾伯特的相處可以說是水火不容。但看似是水火不容的關系,卻有著特殊的默契。或是因為兩人所處的奮斗環境相同,兩個人表面雖不和,背地里卻是惺惺相惜的。小說中,馬修逝世之后,吉爾伯特為了安妮主動辭掉了阿馮利學校的教師職位,愿意跑到更遠的白沙鎮去教書。吉爾伯特這一不計前嫌表現使安妮深深感動,使她為自己的局促感到深深的抱歉和懊悔,最終主動鼓起勇氣向吉爾伯特道謝。在故事的結尾,安妮和吉爾伯特都得到了彼此美好的友誼。在《綠山墻的安妮》外,作者也將安妮和吉爾伯特兩性和諧的關系延續下去,在《綠山墻的安妮》的后續小說《女大學生安妮》中他們走到了一起,并且定下了婚約。安妮和吉爾伯特的友好關系及美好結局無疑揭示了作者對美好兩性關系的向往,同時對男性與女性打破傳統束縛,建立友好新型關系必會帶來美好生活持著肯定的態度。
小說《綠山墻的安妮》,通過安妮與自然的親密接觸展示了女性與自然、人與自然、女性與男性之間的平等和諧友好關系。對成年讀者而言,通過閱讀《綠山墻的安妮》,可感知安妮的成長歷程,領會安妮獨特的人格魅力,感受書中大自然的治愈力量,會讓自己找回享受親情、友情與愛情的美好的能力,同時保持一顆熱愛自然、熱愛生活的心,努力去做一個更加貼近自然、貼近自我、具有真正幸福感的人。
參考文獻
[1]露西·莫德·蒙格馬利.綠山墻的安妮[M].馬愛農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
[2]董美珍.女性主義科學觀探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3][法]波伏娃.第二性[M].李強選譯,北京:西苑出版社,2004
[4][美]羅斯瑪麗·帕特南·童.女性主義思潮導論[M].艾曉明譯,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
[5]姜淼.《綠山墻的安妮》的文學地理學解讀[D].齊齊哈爾大學,2014
[6]戴桂玉.從《喪鐘為誰而鳴》管窺海明威的生態女性主義意識[J].外國文學研究,2005(02)
[7]李文耀.人與自然關系演變發展的歷史與思考[J].江西社會科學,1991(05)
[8]夏宗鳳,張華.從成長小說的角度解讀《綠山墻的安妮》[J].長春大學學報,2011(11)
[9]尹靜媛.從女性生態主義視角解讀《綠山墻的安妮》[J].廣西師范大學學報,2010(03)
[10]高志香.生態女性主義視角下《綠山墻的安妮》解讀[J].學園,2015(34)
(作者介紹:許海青,江蘇師范大學學科教學(語文)在讀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