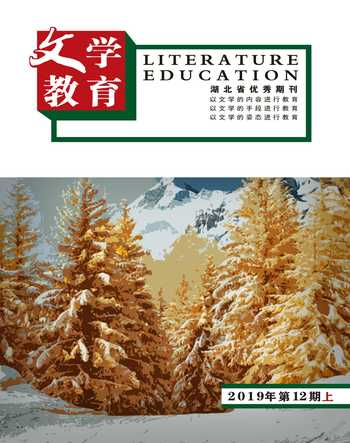從英美新批評(píng)的視角分析陳彥《裝臺(tái)》的現(xiàn)實(shí)意義
內(nèi)容摘要:《裝臺(tái)》是陳彥繼《西京故事》后的第二部長(zhǎng)篇小說(shuō),得益于作者本人二十年深入劇團(tuán)的人生經(jīng)驗(yàn),陳彥將一群裝臺(tái)“下苦人”的底層生活搬上了自己小說(shuō)的舞臺(tái)。臺(tái)上、臺(tái)下;尊嚴(yán)、卑下;誠(chéng)實(shí)、虛偽,在小說(shuō)中借由虛幻夢(mèng)境與沉重現(xiàn)實(shí)的反諷與隱喻構(gòu)成一種生命的張力,引發(fā)關(guān)于普通人如何生活的深刻思考。
關(guān)鍵詞:陳彥 《裝臺(tái)》 英美新批評(píng) 隱喻 反諷 張力
繼《西京故事》后,陳彥的第二部長(zhǎng)篇小說(shuō)《裝臺(tái)》同樣將背景放在了他所熟悉的西安,從社會(huì)底層小民眾的喜樂(lè)疾苦處下筆,在大熱鬧的浮生百態(tài)中聚焦中國(guó)傳統(tǒng)的生存哲學(xué)與生命力量。《裝臺(tái)》的故事主角是祖祖輩輩生活在西京城的刁順子,靠著肯出力吃苦,性格厚道又兼具一點(diǎn)處世必要的圓滑,順子逐漸組建起了自己的裝臺(tái)班子。陳彥的筆墨圍繞著他的家事與這一方使裝臺(tái)的老少爺們能夠養(yǎng)家糊口的舞臺(tái)展開(kāi),卻遠(yuǎn)沒(méi)有止步于此。作者通過(guò)將刁順子生活五次發(fā)生重大變革的關(guān)鍵點(diǎn)同“螞蟻意象”巧妙結(jié)合,使得《裝臺(tái)》細(xì)讀自有一番滋味在其中。
《裝臺(tái)》里兩條主線并行,如同兩路針腳般將刁順子的生活緊緊縫紉在一處:一條是刁順子在舞臺(tái)上所要進(jìn)行的裝臺(tái)工作,一條則是他不得不面對(duì)的家長(zhǎng)里短。刁順子工作的主要內(nèi)容是晨昏不分地忙于舞臺(tái)的布置,以及劇務(wù)的負(fù)責(zé)人周旋,低聲下氣服軟好話地為自己和兄弟們爭(zhēng)取更多的酬勞,舞臺(tái)上的演出再怎樣熱鬧精彩,大多數(shù)情況下也與刁順子無(wú)關(guān),而與他息息相關(guān)的小家之中上演的每日風(fēng)波,較之舞臺(tái)上的愛(ài)恨情仇也毫不遜色。難嫁的女兒菊花是順子的一大心結(jié),新娶入門的第三任妻子蔡素芬本來(lái)可以讓他在疲憊的生活中得到一點(diǎn)慰藉,但女兒同繼母之間不斷升級(jí)的真實(shí)戰(zhàn)爭(zhēng)令順子只想選擇工作受累,好從家中的緊張氛圍中逃離喘息。事與愿違,時(shí)間不僅沒(méi)能緩解菊花對(duì)蔡素芬的敵意,第二任妻子帶來(lái)的女兒韓梅因假期歸家又使家中的戰(zhàn)火愈演愈烈。在《裝臺(tái)》的文本中,反諷、隱喻以及情節(jié)節(jié)奏起到的修辭效果構(gòu)成的張力使刁順子的生活被放置在了更大的舞臺(tái)之上,從與觀眾無(wú)緣,無(wú)足輕重的裝臺(tái)人變成了被作者請(qǐng)到聚光燈下的主角,這個(gè)名為人生的舞臺(tái)所呈現(xiàn)出的正是平凡普通人的生活哲學(xué)。
一.反諷:順子的生活并不“順”
刁順子是西京城內(nèi)普通的裝臺(tái)人,可他也有不普通之處,西安城內(nèi)說(shuō)到裝臺(tái)第一個(gè)想起的就總是他,這全憑他的肯“下苦”。然而他的一生似乎沒(méi)有順?biāo)彀卜€(wěn)過(guò),順子勤快肯干,但生活中大大小小的坎兒似乎無(wú)法都用“下苦”解決,在家中,他雖為自己大女兒菊花操碎了心,菊花卻絲毫沒(méi)有替他省心一二,這唯一的親骨血反倒成為了他人生中的桎梏;在工作中,他對(duì)自己的兄弟們關(guān)照有加,但這群下苦人也給他惹了不少麻煩;甚至除去這些人,連刁順子家的一條瘸腿狗,都能引發(fā)一場(chǎng)大戰(zhàn)。小說(shuō)圍繞刁順子展開(kāi),順子身邊的人和所經(jīng)歷的事都帶著一些對(duì)應(yīng)的意味,仿佛鏡子的兩面,一面是美好的愿景,一面是不如意的現(xiàn)實(shí)。從小說(shuō)的發(fā)展中,可以提取的對(duì)應(yīng)例子很多,比較典型的可以舉出三個(gè):美貌的韓梅——容貌不佳的菊花、佛像的圣潔——世俗的玷污、名叫好了的狗——人面桃花中的“狗”。
順子有過(guò)三場(chǎng)婚姻,第一場(chǎng)婚姻的對(duì)象貌美輕浮,留下菊花后在臘月初八和人私奔,而菊花的相貌沒(méi)有隨她娘那般姣好,反而隨了平平無(wú)奇的刁順子,有些過(guò)分“扁平”。第二任妻子趙蘭香善于操持,帶來(lái)的女兒韓梅也同母親相像,容貌出眾。菊花和韓梅的關(guān)系在童年時(shí)期相處融洽,失去母親的菊花很高興繼母的到來(lái)帶給了她樸拙的父親所不能提供的母愛(ài),也因有了韓梅作為姐妹和玩伴,消解了一些父親忙于裝臺(tái)工作無(wú)暇顧及自己的孤單。但隨著趙蘭香的去世,韓梅的逐漸長(zhǎng)大,菊花的心性逐漸扭曲,二人間從融洽逐步走到針?shù)h相對(duì)的局面。同為順子的兩個(gè)女兒,韓梅和菊花似乎從表到里都截然相反,菊花是刁順子的親生女兒,她的母親留給順子的是不如人意的回憶甚至來(lái)自鄉(xiāng)鄰眼光的恥辱,而韓梅雖然不是順子的骨肉,但她的母親趙蘭香在的那幾年可以說(shuō)是順子人生中難得的踏實(shí)日子,鄰里夸贊有加。這一對(duì)姐妹倆相貌美丑,在讀書(shū)上的才能甚至在愛(ài)情上的際遇都似乎是鏡子的兩面,菊花因容貌不佳一直沒(méi)有對(duì)象,使得她對(duì)于自己的相貌越發(fā)在意,高考落榜后自己開(kāi)的美容店也沒(méi)有起色,于是將一切歸結(jié)到父親的無(wú)能上;韓梅容貌姣好,在商洛讀大學(xué)的期間還結(jié)識(shí)了作為同學(xué)的男友,她對(duì)刁順子這個(gè)繼父感恩的情緒更多。但這二人卻并非毫無(wú)相似之處,刁菊花與韓梅的共同點(diǎn)在于她們都讓刁順子勞心勞力,苦不堪言。韓梅為了留在西安城內(nèi)拼命守衛(wèi)自己在二樓的一間房間,而菊花傾盡全力要將“自己以外的所有女人”從他無(wú)能的父親的房子里趕出去,兩人都在宣誓自己的主權(quán),甚至發(fā)生了兩次爭(zhēng)打和血淋淋的殺狗事件。菊、梅、蘭、芬刁順子生命中最親密的女人名字中都充滿花香,但無(wú)論美丑,性格緩急,出于本心還是天意,都沒(méi)能把他的生活點(diǎn)綴得更加精彩,相反帶來(lái)了無(wú)數(shù)的痛苦折磨。刁菊花的所作所為固然并不討喜,作為菊花反面的韓梅,也無(wú)法使人感到美好和安慰,作者通過(guò)完全相反的姐妹二人道出了某種無(wú)奈的真理,丑惡的對(duì)立面總是被冠以美好的希冀,但往往美好并不等在那里。
寺廟,神佛,這些本該在香客們虔誠(chéng)地香火中煙霧繚繞的意象有時(shí)也并不慈悲。順子在經(jīng)歷了為《金色田野的頌歌》節(jié)目裝臺(tái),卻遇上了詐騙撈錢的草臺(tái)班子,一無(wú)所獲后,經(jīng)劇團(tuán)的劇務(wù)寇鐵介紹,為寺廟活動(dòng)進(jìn)行一次裝臺(tái),以期能稍加得到資金補(bǔ)償,盡快為兄弟們發(fā)下工錢,然而在寺廟這種“圣潔所”,裝臺(tái)兄弟中的墩子卻做出了不潔事,被僧人們發(fā)現(xiàn),墩子早已先行逃走,順子代為受過(guò),在佛堂中苦跪一晚。被玷污的菩薩像看起來(lái)和順子的第二任妻子趙蘭香長(zhǎng)得很是相像,這是順子悄悄在心里想?yún)s不敢告訴任何人的秘密。菩薩在尋常人眼中,常常是一種寄托,去廟中進(jìn)香的香客,也通常是對(duì)著“救苦救難”的菩薩禱祝祈求,以期讓自己的生活產(chǎn)生一些良好的改變。趙蘭香的到來(lái),對(duì)順子而言,似乎也具有這種意味,她的加入了順子的家庭,那幾年中是順子少有的衣服頭臉整潔,趙蘭香持家有數(shù),手巧人勤,也給予了菊花母親般的溫暖和關(guān)懷,可以說(shuō),她對(duì)于這個(gè)家所做的一切,稱得上是救其于水火。諷刺的是,這種仿佛美夢(mèng)般的“神跡”并不持久,很快趙蘭香的病逝使刁順子的家更加風(fēng)雨飄搖,就如同寺廟中給人以美夢(mèng)安慰的菩薩,眉目下垂,看似大慈大悲,卻給順子帶來(lái)了皮肉之苦,就要到手的工錢也就此泡湯,甚至是寺廟中本該六根潔凈的出家人,行事也勢(shì)利而跋扈,這種反差和對(duì)比下,順子依舊從“菩薩”中得到了對(duì)生活的信心和安慰也就變得更加使人感到唏噓悲痛。
順子家分崩離析的導(dǎo)火索來(lái)自菊花的“殺狗事件”,這條名叫“好了”的狗是趙蘭香留下的,對(duì)她的女兒韓梅來(lái)說(shuō)意義非凡,對(duì)剛進(jìn)入家門,備受菊花針對(duì)排擠,順子無(wú)奈忍讓而內(nèi)心頗感委屈的蔡素芬而言,好了也曾給過(guò)她一絲安慰。好了是一條狗,雖然名叫好了,卻一直拖著一條斷腿,小心翼翼地察言觀色,只敢對(duì)韓梅撒歡撲撞,雖然蔡素芬將它抱在懷里連聲念著它的名字時(shí),或許也期待一切都會(huì)像好了的名字一樣,慢慢變好,但直到她離開(kāi)這個(gè)家,一切也沒(méi)有真正好轉(zhuǎn),所有人的關(guān)系依舊緊張,好了也最終被菊花殺死,徹底斷了它這個(gè)討口彩的名字所能帶來(lái)的幸福期望。好了生就一條狗,犬生凄苦,順子生為人身,卻在扮演一條狗中達(dá)到了人生巔峰。《人面桃花》匯演中,因演員臨時(shí)無(wú)法到位,順子客串出演了在女主人公身邊的一條狗,在扮演一條狗的過(guò)程中,順子嘗到了從未體會(huì)過(guò)的掌聲和鮮花,甚至輕松順利地拿到了工錢,在劇情中這條由人扮演的狗同樣死亡,但不同于好了的死,順子在扮演這條狗死亡的過(guò)程中,感到快樂(lè)無(wú)比。名叫好了的狗,由人扮演的狗,兩起死亡,臺(tái)上的是美好的愿景,臺(tái)下的是血淋淋的現(xiàn)實(shí)。
二.隱喻:從物到人
從素芬來(lái)到家中起,順子見(jiàn)過(guò)五次螞蟻搬家,第一次是素芬剛來(lái)的夜晚,順子發(fā)出了自己與螞蟻同樣疲于奔命,信命安命的感慨;第二次則是帶素芬同去城郊為《金色田野的頌歌》進(jìn)行裝臺(tái),二人坐在田埂上,只覺(jué)得鄉(xiāng)郊的螞蟻比城里的更大,托的物體更重,更要硬抗著生活;第三次是菊花與韓梅發(fā)生沖突,用開(kāi)水燙死正在搬家的列隊(duì)螞蟻;第四次與前幾次有所不同的是,順子先做了一個(gè)夢(mèng),夢(mèng)中他也變成了螞蟻,同螞蟻一起奔波生活,醒來(lái)再次看見(jiàn)螞蟻搬家;最后一次見(jiàn)到螞蟻,是在尾聲部分,順子心態(tài)平衡,覺(jué)得托著重物的螞蟻們走得很有尊嚴(yán)。
螞蟻?zhàn)鳛橐粋€(gè)典型意象,在整部小說(shuō)中反復(fù)地出現(xiàn)。第一次代表的是素芬來(lái)到家中,生活雖苦,但順子秉持一直以來(lái)的“下苦”信條,安于此道,決心兩人一起在忍耐中,將日子過(guò)得有些聲色。第二次在鄉(xiāng)郊則是二人關(guān)系的蜜月期,順子在西安城內(nèi)土生土長(zhǎng),甚至對(duì)鄉(xiāng)郊的更為辛苦的“螞蟻”抱有同情,這也是最后一次二人一起觀看螞蟻,自此之后,菊花殺狗逼走韓梅,燙死螞蟻,素芬不堪忍受菊花的折磨,再也無(wú)法像螞蟻一般忍耐,就此離開(kāi)順子,也迎來(lái)了全書(shū)中最為關(guān)鍵的一次螞蟻描寫(xiě)——順子的蟻夢(mèng)。
這個(gè)故事其實(shí)并不令人感到陌生,人變成了螞蟻飽嘗悲歡榮辱大起大落,唐代李公佐在《南柯太守傳》中就已經(jīng)寫(xiě)過(guò)。螞蟻的意象,在此時(shí)與南柯一夢(mèng)的典故自然地關(guān)聯(lián)在了一起,有趣的是順子的蟻夢(mèng)同南柯太守的正好形成了一組對(duì)比。淳于棼夢(mèng)中螞蟻?zhàn)冏髁巳耍谄渲邢肀M人生跌宕起伏,好事多過(guò)壞事,而順子的夢(mèng)中,人變作螞蟻,除卻勞作,便是風(fēng)險(xiǎn),壞事多過(guò)好事,南柯國(guó)王一年之約,淳于棼魂歸蟻國(guó),而順子在大夢(mèng)方醒后,卻是回歸到依舊波折不已的現(xiàn)實(shí)生活中去,回歸到他的位置上,去做那一班同是下苦人兄弟的支柱,領(lǐng)頭人,繼續(xù)硬扛著生活。
夢(mèng)境與現(xiàn)實(shí),臺(tái)上與臺(tái)下,如果說(shuō)舞臺(tái)是一場(chǎng)美好的大夢(mèng),上面上演著美化過(guò)的悲歡離合,那么臺(tái)下的現(xiàn)實(shí),最深有體驗(yàn)的莫過(guò)于順子等與舞臺(tái)無(wú)緣的裝臺(tái)人。大幕一旦拉開(kāi),意味著表演就要開(kāi)始,也意味著順子等人的裝臺(tái)工作已經(jīng)完成,就要退出不屬于他們的舞臺(tái)。順子夢(mèng)醒回歸現(xiàn)實(shí),便是從夢(mèng)境的聚光燈下,回到了屬于自己的臺(tái)下,他是西安城內(nèi)的小人物,同他一樣的小人物數(shù)不勝數(shù),就像他在蟻群中所見(jiàn)的成群結(jié)隊(duì)的螞蟻,他們經(jīng)受苦難,但互相扶持拉扯,他們的舞臺(tái)在于臺(tái)下,在生活之中,順子對(duì)此有所領(lǐng)悟,故而感到一種莊嚴(yán)自持的驕傲與滿足,才會(huì)在小說(shuō)的結(jié)尾處,覺(jué)得如果導(dǎo)演看見(jiàn)了緩慢行進(jìn)的蟻群,會(huì)要求為它們打上聚光燈束。關(guān)于螞蟻含混的隱喻落到現(xiàn)實(shí)之中,現(xiàn)實(shí)的重量將看來(lái)虛幻縹緲的含混拉扯進(jìn)泥土,得以生長(zhǎng)出小人物的生活哲學(xué)。
三.張力:從瑣事到巧合
俄國(guó)形式主義將情節(jié)視為修辭功能的一種,在《裝臺(tái)》中,情節(jié)的節(jié)奏傳達(dá)出這樣的情緒:《裝臺(tái)》的故事中,主人公的生活并不順利,稱不上遭受大風(fēng)大浪,但也是坎坷無(wú)比,就這樣苦熬度日,內(nèi)心麻木而疲憊,又帶著一種未開(kāi)化般的野蠻生命力量。與這樣的表達(dá)主題相契合的是整部小說(shuō)的敘事節(jié)奏,在情節(jié)的安排上,從頭到尾充滿小波折。
順子的生活從來(lái)不順,小說(shuō)開(kāi)頭第一頁(yè)的短短篇幅中,就已經(jīng)是焦頭爛額,劇團(tuán)的工作忙得人焦頭爛額,已經(jīng)是“兩頭不見(jiàn)天兒”,倉(cāng)促娶了新妻,還沒(méi)進(jìn)門,女兒已經(jīng)在指桑罵槐地宣示主權(quán)。順子感到對(duì)女兒愧疚,選擇隱忍,新來(lái)的女主人也感到委屈,小小的院落中人跳狗叫,碗盆摔做叮當(dāng)亂響。故事從一開(kāi)篇就將讀者帶入進(jìn)一種焦慮的情緒之中,但作者筆鋒一轉(zhuǎn),又給這根擰緊的弦松上了一松。蔡素芬的到來(lái)并不全給順子和整個(gè)家庭帶來(lái)了戰(zhàn)爭(zhēng)一觸即發(fā)的緊張氣氛,對(duì)順子來(lái)說(shuō),這個(gè)女人使自己又重新感受到了年輕和活力,燃起了他對(duì)生活新的向往。讀者剛剛從壓迫感中找到了喘息的空間,菊花在窗外對(duì)正與新婚妻子溫存的父親的謾罵又再一次將順子和讀者一起拉扯回了緊張的空氣中。
全書(shū)在這樣反反復(fù)復(fù)的拉鋸中行進(jìn),波折之間的聯(lián)系強(qiáng)度卻不過(guò)大,如同順子的隱疾一直拖延就醫(yī)般拖拽著推進(jìn),給讀者帶來(lái)一種強(qiáng)烈的疲憊感,在這種感覺(jué)中放大了順子對(duì)于生活的逆來(lái)順受,又在讀者已然形成了期待視野,認(rèn)為順子的人生難以發(fā)生太大改變時(shí),通過(guò)順子不堪忍受寇鐵的欺壓,一改往日的唯唯諾諾服軟遞話,前去強(qiáng)硬討要工錢,在此之前他已經(jīng)去寇鐵家中拜訪了三次,每次的態(tài)度都幾近軟弱,按順子的觀點(diǎn),“這么多年來(lái),他就是用自己的低下,可憐,甚至裝孫子,化解了很多矛盾,解決了一個(gè)又一個(gè)不好解決的問(wèn)題”。但到了最后,真正使他拿到被拖欠已久的工錢的,卻是他難得的強(qiáng)硬。
順子是西京這個(gè)古老的大城市中最底層的普通人,與他的小學(xué)同學(xué)相比,他也算混得不上不下,但在他小學(xué)老師眼中,這個(gè)平凡的學(xué)生是幾十年來(lái)唯一還記得每年登門拜望的孩子,他雖然平凡,甚至被生活逼迫的有些懦弱,卻絕不卑微,靠本事吃飯,堂堂正正。同小學(xué)老師的兩次拜訪對(duì)話,暗中使順子這個(gè)人物在讀者眼中的形象發(fā)生了改變,在生活苦難的稻草一根根落下時(shí),駱駝不僅沒(méi)有被壓垮,反而從在苦難中的堅(jiān)守過(guò)程中,找到了自己人生的尊嚴(yán)。在這個(gè)敘述過(guò)程中,情節(jié)變成了構(gòu)成張力的手段,而對(duì)情節(jié)節(jié)奏的出色控制則是張力得以實(shí)現(xiàn)的重要原因。
四.結(jié)語(yǔ)
我們給予平凡者目光的時(shí)候并不多,能夠?qū)⒁暰€落在普通人身上投入筆墨的作者也不多,舞臺(tái)上的戲固然好看,但實(shí)際上演悲歡離合的舞臺(tái)總是生活。反諷,隱喻,這些手段構(gòu)成的張力實(shí)際上來(lái)自于普通人對(duì)于生活的各自感悟,讀來(lái)才能知其味,解其意。普通人在苦難生活中的“下苦”,往往正是其人格光輝的體現(xiàn),莊嚴(yán)自持的堅(jiān)守,值得任何一盞聚光燈的照射和凝視,以及為之自豪。南柯太守可以一夢(mèng)了之,作為普通人的一份子,總難成夢(mèng),夢(mèng)醒后如何有尊嚴(yán)地活著,才是值得思考的問(wèn)題。
參考文獻(xiàn)
[1]陳彥.裝臺(tái)[M].作家出版社.2015.
[2]徐翔.戲臺(tái)邊上的悲喜人生———論陳彥《裝臺(tái)》的底層書(shū)寫(xiě)[J].西安建筑科技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 2017(0).
[3]曹順慶,盧康.中國(guó)話語(yǔ)”重建的文脈——以當(dāng)代西方文論在中國(guó)的研究情況為視角[J].中外文化與文論.專欄一.
[4]李曦朦.韋勒克文學(xué)架構(gòu)的理論來(lái)源和對(duì)英美新批評(píng)的超越性發(fā)展[J].文教資料.2018(36).
(作者介紹:王夢(mèng)楚,溫州大學(xué)人文學(xué)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學(xué)理論及文藝批評(pí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