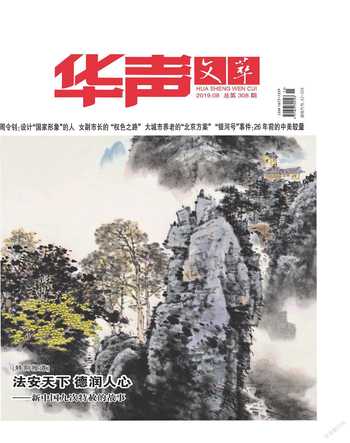揭秘層出不窮的騙醫保手段
病床只有10張,同時“住院人數”卻有136人;一年“被檢查”8次,有7次是假的;1000多元錢的小手術做到一半,手術臺上的人被告知有生命危險,結果加價到兩萬多元;有人去世已有5年,但還在人間兩次報銷“住院費”……記者近期調查發現,不少地方醫療機構騙取醫保資金的現象屢見不鮮,還有個別監管人員與之“里應外合”。層出不窮的騙保手段花樣不斷翻新,成為啃食救命錢的社會毒瘤。
當田淑芬(化名)走進一家民營醫院時,她沒想到自己竟然將成為一名癌癥患者。一番煩瑣檢查后,這家醫院下了一份診斷。主治醫生告訴她,病情很嚴重,如不住院治療會變成子宮癌。
于是,原本只是患有普通婦科炎癥的田淑芬在這家醫院花了3萬多元的治療費。更讓她意外的是,醫院在給她治療時,同時還索取了田淑芬本人及3名家人的身份證、戶口本、合作醫療卡等證件,醫院利用這些證件虛構診療信息,從縣醫保部門騙取了醫保資金6000多元。
和田淑芬一樣經歷“陡然病重”的人還有不少。李軍(化名)到一家縣民營醫院做簡單的包皮手術,手術前被醫生打了一針藥物后,身體出現了不良反應。躺上手術臺后,他被醫生告知這是囊腫瘤,危害很大,需要增加手術費用。于是,他被連恐帶嚇地多支付了費用。
看似為患者著想,實際卻是借診療為名將手伸向了醫保基金……今年以來,山東、廣西、安徽、重慶等省區市或下轄地市對此類欺詐騙取醫保基金的行為開展集中打擊行動,披露了一批典型案例。
在中部某省,辦案人員對一家民營醫院涉嫌騙取醫保資金檢查時,甚至發現了“死人住院”的現象。一家民營醫院的報賬資料顯示,吉華霜(化名)在2016年7月至9月先后兩次到該院住院報銷,而實際上她已在2011年5月離世。
不僅是騙病人,一些醫療機構為套取醫保資金,還在賬目上“騙自己”,更騙監管部門。一些醫療機構在治病過程中通過“陰陽處方”開出高價藥,實際使用普通藥,以此騙取醫保資金。如有的醫生實際治療患者使用一套處方,醫保報賬使用另一套用藥更貴的處方。中部省份某地在檢查中發現,有的醫院用國產每支2.8元的針劑冒充進口藥,以每支38元的價格給患者使用;有的醫院將患者自費藥品換成可報銷藥品,騙取醫保資金近16萬元。
記者調查發現,一些地區的醫療機構、監管部門工作人員和部分患者之間形成了一條騙取醫保資金的灰色利益鏈條,不斷地啃食群眾的救命錢。部分地區民營醫院成為騙取醫保的重災區。中部省份某地在調查中發現,有以福建莆田系為主的多家民營醫院通過醫保報賬近8000萬元,其中騙取醫保資金1500余萬元。實際上,一些民營醫院雖然冠以不同的名字,但卻隸屬于一個控股方,穿上“不同的馬甲”在多個縣市注冊非營利性機構,實施醫保資金詐騙。
多名查辦騙取醫保資金案件的人員認為,加強對醫保資金使用的監管十分重要,對相關制度“查缺補漏”刻不容緩。
一方面,有的職能部門不同程度給鄉鎮衛生院下達分配保底盈利目標,達不到目標便從撥付各鄉鎮衛生院的工作經費和人員工資中扣除。另一方面,監管仍存在較大的不足。據介紹,醫保基金管理涉及衛計、醫保、物價、市場監管等多個部門,管理鏈條較長,部門之間協作機制不暢。
此外,當前對詐騙醫保行為的處理力度偏輕。據辦案人員介紹,相關職能部門對存在違法騙取醫保資金行為的醫療機構往往采取核減一定數額補償資金、罰款整改、暫停報銷等方式處理,但未及時將其清理出醫保定點單位。
同時,國家醫保局將全面提升醫保基金監管水平,包括建立“該發現的問題沒發現是失職、發現不處理是瀆職”的問責機制,堅持“零容忍”態度,對違法違規行為,發現一起,查處一起,加快建立基金監管長效機制,加快醫保監管立法,完善智能監控體系,實行部門聯動等。
清華大學醫院管理研究院教授楊燕綏建議,建立全程智能審核監控制度和全國統一的醫保基金監督制度,建立覆蓋醫療機構、醫務人員、藥品供給商、參保患者的信息系統,建立大數據分析系統,一旦發現異常立即啟動檢查;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建立專業執法機構,做到違規違法必究,提高犯罪成本。
(摘自《新華每日電訊》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