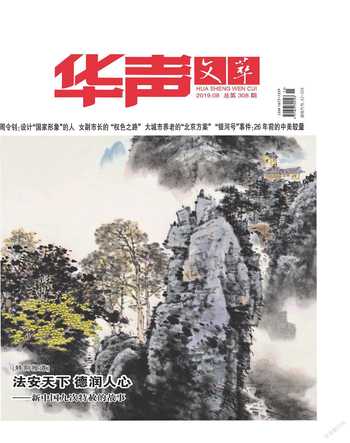劉少奇長孫:“中國是父親,俄羅斯是母親”
阿廖沙 崔雋
阿廖沙,中文名劉維寧,1955年出生于莫斯科,系劉少奇長孫。阿廖沙的父親劉允斌14歲時前往俄羅斯求學(xué),結(jié)識俄羅斯姑娘瑪拉并結(jié)婚,育有女兒索尼婭和兒子阿廖沙。阿廖沙曾在蘇聯(lián)航空航天局工作。2003年第一次來到中國,2007年定居廣州,2010年創(chuàng)辦俄羅斯亞洲工業(yè)企業(yè)家聯(lián)合會。下文是作者據(jù)阿廖沙的口述整理。

接到祖父劉少奇的來信時,父親剛剛獲得莫斯科大學(xué)核物理專業(yè)副博士學(xué)位。祖父在信中說,國家需要留學(xué)生們回來服務(wù),希望父親早日歸來,用所學(xué)回報祖國和人民。
這是一個兩難的選擇。父親舍不得這個溫馨的四口之家,可他曾立志絕不辜負(fù)人民的培養(yǎng)。學(xué)有所成,報效國家,這是他人生的意義。
父親回國時我才2歲,所以我對父親的記憶,大多是通過照片、信件還有母親的講述拼湊的。
父親回國后,被分配到中國原子能科學(xué)研究院工作,他常常把工資換成盧布寄給母親,補(bǔ)貼家中開銷,并寫信到莫斯科,表達(dá)他對我們的愛意。
這些信件我都完整保留著。信的內(nèi)容大多數(shù)是父親講自己回國后的日常生活,某天吃了什么,做了什么,很瑣碎但很溫暖。在問候母親之后,他一定會詢問我們的學(xué)習(xí)和成長。印象最深的是父親對我們說,和取得個人成就相比,能為國家和民族奉獻(xiàn)自身才是最大的幸福。長大后,我才明白,這應(yīng)該就是他的信仰。
在長期的分離中,父親和母親不得不決定結(jié)束婚姻關(guān)系。隨著兩國關(guān)系的變化,父親與我們的書信往來也被迫中斷,一家人從此失去了聯(lián)系。
1960年,中蘇關(guān)系公開交惡。就在此時,年幼的阿廖沙見到了為緩和中蘇關(guān)系而專程來訪的祖父劉少奇。
一天傍晚,家門前來了一輛氣派的黑色轎車,母親說要帶我們?nèi)ヒ娨晃婚L輩。車子把我們接到一棟建筑里,在那兒我見到了一位身材高大、頭發(fā)花白的老人。母親說,這就是我的祖父。祖父見到我很高興,摟住我,親了親我的臉頰。
祖父給我?guī)砹送婢吆吞枪步o外公外婆帶了禮物——一套印著中國山水畫的煙具和一幅繡著老虎的絲綢畫。他還對母親說:“生活上有什么困難時,可以通過中國駐蘇大使館尋求幫助。”沒想到,這會是我和祖父唯一一次親近的見面。
1979年,我開始在蘇聯(lián)航空航天局任職,那正是蘇聯(lián)航天發(fā)展的好時期。我參與了人類首個可長期居住的空間研究中心——“和平號”空間站的發(fā)射工作。后來我成為蘇聯(lián)國家航天指揮中心的高級工程師。
1987年,姑姑劉愛琴費(fèi)了很大工夫,從她的莫斯科同學(xué)那里打聽到我們的下落,失散多年的親人終于聯(lián)系上了。也是在此時,我們從中國朋友那里聽說父親早在1967年就去世了。
上世紀(jì)60年代,父親在內(nèi)蒙古包頭的二○二廠工作,并組建了中國第一個熱核材料研究室。當(dāng)蘇聯(lián)停止對中國的技術(shù)援助時,父親帶領(lǐng)科研人員自力更生,踐行著他為國奉獻(xiàn)的信念。然而,隨著“文革”的開展,他在痛苦和彷徨中選擇了自殺。現(xiàn)在越了解歷史,越知道父親是個先行者,他堅信自己的信仰和方向是正確的。他的死是那個時代的悲劇。
1998年祖父劉少奇100周年誕辰時,王光美奶奶委托中方向我發(fā)出了邀請函,希望我可以參加。這在當(dāng)時引起了很大轟動,我的同事們得知后都非常驚訝,相關(guān)部門也找我談話,向我提出了很多問題。因為我當(dāng)時是在職軍官,出國前要走復(fù)雜的審批流程,最終我遺憾地錯過了這次紀(jì)念活動。但這件事情過后,我內(nèi)心有一個念頭越來越強(qiáng)烈,那就是一定要去中國看看祖父生活的地方,一定要親手給父親掃墓。
為了能早日去中國,我申請了提前退役。按照規(guī)定,退役5年后才能自由出行。這段時間里,我和妻子冬妮婭做足了功課,試圖從各個方面了解中國。我還在莫斯科找了一位中文老師,認(rèn)真學(xué)習(xí)中文。
2003年,我終于來到中國。在北京,我見到了王光美奶奶。剛一見面,她就給了我一個擁抱,盡管當(dāng)時我已經(jīng)是一個中年人了,但還是感受到了來自長輩的溫暖。
在后續(xù)的旅程里,我去了中國很多城市。在湖南寧鄉(xiāng),我拜訪了祖父的故居,那里也是父親度過10年童年時光的地方。在南京雨花臺,我為父親的生母何寶珍奶奶敬獻(xiàn)了花圈。
此后幾年間,我來中國的次數(shù)越來越多,發(fā)現(xiàn)最喜歡的城市是廣州。于是,我們一家人決定在廣州定居生活。
曾經(jīng)有人問阿廖沙,中國和俄羅斯到底哪個是你的家?阿廖沙的回答是:“其實(shí),俄羅斯和中國都是我的祖國。在俄羅斯居住時,我沒覺得自己離開了中國,如今在中國生活,我也不認(rèn)為我離開了俄羅斯。俄羅斯是母親,中國是父親,不管何時何地,它們都是我的家。”
(摘自《環(huán)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