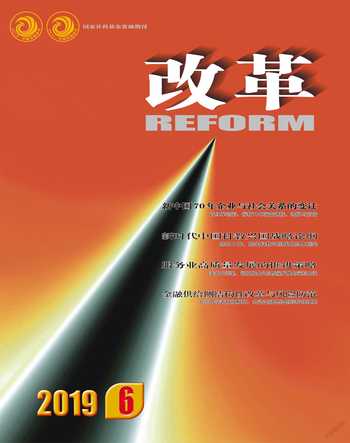新中國70年城鄉關系演變及其啟示
邢祖禮 陳楊林 鄧朝春
內容提要: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城鄉關系歷經曲折,探討城鄉關系演變邏輯可為把握未來城鄉關系取向提供線索和啟示。1949~1952年,我國城鄉關系基本處于自然發展狀態;1953~1978年形成了城鄉“二元分割”格局,農業農村為城市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1979~1985年城鄉關系趨于緩和,農業農村得到快速發展;1986~2005年隨著“發展型政府”的興起,城鄉關系產生了分離;2006~2011年國家決心遏制和改變分離狀態,將城鄉一體化作為一項長期任務來推進;2012年以來,中央高度重視城鄉關系調適,城鄉關系進入融合發展的新時代。我國城鄉關系的實質是國家與農民的關系,國家戰略和政策取向對城鄉關系演化有重要影響,市場化在城鄉關系中扮演著“雙刃劍”角色,應在重構國家與農民政治經濟關系的前提下協調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從而實現新時代城鄉關系的融合發展。
關鍵詞:城鄉關系演變;城鄉一體化;城鄉融合發展
中圖分類號:F120.2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3-7543(2019)06-0020-12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現階段,城鄉關系之間不平衡、農業農村發展不充分已成為我國現代化進程的障礙。如何克服這個障礙,成為新時代理論研究和政策實踐的焦點問題。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正是國家在戰略層面上對這個問題的回應。以往研究文獻大多注重城鄉關系演變過程中的數量特征,而本文著重從理論邏輯角度,對新中國70年我國城鄉關系的演變歷程進行梳理,以期從中發現國家政策與我國城鄉發展之間的深層次邏輯關系,為更好解決城鄉之間不平衡問題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供相關建議。
一、1949~1952年:城鄉關系的自然發展狀態
新中國成立初,我國通過土地改革、取消帝國主義在華特權、沒收官僚資本和“三反”“五反”運動,將舊時代的經濟改造成為包括國營經濟、集體經濟、私營經濟和個體經濟并存的“混合經濟”。這種“混合經濟”具有典型的農業社會形態特征。1952年,我國農業凈產值占工農業凈產值的比重高達74.7%,而且就業人口中占83.5%的農業勞動者分散在廣袤的土地上從事小農生產和家庭副業或手工業經營[1]。當時的城鄉關系既包含著國家與農民之間的利益關系,又包含著農村與城市之間的自然演變關系。
(一)農村支援城市
新中國成立初,為了鞏固新生政權、穩定物價、恢復和重建國民經濟,我國對糧食、棉花、油料、肉類等重要農副產品進行大量征購,以滿足軍隊和城市居民的基本需求;同時鼓勵私營商業參加城鄉貿易交流,滿足居民特別是城市居民的多樣化需求,使城鄉經濟逐漸活躍并得到了充分的發展。農民為新中國的國民經濟恢復和持續發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除了國家利益取向的考慮外,就純粹經濟學觀點來看,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是一個典型的農耕社會,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在緩慢演化,城鄉關系也處于劉易斯所說的“二元經濟”自然狀態當中[2],工業化和城鎮化也在自然演進,農業農村為城市工業提供勞動力、原(材)料和原始資本積累。由于農業社會勞動分工程度低,生產技術落后,農民家庭生產的農副產品交納稅費,留下滿足自身家庭需求后,只有少量余額進入集市貿易或城市貿易。農民對城鎮工業產品的需求量不大,不易形成發展工業所需要的資本積累。更為重要的是,農民家庭所需的部分生活資料(如衣服、燃料、肥皂等)以及部分生產資料(如農具、肥料、運載工具等)都通過家庭手工業或副業自行提供,減少了對工業產品的依賴,這在相當程度上限制了工業的發展和規模。
這一階段,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資料(如糧、棉、油、肉等農副產品),均由國家通過征購方式從農民手中得來,再通過國營和集體性質的批發零售渠道提供給城市居民,城市所需要的其他消費產品和生產資料,則由自由市場提供,這種自由市場的機會為城市周邊的農村所利用,它們飼養家禽、種蔬菜、養魚,發展城市所需各類事業以獲得利益,當然這種利益由于交易費用的限制不能夠擴展到更廣大的農村地區,特別是偏遠的農村地區。總之,城市工業產品(含手工業產品)和服務業大多在城市內部自行運轉,城市銷售給農村的工業產品僅限于火柴、食鹽、糖果、洋布、洋油、鐵制農具等少數產品,限制了城市工商業的發展和規模,使得城鄉之間呈現“二元經濟”結構特征,城鎮化處于自然演進過程。
(二)平等的城鄉關系
這一階段,城鄉關系典型特征非常集中地反映在工農產品價格關系和生產要素是否自由流動兩個方面。此時國家管制和政策性干預力度比較小,國營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不占明顯優勢;雖然對私營和個體工商業在某些領域有所限制,但在更多的領域是扶助和鼓勵。
除少數重要農副產品和工業產品外,大多數工農業產品的價格都是競爭性的市場價格。馬克思認為,商品交換關系實質上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工農產品之間的關系就是城鄉居民之間的關系,它體現出等價交換原則,這既得益于國家對“混合經濟”的保護,又得益于眾多微觀經濟主體自由競爭,因此城鄉關系總體上是一種平等關系。
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是自由流動的。在此期間,我國農民獲得了充分的選擇自由,經濟學中關于生產要素配置的四個基本問題(生產什么?如何生產?為誰生產?誰作決策?)都由農民自己來回答;同時這種選擇自由還反映在生產要素的空間配置上,這就涉及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的流動,國家此時沒有限制農民的就業自由,城市勞動者的工資是競爭性均衡的工資,新舊工人或新舊居民“同工同酬同待遇”,這是由市場力量決定的。國民經濟的恢復吸引了大量農民流入城市就業,他們從事工業制造、手工打磨、商業批發零售、交通運輸、沿街叫賣等各行各業。1950~1952年,城鎮人口由5765萬人增加到7163萬人,增加了1398萬人,城鎮化率由10.64%上升到12.46%[3]。這一時期城鄉關系處于自然發展狀態。
二、1953~1978年:城鄉“二元分割”狀態
國民經濟恢復后,1953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一化三改”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和“一五”計劃。1954年《憲法》規定:“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是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逐步完成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一五”計劃的具體任務就是建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進行以重工業為主的工業建設。我國模仿蘇聯經驗進入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趕超戰略時期,一直延續到1978年改革開放大幕開啟。雖然其間國民經濟發展比例嚴重失衡和遭遇“文化大革命”沖擊,但“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并未改變。我國城鄉關系內生于該戰略邏輯框架,形成了“二元分割”格局。
(一)“重工業優先發展”的邏輯必然性
我國要成為工業化強國,需要在電力、煤炭、石油、鋼鐵、有色金屬、化工產品、大型機床、汽車、拖拉機、飛機等重工業領域進行大規模投資,然而我國是一個以分散的小農經濟為主體的發展中國家,龐大的資本積累從何而來?顯然不能依靠分散的市場力量,一個可行的辦法就是依靠行政力量來組織動員和集中全國力量辦大事,將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納入國家全面掌控之中,即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建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系。在“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主導下,城鄉關系的自然演化進程被中斷。
(二)統購統銷制度與“工農剪刀差”
1.統購統銷制度
國家為了獲取更多的農業資源以支持城市工業化,一方面盡可能征收公糧,另一方面以低價格方式收購糧食。由于存在著競爭性私營糧店,低價收購政策會失效,因而只有壟斷糧食交易才能實現低價格策略,其他農副產品情況與糧食類似,于是國家在1953年對糧食和棉花進行統購。很快農民發現多生產沒有壓低價格的產品是有利的,因此1954年國家不得不將統購擴展到肉類、油料、花生等所有產品。同時將這些產品又同樣以低價格方式統一銷售到計劃指定的城鎮企業事業單位,低價格又大大降低了城市企業事業單位的生產生活成本。
這種一直延續到1985年的統購統銷制度將農業剩余轉移到城市,為工業化積累創造了條件。僅“一五”期間,國家對糧食、食用植物油、棉花、棉布等實行統購統銷,5年內國家征收公糧833億公斤,收購糧食1345億公斤,二者合計占糧食總產量(折成去殼糧)的28%,扣除返銷給農村的部分,國家實際向農民征購的糧食為1296億公斤,占糧食總產量的16.6%[4]。
2.工農“剪刀差”
為了維持高價格,國家不得不消滅商業競爭者以形成壟斷經營,社會主義改造逐漸從制度上消滅了競爭者,保護高價格長期有效運行。工農產品“剪刀差”是城鄉之間不平等交換關系的反映,是農民為工業化付出的代價。嚴瑞珍等運用折合工農業勞動比的方法,計算出1953~1985年“剪刀差”絕對額合計相當于同期全國預算內的固定資產投資額7878億元[5]。
(三)農業合作化運動與人民公社
如果農業剩余是工業化的必要條件,那么促進農業大發展從而為工業化提供更多的農業剩余就是國家農業政策的基本意圖。如何才能促使農業大發展呢?從現實情況看,在短期內增加土地、資本要素投入以及實現農業科技大發展都不現實,而利用計劃手段來快速進行農業組織制度變革從而增加勞動力投入是可行之道,政府希望通過推進農業合作化運動來實現國家意圖。1953年開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從“互助組”、初級合作社、高級合作社,快速發展到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農業合作化道路將農民束縛在集體經濟當中,農民逐步喪失了自主選擇權、退出權以及生產積極性。
(四)戶籍制度和票證制度:城鄉分割
1953年開始的“一化三改”的目標是為了盡快實現工業化。工業化會伴隨著城鎮化,吸引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入城市。然而,當時我國的工業化是以發展重工業為主,增加的城市重工業投資是資本密集型的,對勞動力吸收有限,甚至不能解決城市新增勞動力的就業需求,就業競爭壓力較大。農民進城對農業生產也不利,雖然農業合作化運動從組織上減少了農民外流的可能性,但畢竟加入合作社不是制度性強制,而是實行自愿平等原則,還不足以阻止農民入城。于是,195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施行,以法律的形式明確規定城鄉人口登記與遷徙手續:“只有持有勞動部門的錄用證明、學校錄取證明及城市戶口登記機關的準予遷入,并向常住戶口登記機關申請辦理遷出手續,公民才能由農村遷往城市。”由此,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建立起來,限制了農民自由遷移的權利。
從此,戶籍制度和先前實施的票證制度結合,就連那些想要違反規定“非法就業”的農民也被阻止了,因為國家對城市戶口居民的生活資料實行憑票供應的配給制,沒有城鎮戶口的農民無法在城市生存,更不用說享受城市工資和各種福利待遇。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和計劃經濟體系導致城鄉分割,工農關系不平等,他們為工業化付出犧牲的同時卻無法享受工業化帶來的好處。1978年城鄉居民實際收入差距達到3∶1,與之相對應的是我國城鎮化嚴重滯后,1950~1980年,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8.4%上升到 41.3%,其中發展中國家由16.2%上升到30.5%,但是我國僅由 11.2%上升到19.4%[6]。
三、1979~1985年:城鄉關系趨于緩和
1978年底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將黨和國家的中心任務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開始松動,市場化改革應運而生,城鄉關系在市場化改革過程中向好的方向發展。改革首先從農業領域開始并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全國范圍內展開,在政府大力支持下糧食產量快速增長,1984年全國糧食產量創造歷史最高記錄,基本解決了長期以來的糧食短缺問題。糧食安全得到保證后,1985年政府取消了統購統銷制度,鼓勵農民家庭調整資源投入,開展多種經營,并相應地改革了農副產品流通體制。隨著農業技術的進步,越來越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可以轉入非農業領域,獨具特色的鄉鎮企業開始興起。由此,城鄉不平等關系得到逐步糾正并趨于緩和,其結果是我國城鎮化開始加速,“六五”時期城鎮化率從1981年的20.16%提高到1985年的23.71%[7];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日益縮小,城鄉居民收入比從2.05∶1下降到1.71∶1[8]。
(一)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允許農民包產到組或包干到組,禁止包產到戶或包干到戶。但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18戶村民冒險實行包產到戶,并大獲成功;1980年包產到戶得到快速發展。在這種情形下,1981年11月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予以確認:包產到戶、包干到戶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不是資本主義經濟性質,并要求在全國推廣。1981年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生產隊達45%,第二年提高到80%,到1984年全國農村99%都實行責任制,結果是1978~1984年農業增長速度由原來的2.9%提高到7.7%[9]。
正是以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改革起點,我國開啟了“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式市場化改革進程。隨著城鄉關系中市場化因素日趨濃厚,長期城鄉“二元分割”關系開始在市場化進程中消解,從不平等逐步走向平等。
(二)放松管制與市場化改革
1981年國家放松對農副產品統購統銷管制,規定一類統購產品有糧食、棉花、油料和木材,二類派購產品有127種(其中,中藥材54種,水產品21種),其他產品為三類產品,三類產品和完成派購任務的二類產品可以自由出售。從1983年起,國務院調整統購派購范圍,將一些二類產品改為三類產品;1984年屬于統購派購的產品只剩下38種(其中,中藥材24種)。1985年1月1日起,國家不再向農民下達統購派購任務,分別實行合同定購和市場收購,定購的糧食國家統一按“倒三七”計價(三成按原統購價,七成按原超購價①);定購的棉花,南方按“倒三七”計價,北方按“正四六”計價。定購以外的糧食和棉花以及取消派購后的生豬、水產品、牛羊肉、 家禽、蔬菜等農副產品都可以自由出售,價格由市場供求決定,工農產品“剪刀差”扭曲的程度得到相當大的緩解。
越來越多的農副產品進入市場,激發了農民調整種植結構和多樣化經營的積極性,日益增長的農副產品不可能在農村內部消化,供應城鎮市場勢所必然。這就倒逼政府改革不合時宜的農副產品流通體制,鼓勵集體商業和個體商業經營,實際上國營商業和合作社雖然參與農副產品經營,但大部分農副產品由集體商業和個體商業主導經營。1983年中央印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草案)》,強調走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農工商綜合經營的道路;允許農民采用機動車船出縣、出省長途販運。城鄉農貿市場開始興盛,城鄉經濟交流形式和規模日益發展,城鄉聯系日益密切。
(三)鄉鎮企業的興起
從邏輯上講,農村市場化改革帶來的原材料增長、資金積累和剩余勞動力可以再投入農業生產當中形成擴大再生產。但農業生產服從邊際產品遞減或規模報酬遞減原則,因而增加的生產要素應該轉向非農業領域以獲取更多的利益,通常這些生產要素按照市場原則會流入城市。但是改革開放之初(1979~1984年),由于戶籍制度限制,新增的資源難以在城市中尋找自身的價值,于是這些資源激活了原本沉寂的社隊企業,鄉鎮企業在此基礎上興起。從本質上看,鄉鎮企業是我國工業化的一種特殊形式,它改變了傳統“農村—農業”和“城市—工業”的產業布局邏輯,出現了獨特的“農村—工業”形態。這種形態在我國20世紀五六十年代也出現過,即全民“大煉鋼鐵”時期,只不過那時的農村—工業形態由計劃強制形成,而今是市場自發選擇。
1.鄉鎮企業大發展
1984年全國鄉鎮企業發展到606萬個,鄉鎮企業總產值達1709億元,鄉鎮企業總收入達1537億元,從業人員5206萬人,占農村總勞動力的14%[10]。1985年鄉鎮企業總產值達到2728億元,占農村社會總產值的44%;就業人員6000萬人,占農村總勞動力的20%。鄉鎮企業的生產經營范圍涉及廣泛,包括冶金、電力、煤炭、石油、化工、機械、建筑建材、紡織、皮革等,許多產品在全國同類產品中占相當大的比重。
2.城鎮化的新途徑
鄉鎮企業的大發展為我國城鎮化提供了一種新的途徑。鄉村工業的持續繁榮促進了小城鎮的發展,并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甚至到了200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小城鎮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指出,市場化力量已經成為推動城鎮化的主要力量,這個觀點在當時是主流觀點。的確,鄉鎮企業為市場化力量所催生,戶籍制度和城市改革滯后使得鄉村產業經濟不得不進行“自循環”。但當戶籍制度開始松動,城市市場化改革興起之后,這種“自循環”經濟很快就被整個國民經濟所稀釋。鄉鎮企業所面臨的環境條件改變了。城鄉關系因農村經濟市場化改革而走向融合,但也因市場化改革在全國范圍和各行各業內展開而再次面臨挑戰。
四、1986~2005年:城鄉關系失衡
主要得益于前期農村率先推行市場化改革的城鄉關系融合,也因后來農村改革停滯和城市改革興起而再陷分離。城市改革開啟后,整個國民經濟中市場化特征日益明顯;1992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開始建立,順應新的市場體制要求,1994年“分灶吃飯”財政體制(即“分稅制”)產生,“發展型”地方政府應運而生。地方官員為了地方GDP增長開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投資沖動;2001年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他們又控制不住“招商引資”的熱情,這都導致了地方政府“城市偏好”政策[11]。為了快速做大經濟蛋糕,地方政府官員不僅沒有加大農業投入力度,反而加大了對農村土地租金和金融資源的汲取,以支持工業化和城鎮化。
這一階段的城鎮化導致城鄉關系呈現地區差異化特征:東部沿海地區由于鄉鎮企業和外向型經濟的發展,城鄉融合持續深入,城鄉差別越來越小;廣大中西部地區,城鄉差距持續惡化。同時廣大“農民工”群體由于戶籍限制沒能享受到工業化和城鎮化帶來的利益,總體上看,城鄉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城鄉居民收入比從1985年的1.86∶1擴大到2005年的3.22∶1(見圖1,下頁)。
(一)加快推進城市改革
我國經濟改革遵循“漸進式”和“先易后難”的策略。率先發動的農村改革取得了可喜成功后,進入了停滯時期,國家將注意力轉向了城市改革,希冀國民經濟運行在充滿活力的微觀經濟主體(企業)之上,圍繞激發企業活力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1984年《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改革的中心環節是增強企業活力,實行政企分開,簡政放權,探索包括租賃、承包、股份制等多種經營機制;同時鼓勵發展多種所有制形式工商業和個體經濟以增加競爭主體;隨后改革計劃管理、商業流通、財政、投資、金融、科技教育等宏觀管理體制,將企業改造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微觀經濟主體;進一步發展對外開放和對外貿易,通過對外開放來“倒逼”內部改革。
經過一系列的改革,國民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城市勞動者的工資、獎金、福利等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他們成為改革開放的堅定擁護者。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隨后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以及1997年黨的十七大提出“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預示著國家在重構國民經濟的微觀基礎,這些都具有典型的城鎮化和工業化特征,農村農業農民問題日益積累,形成后來備受關注的“三農”問題。
(二)實施“城市偏好”政策
在這一時期,不僅國家對經濟體制改革的力量集中在城市,而且這種“偏好城市”的選擇更是體現在地方官員的行為當中。1994年國家財政體制實行“分稅制”改革,中央與地方開始“分灶吃飯”,由此,地方官員獲得了發展地方經濟相當大的自主權。由于農業是弱質產業,產品需求彈性小,而許多城市工業是新興產業,產品需求彈性大,后者更容易產生GDP貢獻,因而政府多鼓勵企業投資流向新興工業。在整個政府財政支出結構中,消費型支出(如教育、醫療衛生和社會保障)不如投資型支出(如公共基礎設施)對GDP的貢獻大。城市基礎設施的回報率高于農村基礎設施,而且良好的公共基礎設施服務對“招商引資”更為有利,所以不管是產業政策還是財政政策都會是“城市偏好”型的。Zheng Song等指出,這種經濟增長競爭不僅造成了城鄉之間增長不平衡,而且也造成東部沿海與中西部地區之間的地區增長不平衡[12]。
(三)吸收農村土地租金和金融資源
在城鎮化過程中,城市周邊的農村土地不斷增值,這本是城鎮化帶給農民的意外收益,但是在政府征用這些土地時,并未按照土地的市場價格征用,而是以低得多的價格征地。早期的城鎮化過程伴隨著不平等的交易關系,政府低價格征用來的農業土地通過略加改造,就能以工商業用地方式出售給開發商以獲得巨額土地出讓金,這些土地租金成為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形成“土地財政”[13]。
同時,隨著農民發展生產經營收入或外出務工工資收入的不斷增加,這些收入逐年積累到相當大的數額,以貨幣存款形式存放于農村金融機構和農村信用社,它本可以為鄉鎮企業和農業經濟提供信貸資金支持,但是正如前面所述,由于政府的城市偏好以及農村投資的收益較低,而城市和沿海地區投資收益高,因而市場存在的存貸利差誘使農村金融機構和信用社將金融資源轉移出農村,留給本地和農村的信貸資金則非常有限。比如,1999~2002年農業和鄉鎮企業貸款余額占各項貸款總額的比重僅分別為10.69%、10%、10.8%和10.4%,而僅在2001年國有商業銀行以吸收存款的方式從農村地區抽取的資金就高達3000億元[14],這樣數以萬億元的農村資金流向城市。
五、2006~2011年:城鄉一體化發展
董全瑞認為,我國城鄉關系的演變過程體現出“路徑依賴”的特征:改革開放前通過統購統銷、人民公社和戶籍管理等制度安排攫取農民剩余;改革開放后在時間變量和環境參數約束下,把統購統銷改為計劃和市場相結合的二重交易規則,戶口政策由限制農民向城市流動變為限制農民的權利,工農“剪刀差”轉換為生產要素價格雙軌制,農村支持城市的“單向關系”始終沒有改變[15]。因此,隨著制度安排的自我強化效應,城鄉之間的“單向關系”造成的矛盾達到危險的地步,“三農”問題日益突出,這不僅會影響國民經濟的健康運行,而且可能會根本上動搖我國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和政權的合法性。此時國家不得不正視這些矛盾和問題,并決心遏制和改變不平衡狀態,將城鄉一體化作為一項長期任務來推進。針對農村支持城市的“單向關系”,2004年國家開始考慮“反哺”問題并實施“反哺”政策。在考慮工業“反哺”農業的同時,農業農村自身也要苦練內功。2006年,國家“十一五”規劃綱要提出“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要求,提出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我國將城市和農村的發展更加緊密結合起來統一考慮,進行城鄉統籌。2010 年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三化”同步,這是城鄉一體化策略的目標要求。
(一)實施“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政策
2004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我國總體上已經到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我們應當順應這一趨勢,更加自覺地協調整個國民經濟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積極地支持“三農”發展。隨后2006年農業稅被廢止,農民負擔大大減輕,城鄉之間矛盾得到暫時緩解,依附在農業稅上的“三提五統”和亂收費等也被終止,“多予少取放活”反哺政策開始產生效力。
然而,當時學術界關于這項政策頗有爭議。經濟發展理論認為,工業反哺農業是工業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工農關系、城鄉關系變化特征的一種概括,但至于經濟發展到什么程度才適合“反哺”呢?或者說,我國能否實行農業保護政策呢?林毅夫認為,我國當時還沒有達到工業反哺農業階段,理由包括:我國當時的財政還不能滿足對農民的大量補貼;對農業補貼會導致農產品過剩, 不利于維持良好的國際貿易和外部環境;一旦對農業開始進行補貼,就很難取消掉, 因為取消補貼往往會引發社會和政治問題;對農產品進行補貼,在執行上非常困難[16]。蔡昉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并結合我國的實際進行比較分析,認為2004年我國農業產值比重下降到15.2%,農業勞動力比重下降到46.9%,具備了進行“反哺”農業的條件[17]。其實仔細分析這種爭議就會發現,兩人的觀點并不矛盾:林毅夫是從“反哺”政策可操作性意義上得出否定結論的;蔡昉是從“反哺”的必要性意義上作出肯定結論的,但他認為我國實施農業保護政策不可取,應該尋找新的途徑。
2008年中央“反哺”方針的提出肯定了蔡昉的主張,然而中央“反哺”政策的操作效果證明了林毅夫的顧慮并非多余。2004~2012年,中央財政“四項補貼”(糧食直補、良種補貼、農資綜合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支出從145.7億元增加到1668億元,累計補貼金額 7661億元,增長了10.4倍,年均增長35.6%[18];但是農業保護政策效果并不好,城鄉收入比從2000年的2.79擴大到2007年的最高值3.33,然后下降至2011年的3.13,但遠遠高于1985年的最低值1.71。李志杰也指出,黨的十六大以來國家實施了不少有效的惠農舉措,但是城鄉二元結構實質性改變和城鄉關系顯著改善絕非短期內就能完成的,城鄉一體化進程只能是漸進式的[19]。
(二)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通過以上的分析可知,僅僅靠國家的農業保護政策并不能解決“三農”問題,國家需要在許多方面加大支農資金投入。我們不得不面臨一個經濟學的規律,即經濟發展并不會自動導致城鄉差距的縮小,市場并不會促使城市工業形成“反哺”農業農村的自發機制。說到底,除了政策性支持外,農村農業還得“自力更生”。2006年國家“十一五”規劃綱要提出“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要求,要求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經濟建設方面,建立農民增收長效機制,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政治建設方面,加強農村基層民主制度和農村法制建設,引導農民依法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文化建設方面,開展多種形式的體現農村地方特色的群眾文化活動,豐富農民群眾的精神文化生活;社會建設方面,在加大公共財政對農村公共事業投入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農村義務教育和職業教育,加強農村醫療衛生體系建設,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
新農村建設是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它保證了廣大農民參與經濟社會發展過程,共享發展成果。為了支持新農村建設,國家繼續對農村義務教育、鄉村公路建設、鄉村基礎設施建設以及農村醫療建設等進行專項財政資金投入,并加大了投入力度。2004年國家支農資金達2626億元,2005年、2006年分別達2975億元、3397億元,分別增長了13.3%和14.2%。地方政府對專項資金進行配套,吸引了更多的資金進入農業農村,極大地促進了農業農村的發展。在2006年的基礎上,2007年進一步擴大整合資金的渠道,中央財政增加了支持試點的引導性資金,同時選擇一部分地區和縣級單位開展扶貧資金和其他支農資金統籌安排使用的試點,試點范圍從糧食主產區擴大到全國范圍,重點是支持現代農業發展和新農村建設。國家在專項資金的基礎上,持續擴大“三農”資金投入規模,2007~2012年中央財政“三農”累計支出4.47萬億元,年均增長率高達23.5%[20]。在國家資金的大力支持下,農村內部的潛力和活力也得到了挖掘和發揮,農民人均純收入較快增長,2010年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開始縮小,城鄉關系持續惡化的情況得到遏制并逐步改善。
(三)實施城鄉一體化政策
城鄉一體化是從統籌城鄉的發展思路演化而來的,它試圖將城市與農村的發展緊密結合起來,統一協調、全面考慮、綜合平衡。2008年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把加快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作為根本要求;2010年10月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明確提出,在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深入發展中同步推進農業現代化,是“十二五”時期的一項重大任務。
周江燕等將城鄉發展一體化的內涵界定為:在城鄉共同增長的前提下,城市與農村兩大地域子系統的空間界限逐漸模糊,經濟差距逐漸縮小,社會發展成果逐漸均等,生態環境差異逐漸消失,最終達到最大限度地縮小現存的城鄉差別,實現城鄉合作大于城鄉沖突,建立城鄉互補、協同與融合發展的共生模式[21]。我國城鄉一體化程度提升較為緩慢,2000~2011年城鄉經濟一體化指數由0.57 提高到1.05[22];我國城鄉社會一體化發展滯后,城鄉二元對比系數雖然從2005年的0.162 增加至2011年的0.190,但依舊低于發展中國家的最低值0.310①。
不僅如此,我國城鄉一體化程度在省、市、縣際水平上也是異質性的。汪宇明等釆用主成分分析法對2008年我國30個省域的城鄉發展一體化水平進行了測度,結果發現我國城鄉發展,無論是東部相對發達省份還是西部欠發達省份,內部差異均較顯著并呈現非均衡的特點[21]。2007年6月,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正式批準重慶市和成都市設立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中國人民銀行成都分行金融研究處課題組研究發現,成都市城鄉一體化發展程度已經遠超過國家平均水平,城鄉差異度有縮小的趨勢;但是城鄉差別仍然明顯,城市居民收入增速大于農村居民,而城鄉居民在消費上的差異在減小;各區市縣城鄉一體化程度表現出不均衡發展態勢,存在一定的梯度分布特征,發展程度的不均衡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成都市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整體協調推進,這從各個層次上反映出我國城鄉一體化建設需要進一步加速[23]。
六、2012年至今:城鄉關系融合發展
隨著國民經濟的不斷發展,農業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份額將越來越小,發展型政府是難以將“三農”問題置于核心地位的,這促使我們必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尋找新的有效措施和途徑來破解“三農”問題。一方面,我國執行2012年黨的十八大以來的城鄉一體化的整體方針政策,通過工業化、城鎮化和信息化來帶動農業現代化,然而制約“四化”同步的戶籍制度必須從制度層面加以解決;另一方面,留在農村的人口的生存、溫飽和富裕的問題也是我國面臨的挑戰,特別是農村深度貧困地區,扶貧脫貧任務復雜繁重。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精準扶貧”方略,在整體規劃的同時尋求農村重點人群的突破,農村農民迎來了新時代的春風。2017年黨的十九大之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社會的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村發展不充分問題已經上升為國家層面的戰略問題,成為影響社會主義現代化成敗的關鍵,由此鄉村振興戰略應運而生,城鄉關系進入融合發展的新時代。
(一)加快推進戶籍制度改革
長期實踐經驗和理論研究表明,解決“三農”問題最有效的“新”途徑是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而戶籍制度是農民工進城落戶的根本障礙。Whaley & Zhang在假設戶籍制度是勞動力遷移的唯一障礙的條件下,通過一項模擬表明,一旦取消以戶籍制度為代表的對于勞動力遷移的障礙,現存的收人不平等則會全部消失[24]。2012年以來,國家陸續出臺政策,加快改革戶籍制度,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轉為城鎮居民,并著力解決暫不具備落戶條件的農民工在勞動報酬、子女上學、技能培訓、公共衛生、住房租購、社會保障、職業安全衛生等方面的問題,努力實現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2014年,我國提出到2020年努力實現1億左右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統一城鄉戶口登記制度,全面實施居住證制度。2016年又提出加快建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激勵機制,除極少數超大城市外,全面放寬農業轉移人口落戶條件。2019年提出要繼續加大戶籍制度改革力度,在此前城區常住人口100萬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已陸續取消落戶限制的基礎上,城區常住人口100萬至300萬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戶限制;城區常住人口300萬至500萬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開放寬落戶條件,并全面取消重點群體落戶限制;對于超大特大城市,要調整完善積分落戶政策,大幅增加落戶規模、精簡積分項目,確保社保繳納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數占主要比例。此間,我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上升較快,從2012年的35.3%提高到2018年的43.37%。戶籍制度改革和新型城鎮化建設,有力地推動了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和城鄉關系融合發展。
(二)實施“精準扶貧”方略
2015年在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扶貧攻堅實施“精準扶貧”方略,增加扶貧投入,出臺優惠政策,廣泛動員全社會力量參與扶貧。許多政策措施出臺,支持農村力度空前,農村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農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截至2018年末,全國農村貧困人口從2012年末的9899萬人減少至1660萬人;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14 617元,城鄉居民收入比由2005年的3.22∶1下降為2.69∶1,雖然這個比率仍然偏高,但出現了非常良好的下降趨勢,城鄉經濟融合發展前景光明。
(三)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精準扶貧”只是解決農村農民貧困的問題,但更深遠的是要解決農村農民富裕的問題。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鄉村振興戰略。2018年《國家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發布,提出讓農民成為有吸引力的職業,農村成為安居樂業的美麗家園。“鄉村振興”戰略較為系統地回答了“誰來振興”、“為誰振興”和“如何振興”等問題。鄉村振興戰略的目標任務是:到2020年,鄉村振興取得重要進展,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鄉村振興取得決定性進展,農業農村現代化基本實現;到2050年,鄉村全面振興,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全面實現。實現路徑是“七條道路”:重塑城鄉關系,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走共同富裕之路;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走質量興農之路;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鄉村綠色發展之路;傳承發展提升農耕文明,走鄉村文化興盛之路;創新鄉村治理體系,走鄉村善治之路;打好扶貧攻堅戰,走中國特色減貧之路。鑒于以往解決“三農”問題的政策措施執行方面存在“雷聲大雨點小”的弊病,要實現這一宏偉的目標,需要在頂層設計框架下,踏踏實實地將各項工作落到實處。可以期望,當鄉村產業興旺、生活富裕之時,就是我國城鄉關系高度融合發展之時。
七、新中國70年城鄉關系演變的啟示
梳理新中國70年城鄉關系演變進程,揭示其演變邏輯,對于妥善處理未來城鄉關系具有重要啟發意義。
(一)國家戰略和政策取向對城鄉關系演化路徑產生重要影響
深入探討影響城鄉關系演化歷程的因素后,我們發現國家戰略和政策取向深刻地影響著城鄉關系演化特征和演化路徑。1953年國家實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城鄉關系從平等向不平等演化,在戶籍制度的限制下形成“城鄉分割”;1978年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市場化改革率先在農村展開,農村經濟在1986年以前獲得快速增長,城鄉關系得到緩和并趨向融合;但是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全面展開,特別是1992年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以及對外開放日益發展,促成了“發展型”地方政府的出現,再次將城鄉關系引向失衡;面臨嚴峻的形勢,2006年國家開始廢止農業稅,推進統籌城鄉發展,提出城鄉一體化策略,城鄉關系嚴重失衡的形勢得以扭轉;2012年黨的十八大以后,城鄉關系引起中央高度重視,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將城鄉關系帶入融合發展的新時代。這啟示我們,未來的城鄉關系的演化路徑,很可能出現“路徑依賴”特征:國家戰略對城鄉關系未來取向仍然會產生重要影響,今后的城鄉關系要更加關注國家戰略的走向和政策取向。
那么,在未來的城鄉關系融合發展過程中,國家能夠提供什么樣的政策支持呢?根據“四化”同步的要求,對于農村農民應該“缺什么補什么”。具體說來,戶籍制度阻礙生產要素流動,在適當的時候應將其取消;農村土地產權制度需要改革以實現農民生產要素的市場價值;農村基礎設施投入、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方面明顯不足,需要向城市居民看齊;城鄉收入差距仍然較大,相關政策措施應促進農民增收,農業農村相關政策要繼續加大支持力度。這些政策體現在鄉村振興戰略當中,城鄉關系的未來與鄉村振興之路可謂休戚相關。
(二)我國城鄉關系的實質是國家與農民的關系
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過程中,國家明確提出農民是鄉村振興的主體,賦予農民主體地位,充分說明了國家對農民的重視和尊重,大大提升了農民在國家戰略中的地位和作用。
農民在國家政治經濟關系中的地位決定了我國城鄉關系的融合發展程度。國家需要重新認識國家與農民之間的關系,既要從經濟上充分發揮其主體性地位和作用,又要在國家權利結構中給農民足夠的發言權。從歷史經驗中我們發現,滿足農民的權利需求并給予制度和組織保證,是城鄉關系融合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城鄉關系發展過程中的一種自動糾偏機制,因為作為城鄉關系的主體,廣大農民群眾會主動選擇有利于實現自身權利的制度和政策。
(三)市場化是城鄉關系中的一柄“雙刃劍”
張海鵬總結新中國成立70年我國城鄉關系的經驗時認為,堅持市場化改革是城鄉融合發展之道[25],但筆者認為,在城鄉關系的演變過程中,市場化之于城鄉關系是一柄“雙刃劍”:它既可能促進城鄉關系的融合發展,也可能促使它走向分離或失衡。究其原因,市場配置資源的有效性來源于它能夠調動微觀經濟主體的積極性,使資源流向有效率的地方,這個地方可能是農村,如1978~1985年的情形,也可能流向城市,如新中國成立初期、1986~2005年及2006~2011年。市場中資源到底如何流動,是由微觀經濟主體的逐利性決定的。利益所指乃投資所向,農村和城市都有機會,因此關鍵是看政府對城鄉關系的認知。
政府和市場將如何塑造新型的城鄉關系,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力度和領域比發達國家更大更寬,在處理城鄉關系的過程中,政府力量運用是十分重要的,但它相比于市場力量,有一個比較大的弱點,即它的產出和執行效率不如市場那么明確,主要是缺少有效的激勵機制和信息反饋機制[26]。因此,政府在努力提高自身效率的同時,更要為經濟主體創造有利于資源流入農村的有利環境條件,將政府與市場有機結合起來,為實現新時代城鄉關系的融合發展而努力。
參考文獻
[1]韓俊.中國城鄉關系演變60年:回顧與展望[J].改革,2009(11):5-14.
[2]LEWIS W 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J]. The Manchester School, 1954, 22(2): 139-191.
[3]趙偉. 新中國城鄉經濟關系演變的歷史考察[J].學術評論,2013(6):13-21.
[4]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1953~1957年)計劃執行結果的公報[J]. 計劃與統計,1959(7):5.
[5]嚴瑞珍,龔道廣,周志祥,等.中國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的現狀、發展趨勢及對策[J].經濟研究,1990(2):64-70.
[6]許滌新. 當代中國的人口[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294-295.
[7]國家統計局. 中國城市化率(1949~2013)歷年統計數據[M]. 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4.
[8]國家統計局.六五期間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概況[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6.
[9]林毅夫.解讀中國經濟(第三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145-146.
[10]農牧漁業部鄉鎮企業局統計處. 一九八四年全國鄉鎮企業發展概況[J]. 農業經濟叢刊,1985(4):54-55.
[11]陳斌開,林毅夫.發展戰略、城市化與中國城鄉收入差距[J]. 中國社會科學,2013(4):81-102.
[12]ZHENG SONG, KJETIL STORESLETTEN, FABRIZIO ZILIBOTTI. Growing like China[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1(101):196-233.
[13]賈康,梁季.市場化、城鎮化聯袂演繹的“土地財政”與土地制度改革[J].改革,2015(5):67-81.
[14]王永欽. 大轉型:互聯的關系型合約理論與中國奇跡[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9:120.
[15]董全瑞. 路徑依賴是中國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內在邏輯[J].經濟學家,2013(10):89-93.
[16]林毅夫.中國還沒有達到工業反哺農業階段[N].南方周末,2003-07-17.
[17]蔡昉. “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經濟學分析[J].中國農村經濟,2006(1):11-17.
[18]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產業所課題組. 改革開放40年中國工農關系演變:從緩和走向融合[J].改革,2018(10):39-51.
[19]李志杰.中國城鄉一體化的實證分析與政策思路[J].學習與探索,2012(6):50-52.
[20]新華網.中央財政“三農”五年累計支出4.47萬億元,年均增長23.5%[EB/OL].(2013-3-5)http://www.xinhuanet.com//2013lh/2013-03/05/c_132208669.htm.
[21]周江燕,白永秀,王舒傲. 西部地區城鄉發展一體化水平:狀態判斷與類型劃分[J]. 人文雜志,2014(12):43-50.
[22]汪宇明,劉高,施加倉,等. 中國城鄉一體化水平的省區分異[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2(4): 137-142.
[23]人民銀行成都分行金融研究處課題組. 成都市城鄉一體化進程及其水平測度[J]. 重慶社會科學,2010(6):17-21.
[24]JOHN WHALLEY, SHUNMING ZHANG. A numerical simulation analysis of (Hukou) labour mobility restrictions in China[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7, 83(2): 392-410.
[25]張海鵬.中國城鄉關系演變 70 年:從分割到融合[J].中國農村經濟,2019(3):1-17.
[26]于云榮,宋振全.經濟體制變遷條件下政府與市場關系再解構[J].改革,2017(9):18-26.
The Evolu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of the
PRC from 1949 to 2019
XING Zu-li ?CHEN Yang-lin ?DENG Chao-chun
Abstract: The urban-rural relations have undergone twists and turn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Study on the logical evolution of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over last 70 years can provide cues and enlightenment to future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in China. From 1949 to 195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was basically in a state of natural development. From 1953 to 1978, the dual structure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formed gradually;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paid a great price for the strategy of “priority development of heavy industry” in cities. Since 1979 to 1985, the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tended to ease;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developed rapidly. However, with the rise of “development-oriented government” in 1986-2005, urban and rural areas were separated. From 2006 to 2011, the state was determined to curb and change the state of urban-rural separation, and pursu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s a long-term task.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adjustment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and the urban-rural relations have entered a new era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since 2012. The essence of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in China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rural people. National strategy and policy orientation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Marketization has played a “double-edged sword” role in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It is suggested that future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should be based on reconstructing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rural people, and coordinating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so as to achieve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evolution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