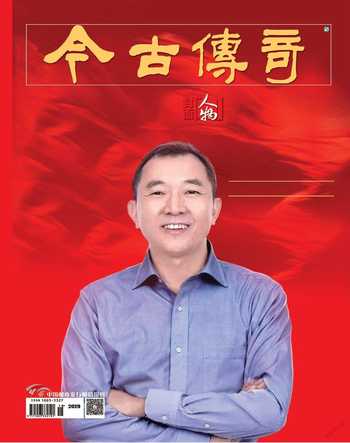“故宮盜寶案”始末
作為故宮博物院的締造者之一,易培基在去世時(shí)背負(fù)了“監(jiān)守自盜”的惡名。最后時(shí)刻他仍希冀國(guó)家能還他清白
1937年10月,故宮博物院首任院長(zhǎng)易培基在上海寓所辭世。作為故宮博物院的締造者之一,他不但沒有收獲公眾應(yīng)有的尊重,反而在去世時(shí)背負(fù)了“監(jiān)守自盜”的惡名。一樁莫須有的“故宮盜寶案”,因?yàn)闃?gòu)陷對(duì)象是易培基,也成了轟動(dòng)一時(shí)的“易案”。
彌留之際,易培基將一份陳情書托老友轉(zhuǎn)交給國(guó)民政府。他寫道:“惟是故宮一案,培基個(gè)人被誣事小,而所關(guān)于國(guó)內(nèi)外觀聽者匪細(xì)。”最后時(shí)刻他仍希冀國(guó)家能還他清白。
一樁毫無懸念的冤案,竟長(zhǎng)達(dá)17年不能結(jié)案,它成為管窺國(guó)民黨政治生態(tài)的一個(gè)標(biāo)本。
悍婦的舉報(bào)信
1932年8月29日,一封匿名信寄到北平政務(wù)委員會(huì),舉報(bào)故宮博物院院長(zhǎng)易培基擅自處理故宮物品,盜賣故宮古物。當(dāng)時(shí),故宮正在公開出售清宮與歷史藝術(shù)無關(guān)的物品,以此來貼補(bǔ)運(yùn)營(yíng)經(jīng)費(fèi)。
其實(shí)早在1927年,故宮博物院就曾經(jīng)提出過“處分(即處理)消耗品”的計(jì)劃。當(dāng)時(shí),控制北京的奉系軍閥與北伐的國(guó)民革命軍激戰(zhàn)正酣,根本沒心思管故宮。故宮博物院的經(jīng)費(fèi)來源,除了門票收入,再無其他。許多職員經(jīng)年累月領(lǐng)不到工資。為解燃眉之急,故宮博物院決定處理一批宮內(nèi)生活用品。但“處分物品”計(jì)劃還沒有實(shí)施,就被人告到了警察廳。檢舉者說,故宮“處分物品”是為了給南方國(guó)民政府籌錢。于是,北洋政府下令緩辦。第一次“處分物品”計(jì)劃就這樣胎死腹中了。
易培基出任故宮博物院院長(zhǎng)后,重提舊事。1931年11月,經(jīng)過精心籌備,“處分物品”公開出售。據(jù)記載,故宮博物院先后進(jìn)行過三次“處分物品”,而易培基被人舉報(bào)時(shí),正是在第三次“處分物品”之后不久。
接到舉報(bào)信兩個(gè)月后,南京監(jiān)察院派來兩名監(jiān)察員周利生、高魯,專程到北平調(diào)查此事。他們?cè)诠蕦m調(diào)查了兩個(gè)星期,雖然沒查出什么問題,但他們還是向國(guó)民政府政務(wù)官懲戒委員會(huì)提交了對(duì)易培基的彈劾材料。
消息傳來,故宮博物院上下一片嘩然。大家一致認(rèn)為,時(shí)任故宮博物院文獻(xiàn)館館長(zhǎng)張繼的夫人崔振華舉報(bào)的嫌疑最大。
因?yàn)椴痪们埃拚袢A聽說故宮在出售皇家用品,也趕來選購(gòu)。選購(gòu)者照例是要買了故宮的參觀券才能進(jìn)入,崔振華認(rèn)為自己是館長(zhǎng)夫人,于是昂然直入。門衛(wèi)并不認(rèn)識(shí)她,硬是攔住不讓進(jìn)。她怒不可遏,大呼小叫起來。故宮的一名職員看到這一幕,連忙告訴門衛(wèi):“此乃文獻(xiàn)館張繼館長(zhǎng)的太太。”門衛(wèi)一聽,趕緊請(qǐng)她進(jìn)去。
崔振華一路罵罵咧咧來到售賣室。正巧,當(dāng)天是易培基的女婿故宮博物院秘書長(zhǎng)李宗侗值班,崔振華見了他一通發(fā)泄。李宗侗脾氣耿直,當(dāng)即說道:“你又沒告訴我今天要來買東西,門衛(wèi)不認(rèn)識(shí)你,怎能怪我?”兩人你一言我一語(yǔ),互不相讓,鬧得不可開交。
易培基素知崔振華是個(gè)“瘋婆子”,事后并沒有責(zé)怪李宗侗。但崔振華不肯就此罷休,于是她和張繼一起策劃了舉報(bào)易培基的驚天大陰謀。
結(jié)怨于人事
多年后,故宮博物院的老人回憶起這場(chǎng)風(fēng)波都說,崔、李之爭(zhēng)其實(shí)只是“易培基冤案”的一個(gè)導(dǎo)火索,其更深層次的矛盾,早在幾年前的人事安排上就埋下了。
1924年故宮收歸國(guó)有后,清室善后委員會(huì)成立。從那時(shí)起,易培基和李煜瀛一直都是故宮博物院管理層的核心成員。1928年北伐成功后,李煜瀛、易培基、張繼三人均被推為常務(wù)理事,易培基被委任為故宮博物院第一任院長(zhǎng),李煜瀛被委任為理事會(huì)理事長(zhǎng)。張繼本應(yīng)被任命為副院長(zhǎng),但李煜瀛和易培基認(rèn)為他資歷尚淺難以服眾,遂建議其任故宮博物院文獻(xiàn)館館長(zhǎng)。張繼與李煜瀛、易培基也因此結(jié)怨。
就在周利生、高魯發(fā)出對(duì)易培基的彈劾不久,北平《快報(bào)》記者謝振翮等7人聯(lián)合向北平地方法院檢察署檢舉易培基圖利瀆職。他們舉報(bào),故宮博物院在出售金器的時(shí)候價(jià)格太低,而且還處理了具有歷史文物價(jià)值的金八仙碗。這次舉報(bào)隨著媒體的介入,變得人所共知。易培基不得不在1933年1月向國(guó)民政府呈文,為自己申辯。
易培基指出,“處分金器”是經(jīng)過故宮理事會(huì)和國(guó)民政府批準(zhǔn)的。所謂的“金八仙碗”其實(shí)是殘品,“制作惡劣,絕無美術(shù)可言”,而且故宮里類似的八仙碗很多,就連尋常金店里也有銷售。臨時(shí)監(jiān)委會(huì)認(rèn)為,它們并不具備歷史和藝術(shù)價(jià)值。至于把出售之款用于發(fā)工資,更是無稽之談。“處分物品”的收益均作為基金,專款儲(chǔ)存,賬目清清楚楚。
易培基的答辯有理有據(jù),彈劾自然落空了。然而,張繼夫婦并沒未善罷甘休,他們很快又羅織罪名,卷土重來。
報(bào)錯(cuò)電報(bào)露了底
1933年5月1日,南京最高法院檢察官朱樹森拿著天津高等法院的介紹信,以參觀的名義來到故宮博物院。當(dāng)庶務(wù)科虞科長(zhǎng)接待他時(shí),他卻提出來要查看院里的文件卷宗。虞科長(zhǎng)連忙打電話請(qǐng)示。易培基得知此事后,本待應(yīng)允,可故宮博物院“維持會(huì)”副會(huì)長(zhǎng)吳瀛卻覺得不妥:“他拿著天津高等法院的介紹參觀信,如何能看文件呢?”于是,經(jīng)過雙方商議,朱樹森只在院內(nèi)參觀,但經(jīng)手過“處分物品”的人員要隨時(shí)聽候他問話。
第二天一早,朱樹森來到故宮,李宗侗、吳瀛等參與過“處分物品”的人紛紛到齊。剛開始朱樹森問了問“處分物品”的經(jīng)過,并沒什么新發(fā)現(xiàn)。正待作罷,負(fù)責(zé)“處分”綢緞的書記員尹起文忽然站起來說:“就是有一筆秘書長(zhǎng)同院長(zhǎng)購(gòu)買的3000元錢的綢緞皮貨……并不是在星期日買的。大家都有一些……”朱樹森抓住這個(gè)“話柄”,連忙追問李宗侗有關(guān)細(xì)節(jié)。
原來,“處分物品”時(shí)為了促銷,故宮方面規(guī)定購(gòu)買2000元以上者打七五折,購(gòu)買3000元以上者打七折。李宗侗起初買了二三百元皮貨,后來又買了二千五六百元東西,尹起文便建議他把兩次購(gòu)物的錢算在一起,這樣可以打七折。李宗侗一琢磨能省點(diǎn)兒錢,便欣然應(yīng)允,他買東西那天也確實(shí)不是公開售賣日。
其實(shí),這并不是什么大事。頂多只能算程序瑕疵,絕對(duì)不算違法,但在朱樹森的追問下,李宗侗竟然支支吾吾道:“我……我……我記不大清楚了。”當(dāng)時(shí)也在場(chǎng)的吳瀛見李宗侗這副表現(xiàn)十分氣惱。事后他對(duì)李宗侗說:“物品公開發(fā)賣,為什么你買不得呢?你今天不該吞吐,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什么叫‘記不清’呢?你顯得軟弱心虛。這事昨日他們預(yù)先有接洽是無疑的!”
吳瀛所料不虛,尹起文正是崔振華介紹來故宮工作的。上一次,因?yàn)闊o憑無據(jù),檢舉落了個(gè)空。這一次,他們?cè)诎醽碜罡叻ㄔ旱耐瑫r(shí),還從故宮內(nèi)部挖了許多黑材料。
不久前,故宮博物院會(huì)計(jì)科職員秦漢功因沾染不良嗜好,被故宮免職。他向張繼夫婦告發(fā),會(huì)計(jì)科負(fù)責(zé)人蕭登青趕著辦理積壓數(shù)年的報(bào)銷,讓文具店老板改開了幾張單據(jù),做假賬。
根據(jù)這個(gè)爆料,朱樹森查賬后,發(fā)現(xiàn)蕭登青“虛報(bào)賬目”一說是子虛烏有。很快,朱樹森便返回了南京。
1932年日本人的勢(shì)力已經(jīng)逼近平津,為保國(guó)寶無虞,故宮人開始醞釀“國(guó)寶南遷”事宜。如今看來,“國(guó)寶南遷”在戰(zhàn)亂年代保全了中華民族的文脈,無疑是明智之舉。但在當(dāng)時(shí),無論是社會(huì)上還是故宮內(nèi)部,反對(duì)的聲音都非常大。吳瀛就曾開誠(chéng)布公地表示:“古物一出神武門的圈子,問題非常多,責(zé)任既重,閑話也多。”不過,在易培基的堅(jiān)持下,第一批國(guó)寶還是上路了。
朱樹森造訪故宮時(shí),第一批國(guó)寶剛順利運(yùn)抵南京不久。易培基、李煜瀛等人以為,發(fā)難者是沖著“國(guó)寶南遷”來的。不過,隨后從南京發(fā)來的一封電報(bào),令他們恍然大悟,原來?yè)v鬼的是張繼夫婦。
一日,電報(bào)局將一封寫著“長(zhǎng)安飯店,朱樹森先生”的電報(bào)送到了吳瀛家。朱樹森當(dāng)時(shí)已返回南京,電報(bào)無法投遞。由于電報(bào)局的工作人員是吳瀛的朋友,知道朱樹森是為故宮博物院而來,因此便將電報(bào)送給了吳瀛。電報(bào)上這樣寫道:
佳電緩辦,即查古物有停運(yùn)否?俾轉(zhuǎn)政院,勿藉案停運(yùn)。張囑尹即來,費(fèi)先籌給,程已保外否?并電復(fù)!烈蒸。
故宮眾人分析,發(fā)電人“烈”,應(yīng)該是最高法院檢察長(zhǎng)鄭烈,“張”即張繼,“尹”則是尹起文。鄭烈是張繼的門生,他能謀得最高法院檢察長(zhǎng)一職多虧張繼提拔。此番恩主有事相求,他自然是不遺余力。尹起文是崔振華介紹到故宮工作的,張繼讓尹起文速來南京,自然是要商議下一步的行動(dòng)。
故宮博物院的締造者之一吳稚暉看到這封電報(bào)后,怒不可遏。張繼夫婦一回北平,他便拿著電報(bào)去找他們對(duì)質(zhì)。面對(duì)吳稚暉的質(zhì)問,崔振華惱羞成怒,供認(rèn)不諱,還完全不顧顏面地撒潑起來。這樣一來,雙方矛盾完全公開化。
易培基辭職
接連遭張繼夫婦兩次構(gòu)陷,易培基忍無可忍,決定反擊。易培基的學(xué)生、當(dāng)時(shí)正在故宮博物院任職的余蓋回憶,就在這時(shí)秦漢功見勢(shì)不妙,見風(fēng)使舵,將張繼夫婦給他賄金,讓他誣告易培基的事和盤托出。易培基令秦漢功寫了一份坦白書。因?yàn)榕略鈴埨^夫婦報(bào)復(fù),秦漢功在易培基的安排下搬到了上海,再也不敢露面。這樣,易培基手里就握有了張繼夫婦構(gòu)陷他的證據(jù)。
1933年10月,易培基向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huì)提出反訴,詳細(xì)說明了張繼夫婦聯(lián)合鄭烈、朱樹森,買通證人,蓄意誣陷他的經(jīng)過。與此同時(shí),他將這篇文章投書《申報(bào)》《大公報(bào)》等媒體,還編印了一本名為《故宮訟案寫真》的小冊(cè)子到處散發(fā)。然而,他的種種努力都石沉大海,并未引起多大反響。
易培基反擊未成,張繼一方更加有恃無恐。此時(shí),李宗侗早已借護(hù)送古物南下的機(jī)會(huì),躲到了上海,并且向故宮理事會(huì)提出辭去秘書長(zhǎng)一職。張繼夫婦看出李宗侗生性膽小,于是請(qǐng)故宮博物院副院長(zhǎng)馬衡和北平圖書館館長(zhǎng)袁同禮找李宗侗調(diào)停。馬衡和袁同禮轉(zhuǎn)達(dá)了張繼夫婦的意思:“只要易院長(zhǎng)辭職,以后雙方都不攻訐,萬事全休。”早已六神無主的李宗侗,一聽此言立馬答應(yīng)去說服易培基。
10月15日,吳瀛在報(bào)紙上看到了易培基已經(jīng)向故宮理事會(huì)辭去院長(zhǎng)一職的消息。吳瀛替易培基抱不平,易培基也是追隨孫中山革命的國(guó)民黨元老,何以讓人擠兌成這樣?在案情沒有結(jié)論的情況下,提出辭職,反而讓人覺得他做賊心虛。易培基無奈地對(duì)吳瀛說:“我本不肯辭院長(zhǎng),玄伯(即李宗侗)鬧了許久,我并沒有聽他的。14日那天晚上,我已經(jīng)睡了,曾經(jīng)吩咐傭人不要他進(jìn)來。他不由分說地闖進(jìn)房來,我是9時(shí)要睡覺的,他糾纏到12時(shí)還不走。我生氣的同時(shí)也實(shí)在受不了,方才說:‘聽你的罷!’他就替我打了一個(gè)電報(bào)辭職,我真沒辦法啊!”
然而,易培基的息事寧人,并沒有讓事態(tài)平息下來。1934年10月,江寧地方法院對(duì)易培基、李宗侗、蕭瑜、秦漢功等9人提起公訴。一年前,南京地方法院對(duì)易李的指控僅是違法舞弊,而此次竟然升格為“盜賣古物”。起訴書中提到,易培基借“國(guó)寶南遷”之機(jī),調(diào)換珠寶,占為己有。
含冤身死
1934年11月4日,全國(guó)各大報(bào)紙都刊登了江寧地方法院對(duì)易培基的起訴書。“國(guó)寶南遷”期間,故宮博物院院長(zhǎng)竟“監(jiān)守自盜”!一下子將故宮博物院推向了輿論的風(fēng)暴眼。
一時(shí)間,各種假消息見諸報(bào)端。有的報(bào)道“江寧地方法院通緝易培基、李宗侗;易培基畏罪逃往國(guó)外”;有的報(bào)道“蕭瑜(原農(nóng)礦部次長(zhǎng))代易培基盜運(yùn)寶物往法國(guó),在馬賽被法國(guó)海關(guān)查出扣留”。而另一方面,易培基等人的辯白文章,卻因沒有檢察機(jī)關(guān)核準(zhǔn),而屢屢被各地報(bào)館退回。
易培基和李宗侗自辭職后,便住進(jìn)上海的租界區(qū)。雖然暫時(shí)不用擔(dān)心安全問題,但是他們?cè)诒逼健⑸虾5姆慨a(chǎn)均被查封,財(cái)產(chǎn)也被沒收了。
吳稚暉、李煜瀛等人沒想到,一場(chǎng)人事糾紛竟會(huì)鬧得沸反盈天。吳稚暉憤憤不平地對(duì)張繼說:“寅村(易培基的別號(hào))今后居滬養(yǎng)病,不再與聞博物院事。你為什么又憑空捏造寅村逃往國(guó)外的消息來?真是荒謬!”吳瀛、余蓋等人紛紛勸易培基反訴。
然而,易培基對(duì)形勢(shì)的認(rèn)識(shí),則更清醒。他一語(yǔ)道破:“此案是政治問題,非待政治好轉(zhuǎn),沒有辯訴平反的希望。”江寧地方法院對(duì)他發(fā)出通緝令時(shí),他曾經(jīng)咨詢過法律專家。他們均認(rèn)為,當(dāng)時(shí)的中國(guó)司法實(shí)際上是有權(quán)有勢(shì)者操縱的工具。易培基若投案反訴,法院可以將他羈押偵查。一事辯清,另生他事,東拉西扯,纏訟不休,不把他拖到皮焦骨枯,誓不罷休。當(dāng)時(shí)易培基已經(jīng)是肺病晚期,經(jīng)受不起無休無止的官司。
1937年夏,吳瀛收到長(zhǎng)女吳珊的信,得知易培基已經(jīng)病入膏肓。他連忙從南京趕往上海去見老友最后一面。當(dāng)時(shí)易培基還幻想著,希望能有“政治解決”冤案的一天。可吳瀛知道,易培基是不可能活著看到冤案昭雪了。
果然,吳瀛回到南京不久,就傳來了易培基的死訊。當(dāng)時(shí),日軍的鐵蹄已踏上上海,滬寧已不通行。易培基離世時(shí),身邊極為寥落,只有吳稚暉和吳珊代為料理后事。
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國(guó)民黨大員們忙著到敵占區(qū)撈錢,對(duì)易培基的未了之案,絕口不提。直到1947年,張繼暴死,法院才對(duì)“易案”作出不予受理的結(jié)論。
沉冤昭雪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成立,吳瀛看到了冤案平反的希望。
1913年,易培基擔(dān)任過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xué)校校長(zhǎng)。當(dāng)時(shí),他對(duì)還是學(xué)生的毛澤東青眼有加。1920年,他聘毛澤東在一師任教,并支持他的共產(chǎn)主義運(yùn)動(dòng)。后來,毛澤東向同窗好友周世釗說:“我那時(shí)能在一師范搞教育,還能在軍閥惡勢(shì)力下宣傳馬列、組建黨團(tuán),多虧易培基先生這個(gè)后臺(tái)老板硬喲!”
吳瀛認(rèn)為,毛澤東與易培基是故人,一定了解他的道德操守。因此,新中國(guó)剛剛成立,他便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替易培基鳴冤。
新中國(guó)肇始,百?gòu)U待興,要忙的事情千頭萬緒,但毛澤東仍立即對(duì)“易案”給予了關(guān)注。他將吳瀛的陳情信轉(zhuǎn)批給了時(shí)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zhǎng)的董必武。論起來,董必武與易培基也是老相識(shí),辛亥革命時(shí),他們同在湖北軍政府共過事。對(duì)于吳瀛的信,董必武也非常重視。
然而,與“易案”有關(guān)的雙方當(dāng)事人——易培基、張繼都已不在人世,崔振華、鄭烈、李宗侗去了臺(tái)灣,證據(jù)也多毀于戰(zhàn)火。怎樣才能平反昭雪呢?
毛澤東、董必武都不主張走法律途徑,而是希望在輿論上給易培基一個(gè)說法。
1950年4月,上海市委統(tǒng)戰(zhàn)部秘書長(zhǎng)周而復(fù)登門造訪吳瀛,把馬衡新編訂的《關(guān)于鑒別書畫的問題》一文交給他。馬衡在這篇文章后面加了一篇言簡(jiǎn)意賅的“附識(shí)”:
此文為易案而作。時(shí)在民國(guó)廿五年,南京地方法院傳易寅村不到,因以重金雇用落魄畫家黃賓虹,審查故宮書畫及其他古物。凡涉疑似者,皆封存之。法院發(fā)言人且作武斷之語(yǔ)曰:帝王之家收藏不得有贗品,有則必為易培基盜換無疑。蓋欲以“莫須有”三字,為缺席裁判之章本也。余于廿二年秋,被命繼任院事。時(shí)“盜寶案”轟動(dòng)全國(guó),黑白混淆,一若故宮中人,無一非穿窬之流者。余生平愛惜羽毛,豈肯投入漩渦,但屢辭不獲,乃提出條件,只理院事,不問易案。因請(qǐng)重點(diǎn)文物,別立清冊(cè),以畫清前后責(zé)任。后聞黃賓虹鑒別顢頇,有絕無問題之精品,亦被封存者。乃草此小文,以應(yīng)商務(wù)印書館之征。翌年(廿六年),教育部召開全國(guó)美術(shù)展覽會(huì),邀故宮參加,故宮不便與法院作正面之沖突,乃將被封存者酌列數(shù)件,請(qǐng)教育部要求法院?jiǎn)⒎猓_陳列,至是法院大窘,始悟?yàn)辄S所誤。亟責(zé)其復(fù)審,因是得免禁錮者,竟有數(shù)百件之多。時(shí)此文甫發(fā)表或亦與有力歟。著者附識(shí)。
一九五〇年一月
馬衡在這篇小文中,明確表示“易案”乃是一場(chǎng)冤案,算是在輿論上公開為易培基平了反。兩個(gè)月后,吳瀛在《大公報(bào)》上發(fā)表了《談文物處理工作》一文,再次聲明“故宮盜寶案”是一樁“憑空捏造”的冤案。至此,這樁歷時(shí)17年之久的冤案,終于塵埃落定。
(責(zé)編/林佳 來源/《“故宮盜寶案”始末》,黃加佳/文,《北京日?qǐng)?bào)》2017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