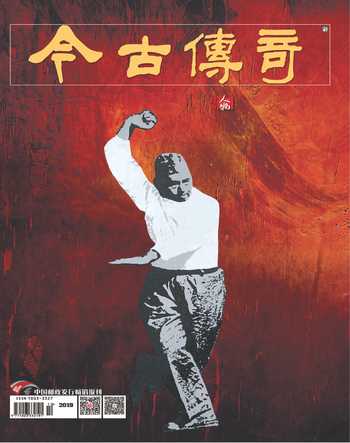美國國會的打架史
胡文利
禍從口出,從單挑到群毆
“國會暴力是因為當時全美國上下都熱衷暴力。政客‘英勇無畏’的品質能吸引不少選民。美國人知道自己選擇的政治人物是什么樣的。”
美國國會大廈標志性的穹頂之下,來自50個州的“民意代表”們仿佛永遠風度翩翩。參眾兩院500多名議員以紳士自居,就算意見相左,也講究“君子動口不動手”。
然而,大概一個半世紀前,籠罩著國會山的卻是一股“叢林法則”的氣息:斗毆乃至決斗屬于家常便飯,流血事件時有發生,議員們隨身攜帶武器以自保。他們的暴力斗爭被視為南北戰爭的預演,在一次次扭打和兵戎相見中,美國社會的新秩序逐步成型。
這是一段血腥、荒誕而鮮為人知的歷史。談到自己的新書《血腥之地:國會暴力和通往內戰之路》,耶魯大學歷史教授喬安妮·弗里曼表示,美國國會一度被混沌統治。“在藝術作品中,議員們穿著長款黑色禮服正襟危坐,言語交鋒間不失氣度。”弗里曼告訴美國《史密森尼》雜志,“事實上,彼時的國會根本沒有如此文明,而是一片充滿暴力的原始森林。”
奴隸制是國會暴力的根源
19世紀30至50年代,美國議員們身負“十八般兵器”上班,這些家伙絕非擺設。《血腥之地:國會暴力和通往內戰之路》一書描述道:“從杰克遜政府到林肯政府,幾乎每次會議都會由唇槍舌戰發展到報以老拳。議員們一言不合就開打,輕則棍棒相加,重則真刀真槍。他們肆無忌憚地群毆,甚至在街頭貼身肉搏。沒有轉化為暴力行動的恫嚇、威脅更是不計其數。”
沖突通常始于辯論。當口舌之爭逐步升級,臟話脫口而出,政治議題便化為私人恩怨。周圍的人要么起哄,要么站在桌上看熱鬧。很快,國會里“響起了怒吼和慘叫”。
1842年,田納西州參議員托馬斯·阿諾德在鬼門關前走了一遭。兩名來自蓄奴州的議員悄悄逼近,其中一人冷不丁地抽出獵刀,把冰冷鋒利的刀刃架在阿諾德脖子上,威脅說要把他的喉嚨割斷。
1850年,怒火中燒的密西西比州參議員亨利·富特對準正在臺上演講的密蘇里州參議員托馬斯·本頓扣動了扳機。他早就盤算好了襲擊方案——先奔向過道,再朝目標開火,以免傷及無辜。幸虧富特槍法不佳,沒有擊中目標,手槍隨即被旁人奪下。
許多暴力事件的根源是奴隸制存廢之爭。據美國《大西洋月刊》記載,1842年,廢奴派議員西奧多·韋爾德描述了約翰·亞當斯引起的風波。“幾十名蓄奴派大呼小叫:‘一派胡言!’‘廢話!’他們團團圍住亞當斯,叫他閉嘴。亞當斯冷冷地回應道:‘我知道你們的痛腳在哪兒,我會更用力地踩。’”好在,作為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的長子及第六任總統,亞當斯在國會享有較高威望,沒人真敢對他動粗。
1840年以前,任何反對奴隸制的言論在美國南方都是違法的,民眾并不清楚上層的分歧。然而,當立法者們開始仔細討論這個問題時,矛盾就壓不住了。“北方佬不喜歡決斗,南方佬認為他們是膽小鬼。用弗里曼的話說,這導致‘欺壓’盛行——南方佬能動手絕不動口,以為北方佬會屈服于鐵拳之下。另外,擔心失去‘財產’(黑奴),也促使他們成為更崇尚暴力的一方。”美國《紐約時報》稱。
禍從口出,從單挑到群毆
歷數林林總總的國會暴力事件,最出名的要數1856年南卡羅來納州參議員普雷斯頓·布魯克斯和馬薩諸塞州參議員查爾斯·薩姆納的對手戲。前者用鐵頭杖把赤手空拳的后者放倒在地,在一分鐘內猛擊40多下,險些要了對方的命。
薩姆納挨揍是禍從口出。在當天的國會發言環節,他沖著《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的制定者、參議員斯蒂芬·道格拉斯和安德魯·巴特勒連發“嘴炮”。該法案允許這兩個州的拓荒者自行決定是否蓄奴,但薩姆納并沒有抨擊法案“腦殘”,而是把矛頭指向立法者。他大罵道格拉斯是“嘮嘮叨叨的死胖子,沒名沒姓的畜生”,諷刺巴特勒“找了個長相丑陋的情婦,把牛糞當鮮花”。
道格拉斯沒有當場發作,而是私下跟別人說:“這個傻瓜會死在另一個傻瓜手里。”果然,有人坐不住了。巴特勒當時不在場,這番侮辱性言論被他的親戚布魯克斯一字不差地聽到。布魯克斯當即提出跟薩姆納決斗,南卡羅來納州議員勞倫斯·基特火上澆油,說薩姆納“不配得到這種待遇”。3天后,他倆在一個會議廳里堵住了薩姆納。基特持槍守在門口,布魯克斯揮杖把薩姆納打了個半死。由于太用力,手杖都斷了。
消息傳開,兩位當事人成了記者筆下的英雄。親北方的《紐約時報》雇了一名拳擊冠軍擔任駐國會記者,為廢奴派壯膽。南方的擁護者則給布魯克斯寄去一根又一根手杖。“唯一的遺憾是,他用的是手杖而非抽打奴隸的鞭子。”一些南方報刊評論道。
矛盾愈演愈烈,單挑發展為群毆。1858年的一天,南北雙方爭論到凌晨2時,耗盡了體力和耐心。兩派議員先是人身攻擊,然后拳腳相加。一時間,國會大堂成了角斗場:共和黨和少數黨派聯合起來對付民主黨,民主黨黨首斯皮克·奧爾氣急敗壞地敲著木槌,沒人理會;警衛官亞當·格洛斯布倫納在推搡中狼狽地高舉著白宮權杖,徒勞無功地維持秩序;共和黨人約翰·波特揪住民主黨人威廉·巴克斯達爾的腦袋,把后者的假發扯了下來,露出閃亮的光頭……人群頓時爆發出哄堂大笑,打斗停了下來。
一名密歇根州法官這樣描述自己的見聞:“一走進大廳,我就看到一個人拿著手杖,把另一個人追得滿屋亂竄。看到這一幕我就放心了——沒錯,這里是華盛頓。”
全面戰爭的導火索
國會山烏煙瘴氣,但主流媒體起初并未曝光亂象,原因之一是怕惹禍上身——好些記者品嘗過議員的拳頭,還有人的手指差點兒被咬斷。結果,民眾對國會里的暴力幾乎一無所知。
局面的改變歸功于電報。曾幾何時,議員的發言要過很長時間才能傳到選民耳中。電報大規模應用后,新聞開始“以光速傳播”。記者們馬不停蹄地寫出一篇又一篇專題報道,暴力成為新聞,新聞又催生了更多暴力。議員們四處散發政治宣傳品,點燃了公眾情緒,引發了一波波抗議游行。就這樣,憲政危機愈演愈烈,戰爭一觸即發。
1859年南北戰爭前夕,加利福尼亞州首席法官戴維·特里和該州參議員戴維·布羅德里克發生嚴重摩擦。兩人來自同一地區、同一黨派,但在蓄奴問題上政見不一。廢奴派的布羅德里克稱蓄奴派的特里為“無恥混蛋”,后者馬上向前者提出以火器決斗。
有那么一段時間,決斗是美國政客最常見的死因。1838年,肯塔基州議員威廉·格雷夫斯殺死緬因州議員喬納森·西里后,國會宣布在華盛頓決斗為非法,可這項法案形同虛設。
史學家認為,特里的槍是找下屬借的。而布羅德里克在扳機上動了手腳,輕輕一碰就能發射。不過,他沒能逃過一劫,在決斗中被槍法精準的特里打死。布羅德里克之死將蓄奴派和廢奴派的矛盾推向白熱化,導致南北戰爭爆發。
《紐約時報》稱,保持對話是民主制度的核心和靈魂,但當時的國會議員和公眾都沒有做到。國會淪為政治派系的角力場,喪失了應有功能。媒體借助電報火上澆油,政府威望搖搖欲墜,敵對情緒在民間蔓延……一切都是災難的前奏,戰爭在所難免。
政客的舉動符合大眾審美
國會山的一幕幕荒誕劇上演時,美國建國不足百年,社會制度尚未完善。印第安人要么被屠殺,要么流離失所;沖突和暴動時時發生,原因多種多樣:支持廢奴、反對廢奴,支持原住民、反對原住民……奴隸制更是充滿暴力和血腥。
大環境如是,政客們無法獨善其身。“constitution center”網站文章稱,“杖刑”風波后,主謀布魯克斯被國會處以300美元罰款,引咎辭職,但很快就重新當選。后來有人上門要求決斗,但布魯克斯在最后關頭退縮了。被施暴者薩姆納在病床上躺了很久,痊愈后整整3年沒踏進國會大門,他“空缺的席位象征著國家的分裂”。
1998年,特里和布羅德里克決斗用的武器以34500美元的高價被賣出。這是兩支比利時生產的步槍,口徑為0.58英寸(約14.7毫米),曾在南北戰爭中被廣泛使用。和步槍擺在一起的還有銅質火藥筒、步槍支架等,這些老氣橫秋的物件是動蕩年代的見證。
“國會暴力是因為當時全美國上下都熱衷暴力。”弗里曼告訴《史密森尼》雜志,“因此,政客‘英勇無畏’的品質能吸引不少選民,人們喜歡投票給最‘硬漢’的議員。實際上,美國人知道自己選擇的政治人物是什么樣的。”
就這一點而言,1850年的美國與2018年的美國似乎沒有什么不同。正如一名讀者在《華盛頓郵報》相關報道下的留言:“我投票給特朗普是因為他能替我做我想做的事。”
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從未遠去。今天的華盛頓和平得多,但黨派之間乃至黨派內部的裂痕有急劇加深的勢頭。《紐約時報》以借古諷今的語氣感慨道:“同樣的故事總是一再上演,雖然換了時間,換了地點,換了原因,但總能找到驚人的相似之處。我們必須改進對話能力,讓溝通更有效、更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