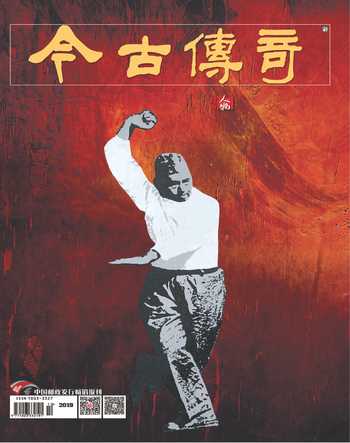黃興與“香山女俠”徐宗漢
陳恒才 楊彥華
既是夫妻,更是戰友
黃興在繁忙的軍務中,寫信給徐宗漢:“吾責至大、至危、至暫,汝責至細、至久、至難,然則汝之責任艱巨于吾乎!”
一生投入革命事業的黃興贏得了世人的無限敬仰,而他身邊那位鼎力相助的革命伴侶徐宗漢也同樣值得記憶與懷念。
黃興一生有過兩次婚姻:1891年秋,奉父母之命,與廖淡如(1873-1939,湖南長沙人,鄉紳廖星舫之女)結婚,這是一段包辦婚姻,婚后兩人相敬如賓,育有6個子女;辛亥革命前期,黃興與“香山女俠”徐宗漢結為患難夫妻,育有兩子。其中,第二段婚姻,成為載入革命史冊的傳奇佳話。
孫中山:“你有如此出色的能力,應該滿天飛,去籌錢,去革命!”
徐宗漢,原名佩萱,原籍廣東香山,于1877年出身一個大戶人家。1894年,經雙方父母說合,與兩廣總督洋務委員李慶春之子李晉一結婚。不久,李晉一因病身故,徐佩萱攜兒女返回廣東。
1905年,革命浪潮翻涌,仁人志士紛紛投身于這股洪流之中。徐佩萱的姐姐徐佩蘭不顧家庭的阻撓,投身革命,只身赴南洋檳榔嶼一家華僑學校執教,并且來信約徐佩萱前去共事。徐佩萱當即將兒女托付給家人,孤身一人遠赴南洋。正是在這里,機緣巧合下,徐佩萱與黃興相識。
當時,黃興與孫中山為革命而來向華僑籌款,到了南洋人生地不熟,又聽不懂馬來語。已學會馬來語的徐佩萱,便自告奮勇當起了向導。更有趣的是,有著獨特語言天賦的徐佩萱,很快就學會了湖南話,能在粵語和湖南話之間切換自如,成為孫中山和黃興之間的“同聲翻譯”。
臨別時,孫中山拍著徐佩萱的肩膀說道:“你有如此出色的能力,應該滿天飛,去籌錢,去革命!”
也許受到“孫黃”等人的影響,徐佩萱很快加入在檳榔嶼成立的同盟會分會,成為一名核心黨員。不久,同盟會急需在廣州建立分機關,徐佩萱應孫中山和黃興之請,立刻返回廣州,主持其事。
廣州起義的絕大部分炸藥,都是由徐宗漢組織運送
1908年秋,徐佩萱從檳榔嶼取道香港返回廣州。因為從事革命活動,她怕連累家人,就改名徐宗漢,搬出了家里,并自辟門面,與畫家高劍父、革命志士潘達微等人創設審美畫會、受貞閣裱畫店,掩護革命工作。
當時,國內革命形勢猶如箭在弦上,那些鐵骨錚錚的硬漢已做好了隨時赴死的準備。剛回到廣州,徐宗漢便接到首個任務——為籌備廣州新軍起義,徐宗漢與陳淑子(胡漢民夫人)、李自屏(馮自由夫人)從香港取水路秘密攜帶軍火進入廣州。
行囊中裝滿了炸藥子彈,被褥內藏有青天白日旗,這些東西猶如一顆定時炸彈,讓陳淑子、李自屏坐臥不寧,唯有徐宗漢,一路滔滔不絕地論服裝、講化妝、談姨太太爭風吃醋一類的市井話題,分散敵人的注意力。
在運送的這批槍械彈藥中,體積大又不可重壓的手榴彈、炸藥的裝運較為麻煩。徐宗漢索性將手榴彈成捆成捆地包好,藏在一只只馬桶內。有一次,碰上突然檢查,倉促中徐宗漢只得坐在馬桶上。
就在廣州起義前夕,為了將彈藥順利運進廣州市內,徐宗漢借一家顏料作坊為掩護,自己則扮成作坊外嫁的新娘。200多名革命戰士扮作迎親隊伍,在喧天的鑼鼓和鞭炮聲中,取出已先期裝在顏料罐里的武器零配件,洗凈后以明辦嫁妝、暗運武器的辦法,先將武器運至廣州市,再由別的同志將武器彈藥分送至各處。
黃興很難想象,時隔4年,徐宗漢已經從一名普通的婦女,蛻變為革命志士,被稱作“香山女俠”。黃興更沒有想到的是,在廣州起義激戰中的絕大部分炸藥,都是由徐宗漢領導的分機關組裝及運送的。
黃興到上海主持和談,徐宗漢恐和議不成,組織“北伐炸彈隊”
廣州起義失敗,清軍草木皆兵。廣州全城戒嚴,清軍四處盤查。4月29日,徐宗漢外出買了一件長衫,為黃興改裝,在醫生張竹君的陪同下,乘“哈德安輪”逃到香港。
據說當時的客輪已沒有單獨的房間,徐宗漢便將黃興安置在廳中梳花椅上裝睡,自己則靠坐其旁,以身體掩護黃興。到了香港,黃興入雅麗氏醫院做手術,但按醫院的要求,做手術需要家屬簽字。或已看出兩人的心思,張竹君便故意慫恿,最后徐宗漢以黃興妻子的名義簽字了。黃興雖然聽不懂粵語,但是已猜出八九分,感激、愛憐油然而生。
手術后,徐宗漢一直在黃興的病榻旁照料,兩人談理想、談革命、談未來。出院后,這對假夫妻很快成為了真正的夫妻,在革命同志中傳為美談。
有徐宗漢的精心照料,黃興心中因廣州起義失敗帶來的傷痛稍許撫平。武昌起義的消息很快就傳來了——宋教仁在上海聞訊,急電黃興,促速北上。1911年10月24日,黃興偕徐宗漢抵達上海。當晚,徐宗漢到《民立報》報社約宋教仁會晤,宋教仁隨徐宗漢到黃興的住處后,兩人討論當時的革命形勢,并商定黃興去武昌主持全局。
但當時上海、江蘇等地的沿江口岸仍掌握在清軍手中,因武昌起義的爆發,各路關口盤查甚嚴,黃興是被全國“通緝”的要犯,怎樣才能到達武漢?
關鍵時刻,徐宗漢又想到了當時在上海開設醫院的摯友張竹君。張竹君此時已有“女界梁啟超”之稱。昔日在廣州時,徐宗漢曾變賣嫁妝支持張竹君興辦福利醫院。這一次,張竹君也鼎力相助。在張竹君的發動下,一個由中外人士參加的紅十字救傷隊,很快啟程赴武漢戰地服務。黃興扮作醫療人員,宋教仁、陳果夫等亦隨救傷隊前行,于10月28日午后順利到達武漢。
黃興渡江親臨漢陽前線,率領革命軍與清軍奮戰了20多天。徐宗漢則冒著炮火,投入救護傷兵工作,并協助張竹君在漢陽設立臨時醫院。后清軍反攻,漢陽失守,黃興被困,清軍封鎖長江。徐宗漢與張竹君用紅十字會一艘渡船,護送黃興從漢陽渡至武昌江岸,才得以脫險。
11月28日,黃興到上海主持和談,而徐宗漢恐和議不成,便組織“北伐炸彈隊”以對付清廷,其肝膽俠義,不讓須眉。
黃興寫信道:“汝之責任艱巨于吾乎”
1912年1月1日,黃興在南京臨時政府任陸軍總長。徐宗漢開始退居“幕后”,以為從此可以哺兒育女,順便參加一些有關婦女界的政治活動。臨時稽勘局局長馮自由還聘徐宗漢為該局名譽審議。
當時,廣東北伐軍姚雨平部從徐州前線回南京時,帶回戰時難童200多人。黃興通知陸軍部副官處覓民房收容,成立南京貧兒教養院,由徐宗漢負責該院工作。徐宗漢成為中國貧兒教育的開創者。
但黃興的事業乃至民族的事業并非一帆風順。1913年,袁世凱撕毀臨時約法,黃興等革命戰士開始了長達多年的討袁運動。當年7月,黃興在南京主持討袁工作,在繁忙的軍務中,寫信給在上海的徐宗漢:“弟(宗漢)在家保育兒輩,我極心感……吾責至大、至危、至暫,汝責至細、至久、至難,然則汝之責任艱巨于吾乎!”這是黃興寫給徐宗漢家書中最為感人的一段。
第一次討袁的“二次革命”很快兵敗,黃興經由上海逃往香港,亡命日本,于1914年赴美國。由于連年征戰奔波,操勞過度,加之革命事業坎坷,憂憤有加,抵美后黃興肝病吐血,暫時在費城郊外一家醫院療養,命長子黃一歐伴送徐宗漢來美國相敘。徐宗漢聞訊,即刻兼程赴美,隨侍黃興,料理其生活起居,并協助做一些接待、抄寫工作,以盡量減輕黃興的負擔。
1916年6月6日,在全國討袁護國的高潮中,袁世凱暴卒,黃興、徐宗漢于7月8日返回上海。各界人士殷切期望黃興挑起建國重擔,但黃興積勞成疾,病魔纏身,于10月31日不幸逝世。
孫中山勉勵她出山,去完成黃興未竟的事業
黃興逝世后,悲痛的徐宗漢開始不問政治,加之江蘇地區落入北洋軍閥手中,她也不能回南京貧兒院主持工作,于是息影上海,一心撫育遺孤。
那些在烽火連天后涌入上海的孤兒,觸動了徐宗漢的熱心腸。在張竹君的幫助下,徐宗漢設立了上海貧兒教養院。在辦貧兒院期間,徐宗漢也曾在“五四”時期參與發起上海女界聯合會,但她始終把貧兒院工作放在首位,準備直至終老。
1925年,病榻上的孫中山豪情滿懷,勉勵徐宗漢重出“江湖”,至少要辦工廠,給長大的孩子受教育和工作的機會,也算是完成黃興未竟的事業。當時,徐宗漢已年過半百,她已不可能像年輕時那樣背著炸藥“滿天飛”,但她還是動搖了。此后,徐宗漢遠赴美國、巴西、古巴、秘魯等地募款。
抗日戰爭爆發后,徐宗漢不顧年事已高和患有嚴重的心臟病,于1938年初,親自帶領部分貧兒出國,到暹羅(今泰國)看望華僑,一邊為貧兒募捐,一邊宣傳抗日救國,呼吁僑胞支持抗戰事業。
她對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的英勇斗爭,由衷表示欽佩。1940年,徐宗漢回國后移居重慶,此后經常接觸共產黨人。她和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等都很接近,常有來往。
抗戰初期,黃興幼子黃乃(黃興與廖淡如所生)在延安抗大學習。徐宗漢曾托周恩來、鄧穎超給他帶去日常生活用品和一封親筆信,信上只有一句話:“努力學習,后會有期!”鄧穎超在延安把東西交給黃乃時說:“我們在重慶時跟你繼母有來往,她請我們吃飯,表現比我們還‘左’,人家說她是瘋婆子!”
鄧穎超為何這樣說?原來,耳聞目睹國民黨政府消極抗戰、貪贓枉法、魚肉人民的行徑,徐宗漢十分不滿;對那些禍國殃民的軍閥、官僚政客,更因憤恨而漫罵、鞭笞,思想逐漸變得激進。
至性之人必有至情。一生肝膽俠義的徐宗漢不僅是一名出色的革命者,也是一位達觀、深明大義的賢妻良母。
南京臨時革命政府成立后,黃興將母親易太夫人與元配廖淡如接到南京,徐宗漢立即去拜見。按湖南人習俗,徐宗漢向易太夫人、廖淡如“抬茶”,并請示留在黃興身邊,全然不計自己在家的地位和名分,可見她對黃興的至深感情。
1944年3月8日,徐宗漢在做好了貧兒院最后一項工作安排后,安然地閉上了雙眼,享年67歲。當天恰是國際婦女節,這或許是上天做出的一次巧妙的安排。據說,如今每逢婦女節,黃興與徐宗漢在上海武康路393號的黃公館門口,還有許多市民為她送來鮮花,以表永恒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