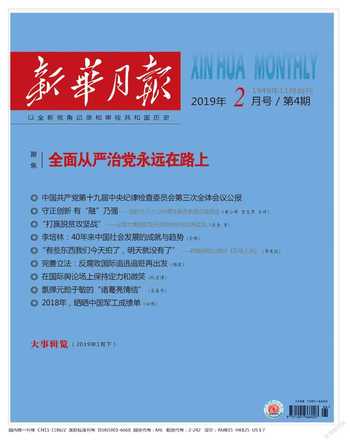澳大利亞危險罪犯立法述評
王濤
澳大利亞昆士蘭州于2003年制定了《危險罪犯(性犯罪分子)法》(以下簡稱《危險罪犯法》)。該法的制定源于昆士蘭州一個臭名昭著的性犯罪累犯Ferguson。其于1987年因綁架、性侵3名兒童被判入獄14年。Ferguson的刑滿出獄,讓澳大利亞社會產生巨大的恐慌,他也的確在出獄后再次犯案。Ferguson出獄對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最終促使昆士蘭州議會通過了上述法律。
《危險罪犯法》的主要內容
《危險罪犯法》第3條明確了該法的主要目的在以下兩點:
一是對于特定類別的罪犯進行繼續羈押或監督以確保社會安全;二是對于特定類別的罪犯提供持續的控制、關懷和治療措施以促進他們改過自新。該法對于“罪犯”的定義為:因實施嚴重性犯罪被處以一定刑期監禁或所實施犯罪中包含因嚴重性犯罪被處以一定刑期監禁的罪犯。該法第5條規定,州總檢察長可以根據相關程序在該罪犯刑期的最后6個月內向法院提出繼續羈押或監督申請,由法院進行初步聽證后決定該罪犯是否對于社會構成危險。
初步聽證中,檢方和罪犯雙方都可以向法院提交各自意見以及證明各自主張的證據。在初步聽證中,如果法院認為存在合理理由認定該罪犯的釋放對于社會將構成嚴重危險,應當確定日期開展正式聽證。正式聽證前,法院可聘請精神病學專家對罪犯本人進行風險評估,州總檢察長應就罪犯危險性問題向法院提交正式報告,原案受害人有權就該罪犯的危險性發表自己的意見。
《危險罪犯法》第13(2)條規定,罪犯滿足以下條件時,法院會認定罪犯對社會構成重大危險:當罪犯獲釋或獲釋后不受監督,存在巨大的實施嚴重的性犯罪的可能。這一認定必須基于充足證據所得出的罪犯會再次實施性犯罪的高度可能性。這些證據通常包括檢方意見、精神科醫師評估意見、涉及罪犯犯罪傾向的信息、罪犯是否存在固定的犯罪行為模式、罪犯的矯正情況及其效果、罪犯的前科劣跡、罪犯再犯罪的風險以及保護社會公眾的需要等內容。
據此,法院將針對該罪犯制發繼續羈押令,將其不固定期限地羈押以繼續管控和矯治;或制發監督令,在規定相關監督條件的基礎上釋放該罪犯。如果法院制發監督令,監督令上必須載明其有效期間。該期間不得少于5年,以監督令制發或罪犯獲釋時二者中較晚者起算。
《危險罪犯法》第16條對于監督令的相關監督條件進行了規定,這類條件與社區矯正等相關措施規定的條件相似;第19B條規定了監督令的延長程序,應由總檢察長在當前令終結前6個月向法院提出延長監督令的申請,申請應當載明延長的期限、理由及依據。
《危險罪犯法》第20條規定,如果罪犯違反監督令的相關規定,地方警察和矯正官有權將向治安法官申請逮捕令,將其逮捕后交由昆士蘭州最高法院依照該法處置。
《危險罪犯法》第26條至30條規定了繼續羈押令的年度復核程序。由總檢察長向法院提出復核聽證申請,第一次復核聽證應當在繼續羈押令生效后兩年內舉行,而后的聽證應當一年舉行一次。被羈押罪犯則可以在法院完成第一次復核后的任何時間向法院提出申請,請求法院對繼續羈押令開展復核,只要法院認為該罪犯的申請與其自身的特別情況相關,便可給予聽證許可,對是否繼續羈押該罪犯作出裁決。《危險罪犯法》第31條至43條規定了上訴程序。在法院作出裁決后一個月內,總檢察長和罪犯若不服,皆有權向昆士蘭州上訴法院提出上訴。被羈押的罪犯若沒有委托代理律師,有權向法院申請親自到庭參與上訴聽證。
早期立法與現實挑戰
昆士蘭州這一預防性羈押罪犯的立法在澳大利亞并非首例。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維多利亞州和新南威爾士州已就預防性羈押罪犯進行了立法。
1994年,新南威爾士州通過了《社區保護法》,目的是將一個名叫Kable的罪犯繼續羈押在監獄中。他于1990年因誤殺其妻而入獄,原定于1995年1月刑滿釋放。然而,他在獄中不斷寫信威嚇已逝妻子的親屬,引起了民眾對于他出獄后可能再度犯罪的擔憂。《社區保護法》第3(1)條直言,其立法目的是將Kable預防性地繼續羈押在監獄,以維護社區的安全。為此,Kable提起訴訟。對此,澳大利亞高等法院(聯邦終審法院)于1996年就Kable v. 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一案作出裁決,認定《社區保護法》導致新南威爾士州最高法院行使非司法的職能,違反澳大利亞聯邦憲法的原則。高等法院擔憂,這種無罪監禁的方式將產生如下的觀感:法院成為行政權力的工具,證據規則將徹底失效。
1990年,維多利亞州通過《社區保護法》,將一名叫David的罪犯刑滿后繼續囚禁直至其1993年死于獄中。此部法律并未在違憲審查上受到當事人的挑戰,傳聞是罪犯本人缺乏法律援助方面的訴訟資金,該法后被2009年的《嚴重性犯罪分子法》所取代。
雖然澳大利亞高等法院在Kable案中認為,對某一個人實施繼續羈押的立法違背憲法,但仍指出各州可以制定通過州法院的普通司法程序實施且具有防護條款的通用的預防性羈押立法。這一觀點成為昆士蘭州《危險罪犯法》得以出臺的原因。
然而,昆士蘭州《危險罪犯法》在實施伊始,就遇到了正當性的質疑。2003年,一個名叫Fardon的罪犯成為第一個因該法被繼續羈押的人。他于1988年在犯罪假釋期間因毆打和強奸一名婦女被判14年監禁。對于法院的繼續羈押令,Fardon向昆士蘭州上訴法院提起上訴,他援引澳大利亞高等法院對Kable案的裁決,認為《危險罪犯法》侵犯了他的憲法權利而應為無效。然而,昆士蘭州上訴法院的多數意見認為,《危險罪犯法》并不違憲,該法的制定嚴格遵照了澳大利亞高等法院在Kable案裁決中的說理。上訴法院認定,《危險罪犯法》的核心要義在于社會保護而非懲罰罪犯。
Fardon不服上訴法院的裁決,向澳大利亞高等法院提出上訴。高等法院駁回了他的上訴,認為《危險罪犯法》符合聯邦憲法。高等法院認同該法的價值在于社會保護而非懲罰罪犯,該法體現的是民事屬性而非刑事屬性,并將《危險罪犯法》與Kable案中的相關立法進行了對比,指出前者所規定的司法聽證、上訴程序、年度復核等保護機制是其符合憲法原則的重要因素。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意見
在窮盡了國內一切救濟途徑的情況下,Fardon根據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下簡稱《公約》)以及《任擇議定書》的相關規定,向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提出申訴。人權委員會在其《意見書》中指出,《公約》第9條第1款明確,每一個人都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的權利,無人應受隨意逮捕或羈押;任何羈押行動應當具有法定理由,依照法定程序進行。但人權委員會認為,任何限制人身自由和安全權利的法定理由或法定程序不應當是武斷的或毀損人身權利本身。
人權委員會需考慮的問題在于《危險罪犯法》有關讓Fardon在服滿14年刑期后繼續羈押在監獄的條款是否武斷。人權委員會的回答是肯定的,并給出以下四個理由:
1.該犯在服滿14年刑期后被繼續羈押在同一個監禁體系內,實質上構成了一個新的監禁刑期,在沒有依法定罪量刑的前提下這種情況不應被允許。
2.監禁具有刑罰屬性。只有在對犯罪行為進行審判的同一個程序中,定罪和判刑方能實施。即便當事國認為程序體現民事屬性,由法院令繼續施加的后續羈押只是基于先前罪行對其未來犯罪可能的預估,但這是一個全新的司法程序,應當受到《公約》第15條第1款的規制。《危險罪犯法》在Fardon刑期屆滿前很短的時間生效,從而使他被繼續羈押,顯然該部法律對于Fardon而言溯及既往。這一情況違反了《公約》第15條第1款,使得他受到了比在其犯罪之時所能適用的刑罰更重的刑罰。
3.盡管《危險罪犯法》規定了特別程序以獲得法院令,但當事國確認這一程序僅具有民事屬性。這種情形并不符合《公約》第14條規定的公正審判和定罪量刑所必需的正當程序。
4.根據罪犯過去的罪行預估其對社會未來的風險,這一邏輯存在問題。它往往基于觀念而非事實。雖然精神病學專家對罪犯作出了評估意見,但精神病學并非一門精準的科學,法院只能根據罪犯過去的行為對其未來可能的行為進行判斷。為避免武斷,當事國應當證明除了繼續監禁沒有其他更有效的措施,特別在Fardon已經服刑14年這樣的案例中。
人身自由與預防性羈押的理性權衡
盡管澳大利亞高等法院認為《危險罪犯法》符合聯邦憲法的原則,但從比較法的角度審視,高等法院的觀點值得商榷。從殖民時代開始,澳大利亞繼受了英國的法律制度,其中包含了威斯敏斯特憲法模式。雖然澳大利亞聯邦擁有一部成文憲法,但澳大利亞的憲制仍帶有柔性憲法的特點。其中就包含著法官對憲法的解釋權,法院有權對聯邦議會和各州議會的立法進行違憲審查,而澳大利亞高等法院作為終審法院擁有對憲法的最終解釋權。
在對相關立法進行合憲性審查時,法院有權將對聯邦政府和州政府權力的限制解讀進憲法的條文。在對昆士蘭州《危險罪犯法》的審查中,澳大利亞高等法院僅從條文形式上對該法進行了審查,認為其中的司法聽證、上訴程序、年度復核等保護機制符合聯邦憲法對人身自由的保護原則,憲法確認的公民自由沒有受到侵害。
然而,在《英憲精義》中,作者戴雪告訴世人:每一個英國人(包含當時澳大利亞自治領的公民)所享有的人身自由并非源于或依賴某一具體文本的主張,個人權利是憲法的基礎而非憲法帶來的結果。人身自由的權利是指個人不受非法監禁、逮捕或其他任何方式的人身強制的權利。只有在兩種情況下,對一個人的人身權利進行限制才是正當的,即此人因犯罪應被拘捕至法院進行審判或法院判定此人有罪而其必須為此接受刑罰。
事實上,在1981年Sillery v. The Queen一案中,澳大利亞高等法院大法官墨菲就曾指出,議會的立法權不得被用以授權殘酷或不正常的刑罰措施。澳大利亞高等法院在審查那些針對某一個人的預防性羈押立法時(如Kable案)所展現的司法邏輯顯然與其在Fardon案中的說理互相矛盾。無論是針對某一個人的預防性羈押立法,還是通用性的繼續羈押立法,在本質上都是對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二者并無實質區別。《危險罪犯法》中設置的司法聽證等程序,僅具有民事程序的特點,缺乏刑事司法所強調的正當程序的屬性。
此外,在立法時確立良好的比例狀態原則是普通法的基本要求。1998年,英國樞密院司法委員會在審理來自安提瓜和巴布達的de Freitas一案中明確指出,立法和行政上的行動不應過分地或無充分理由地侵犯憲法上保證的公民權利;在衡量限制措施是否武斷或過分時,法院應當自問三個問題:第一,限制基本權利的立法目的是否具有充分的重要性;第二,為立法目的而設置的措施是否與之存在理性的關聯;第三,限制權利和自由的措施是否僅足以達成立法目的而不過分。筆者認為,昆士蘭州的《危險罪犯法》,至少難以滿足前述的第三項標準。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意見對澳大利亞沒有強制約束力,相關的立法在澳大利亞仍呈擴張趨勢,澳大利亞法律體系在這一領域未來是否會發生變革,有待進一步關注和研究。
(摘自1月25日《人民法院報》。作者單位: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