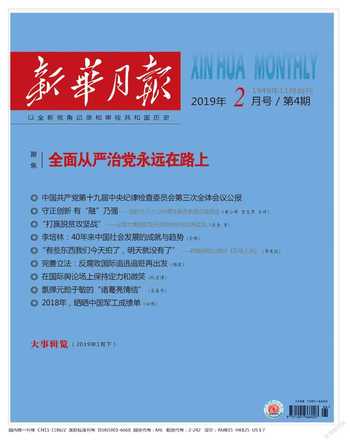戰(zhàn)爭哲思的當代共鳴
胡欣
經(jīng)過幾千年的演進,人類文明創(chuàng)造了空前的物質(zhì)繁榮,但關(guān)于爭斗的本質(zhì)卻似乎沒有改變過。
2018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100周年,戰(zhàn)爭與和平始終是人類文明發(fā)展的深刻命題。“一戰(zhàn)”前,歐洲兩大軍事集團的對立極度尖銳,而在那個地球村初顯雛形、工業(yè)文明突飛猛進的“進步時代”,進步帶來自信,自信催生盲目,積極備戰(zhàn)的各國幾乎都相信戰(zhàn)爭的正義盾牌和制勝長矛掌握在自己手中。
當時,有人單純地以為,戰(zhàn)爭已是無利可圖的暴政,新世紀的繁榮與和平乃人心所向(這種心態(tài)與當今世界那些過度迷信全球化的人有相似之處),如英國媒體稱,“所有的君主、政治家和國民都知道……戰(zhàn)爭將是一場無可估量的大災難”。遺憾的是,理性從來都不是國家的全部,理性的立場從來也都是千差萬別的。薩拉熱窩槍聲響起后,一切寄托于文明進步的信心與愿望迅速崩盤,民族主義、帝國主義、軍國主義驅(qū)動下的戰(zhàn)爭機器轟響了八月的炮火。
從“一戰(zhàn)”廢墟中幸存下來的人渴望不再有如此慘烈的殺戮。盡管和平主義的愿望十分真切,卻依然擋不住20多年后另一場浩劫的發(fā)生。
追究“一戰(zhàn)”爆發(fā)的原因,有說是帝國主義的爭奪,有說是均勢的破產(chǎn),還有說是“修昔底德”式的宿命,而戰(zhàn)爭的后果更有著深遠的意義和影響。對歐洲,大戰(zhàn)的結(jié)束不僅醞釀出“二十年危機”進而走向新的大戰(zhàn),更拉開了以歐洲為中心的全球體系的衰退,西翼的英法等老牌帝國元氣大傷,東側(cè)新的洲際大國蘇聯(lián)漸漸興起,隱現(xiàn)的裂痕昭示了未來的傷口。
對美國來說,“一戰(zhàn)”讓國際主義與孤立主義的角力成為對外政策中日漸凸顯的矛盾,并開始逐漸賦予美國自認為天命所歸的全球領(lǐng)導責任。對弱國,這是一場混雜了怯懦的勝利者、弱小的無助者復雜心態(tài)的國家記憶。當時,如中國這般在國際上處于權(quán)力等級底層的國家,即便戰(zhàn)后僥幸領(lǐng)到一張勝利盛宴邀請函,也不過是從上一個列強的盤中餐變?yōu)樾铝袕姷谋P中餐而已,這也促成了近現(xiàn)代中國一個強烈的認識,即弱國無外交,時至今日依然是影響中國行為的重要觀念之一。
紀念是為了不忘卻痛苦的起源。世界大戰(zhàn)清晰地警告世人,大國既可以是國際安全最重要的穩(wěn)定軸,也可以是最危險的破壞者。尤其當強國站在軍事金字塔的上端,膨脹的決策層、被煽動的民意、軍事冒險主義的盛行和自以為是的戰(zhàn)爭正義,都會成為國際安全的重大威脅。那場大戰(zhàn)后,國際社會曾試圖建立一種既尊重權(quán)力現(xiàn)實、也維護和平理想的諸邊制度。盡管先天不足的國際聯(lián)盟很快就墮向失敗,但也開創(chuàng)了建立全球性國際安全組織的先河,為“二戰(zhàn)”后建立聯(lián)合國提供了重要借鑒。
即便如此,現(xiàn)實主義的魔咒似乎從沒有解除過,新興大國與現(xiàn)有霸權(quán)之間的競爭似乎仍在延續(xù),只是換了劇場和演員。在紀念“一戰(zhàn)”結(jié)束100周年同時,也有人抱著舊思維尋找下一場大戰(zhàn)的原罪之國,并把中俄這樣的新興大國視為新的威脅來源。在新加坡舉行的“彭博創(chuàng)新經(jīng)濟論壇”上,基辛格在把美中關(guān)系類比為“一戰(zhàn)”前的英德關(guān)系,進而提出兩國可能發(fā)生沖突的警告,質(zhì)問“沖突將把我們帶向何方”。
歷史畢竟不會簡單復制。中國不是帝國抑或“修正主義”國家,相反,而是以聯(lián)合國為中心的國際安全機制的倡導者、受益者和遵守者。今天的中國更關(guān)注如何實現(xiàn)和諧治理的愿景。中國想為世界提供的,是在同一片天空下共享繁榮的機遇。中國還一直努力推動構(gòu)建新型大國關(guān)系,開創(chuàng)某種既競爭又共處且能互惠的關(guān)系模式。
近來美國國內(nèi)對華論調(diào)的集體轉(zhuǎn)向雖然預示了未來兩國關(guān)系必將面對更嚴峻的挑戰(zhàn),不過,大國間競爭依然存在可預見性和可控性,塑造新時期的戰(zhàn)略穩(wěn)定也并非遙不可及。
從歷史經(jīng)驗看,穩(wěn)定的關(guān)鍵在于擁有相互敬畏的戰(zhàn)略力量、避免軍事沖突的共識,以及合作共贏的利益空間。當然,塑造這樣的關(guān)系,過程必然是動態(tài)的,也存在被不可控變量改變進程的風險。正因為如此,更加需要大國間能正確地界定核心利益,做到相互尊重、避免沖突。
還顧望來路,所思在遠道。緬懷逝者的傷痛是不區(qū)分種族和意識形態(tài)的,渴求和平的愿望真正是具有普遍意義的。反思“一戰(zhàn)”教訓,最終目標不是要彰顯勝利者的榮耀,而是要讓世人更清醒地記住,戰(zhàn)爭從來不是游戲,而是國之大事,事關(guān)生死存亡。輕易信奉炮艦主義的國家,往往難逃被反噬的命運。
(摘自《世界知識》2018年第23期。作者為國防科技大學國際關(guān)系學院戰(zhàn)略與安全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