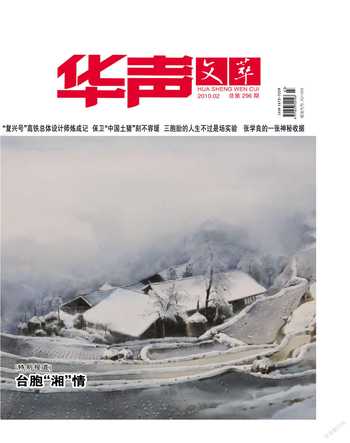立 心
2019-09-10 07:22:44米麗宏
華聲文萃 2019年2期
關鍵詞:杭州
米麗宏
最近閱讀時,遇到兩個有趣的人。一是北宋的詩僧道潛,一是明朝旅行家徐霞客。
道潛在一次聚會中,遇見杭州刺史蘇軾。道潛席上賦詩,蘇軾甚愛之。二人遂結為忘形之交。東坡遭“烏臺詩案”被貶黃州,他不遠千里赴黃州。后來東坡再起,到杭州,道潛自然又赴杭州。東坡又遭貶至海南島,道潛二話不說,又要轉海南相訪。東坡作書勸止道潛才作罷。一番坎坷后,東坡被召回,中途至常州而逝,道潛作悼詩數首。這位本是棄絕七情六欲的化外之人,拂去虛妄,直抵性情本質。
徐霞客32年游歷了21個省。不避風霜雨雪,不懼豺狼虎豹,三次遇盜,數次絕糧,幾次險些喪命……朋友問他:“你游歷天下,有何意義?”
徐霞客說:“我喜歡。”
他是真喜歡。《徐霞客游記》開篇寫寧海天臺山,“云散日朗,人意山光,俱有喜態”。情感與山光合而為一,自在自得。那個年代,男人立身講的是功名利祿,徐霞客卻別開一條僻徑,走獨屬自己的人生。
我細細揣摩二人生平,陷入的是現代人思考的窠臼:他們這一生,都做了些什么?有什么價值?譬如,道潛追隨友人,游山玩水,膩在一起,虛度光陰;徐霞客呢,雖有一部游記傳世,可在他生前并不為人所知。支撐他們一生游蕩的,肯定不是現世功利。
立心,賦予人生意義。穿越時間,率性純真,成為自己,令人長久回味。
我想起一位國學家的論斷:什么是最可怕的文化?就是只講效率功利、不計其他的工具文化。什么樣的民族沒有未來?就是只講效率、只講利害、只講功利、以成敗論英雄的民族。
(摘自《羊城晚報》)
猜你喜歡
科學大眾(2023年17期)2023-10-26 07:38:38
幼兒畫刊(2022年11期)2022-11-16 07:22:36
玻璃纖維(2022年1期)2022-03-11 05:36:12
中國交通信息化(2021年4期)2021-07-21 09:23:34
杭州(2020年6期)2020-05-03 14:00:51
中國音樂教育(2017年2期)2017-05-20 10:20:28
傳媒評論(2017年12期)2017-03-01 07:04:58
汽車與安全(2016年5期)2016-12-01 05:21:55
中國衛生(2016年8期)2016-11-12 13:27:12
看天下(2016年24期)2016-09-10 20:4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