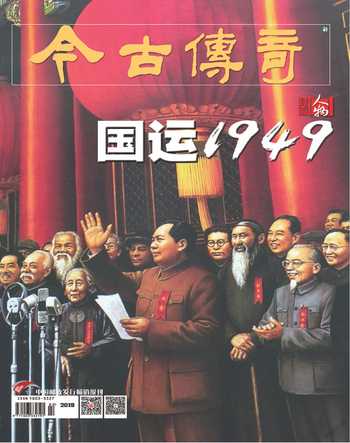曾春華憶父母:為革命舍棄三個兒子
“革命者所要承載的人生苦難是常人難以想象的”
“我對不起你們,讓你們吃了很多苦,
但是當時我也沒辦法,每天都要行軍打仗,
環境很苦,沒辦法帶養你們啊,因此,我要請你們原諒。”
蔡協民(1901-1934),湖南華容縣人,參加過南昌起義、湘南起義,曾參與創建發展閩西革命根據地的斗爭。1930年被派到福建廈門做地下工作,歷任福建省委軍委書記兼福州市委書記、福建臨時省委書記等職。1928年4月與妻子曾志(1911-1998,湖南宜章縣人。曾任中顧委委員、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結婚。在井岡山時期,兩人被稱為“軍中梁祝”。下文是蔡協民與曾志的三子曾春華對父母的回憶片斷。
我被送到武漢母親的身邊
1949年8月17日一大早,還在熟睡的我被伊奶(福州當地對母親的稱謂)推醒,伊奶對我說:“春生,趕快起床上街去看熱鬧,聽說是你父親的軍隊又開回來了。”伊奶是我的養母,我的生身父母都是共產黨員,既然伊奶說是我父親的軍隊開回來了,難道真是共產黨領導的解放軍打到福州來了?于是我起床來到大街上,果然看到大街上站滿了穿著土黃色軍服的解放軍戰士。
一天晚上,我正在夜校上課,伊奶到夜校來找我。回家一看,家里坐著兩名解放軍。這兩名解放軍是奉方毅(1916-1997,福建廈門人。建國后,歷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委常委、省委第二書記,上海市副市長,中央財政部副部長,對外經濟聯絡部部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院長、黨組書記,國家科委主任、黨組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國務委員等職)首長的指示,專門來找我的,要把我送到武漢我生母那里去。
第二天上午,我便見到了方毅叔叔,他當時是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方叔叔發現我身體發育不良,而且還是一個殘疾人時,只說了一句:“孩子,你怎么會變成這個樣子呢?”
為了不把這種心痛的情緒帶給我的生母,方叔叔決定把我留下來先療養一段時間,于是,我在福建省政府招待所住了差不多一個月。在這段時間里,我每天吃得好,睡得好,還有部隊的軍醫定期來給我做身體檢查并進行調理。
1950年3月初,我啟程前往武漢。經過幾天的舟車勞頓,一天傍晚,我順利到達漢口碼頭。
上岸后,一位吳姓船長手持介紹信首先帶我到中南軍政委員會貿易部。我們找到了曾傳六部長家,他家正在吃晚飯,曾部長對吳船長說:“我沒有兒子留在福州,你們要找的可能是對門重工業部曾志副部長吧?”于是,吳船長又帶我到了中南軍政委員會重工業部,經詢問落實后,吳船長把我交給了這里還沒下班的工作人員,然后對我說:“恭喜你找到媽媽了,我走了。”
工作人員安排我坐在辦公室的沙發上。不一會兒母親開會回來了,未見其人,先聞其聲:“我兒子到了嗎?在哪兒?”
母親的硬底皮鞋踩在刷著紅漆的木地板上咯噔咯噔地響,她穿著一件咖啡色的列寧裝一路小跑進屋。她走到我的身邊,然后蹲下問我叫什么名字,幾歲了。我機械性地回答她,心想:“我是你生的,難道你不知道,還要來問我?”然后,母親對身邊的人說:“這是我在福州生的兒子,是托方毅同志找到的。”
一塊“副部長室”的牌子掛在門上,這便是母親工作的地方,也是我的新家。
這一夜,我完全無法入睡,我想了很多很多。我想到了孤苦伶仃的伊奶,不知她現在一個人生活怎樣;我想到了我苦難的童年,那一年,我得了淋巴結核,身上到處腐爛發臭,已奄奄一息,是好心人聯系了一家美國人開的教會醫院為我做了免費手術,切掉了三根肋骨,一條腿也短了三寸,才總算把命保住了;我還想到了父母當初為什么要如此狠心地將我拋棄,以致讓我落下終身殘疾……想著想著,我不禁淚流滿面,繼而號啕大哭。母親聽到我的哭聲之后,來到我的床前問我為什么如此傷心,我默不作答。她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干脆搬了一把椅子坐到我的床前開始跟我聊起家常。
毛澤東曾高度評價父親在井岡山會師中的作用
“孩子,1934年初,我黨的路線斗爭異常尖銳,我和你的父親蔡協民在政治上屢遭打擊,在那個政治生命高于一切的年代里,為了表示對組織的忠誠,懷有身孕的我不得不離開你的父親,由廈門前往福州,到那里接受組織的考驗,參與那里的地下黨中心市委的工作。
“后來,毛主席知道了你父親在福建的處境后非常關切,于是以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的名義調你父親回中央蘇區工作,然則不幸的是,在回蘇區的途中,你父親被叛徒出賣,不幸被捕入獄。
“而我到福州之后,因形勢的需要,與市委書記陶鑄假扮夫妻開展工作,就在那年春末,我生下了你。當時的斗爭非常復雜,隨時都會有犧牲的可能,險惡的環境根本不允許我帶著一個孩子工作。況且那時候我又還背負著‘留黨察看’的政治包袱,工作上不敢有絲毫的懈怠,因此,在你出生只有十多天之后,我便不得不像對待你前面兩位哥哥一樣忍痛把你送人了。不久,又傳來了你的父親在福建漳州英勇就義的噩耗,這讓我悲痛萬分。革命者所要承載的人生苦難是常人難以想象的啊!”
母親的話,我似懂非懂,但我已經開始相信母親當時的內心一定很苦,當年她撇下我,一定是情非得已。這時,我更多的心思是想了解我的父親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人物,于是我開口問了母親。
母親說:“你的父親蔡協民烈士是湖南華容人,他早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大革命時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農民運動領袖。大革命失敗后,他參加了南昌起義,并協助朱德同志一道帶部隊來到我的家鄉湖南宜章發動了湘南暴動,他是暴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我就是在這個時期與他認識并結為夫妻的。其實說來,你的父親在老家已有妻室兒女,只是我們當時在國民黨的報紙上看到了一則消息,說蔡協民的家室已被政府全部處決了,而我的第一任丈夫(夏明震)也于不久前為革命流血犧牲了,因此,我和你父親都成了不幸的人,相似的家庭遭遇和共同的革命志向最終使我倆走到了一起,直到兩三年后,我們才知道那則國民黨報紙上的消息純屬造謠,你父親的家室雖然被反動派多次追殺,但每每都有人暗中保護,得以幸免。
“湘南暴動終歸還是失敗了,接下來,我們面臨的現實是敵人南北夾擊,我們該往哪里撤的問題。在一次討論會上,大家各自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和想法,甚至還有人提出把部隊帶到川貴去打游擊。然而,在你父親看來,這都是一些不切實際的想法,他耐心細致地從天時、地利、人和幾個方面向大家展開論述,不失時機地提出了讓部隊向東轉移,從而實現與在井岡山已建立了根據地的毛主席的部隊會師。他力排眾議,為朱德最終能作出‘進軍井岡山’的英明抉擇排除了一切阻力。后來,兩軍勝利會師,毛主席對你父親在兩軍會師的過程中所起的促成作用曾給予過高度的評價。
“你父親在湖南一師求學時毛主席是他的學長,后來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時,他們又是師生關系,因此,兩人感情很深。我第一次見到毛主席是在我和你父親上井岡山的途中,當時,毛主席聽說我們的部隊快到了,于是提前下山來接我們。毛主席見到我倆后格外高興,他們師生倆似乎有說不完的話,我在一旁聆聽,在我看來,他倆不像師生,倒像一對摯友,那次見面給我留下了終身難忘的印象。
“井岡山會師以后,朱、毛兩支部隊合二為一成立紅四軍,你父親一直擔任紅四軍軍委委員、前委委員和32團黨代表。在此期間,我生下了你的大哥,然而,令人傷心的是,他只在我身邊生活了不到一個月,我便把他送人了,因為,當時井岡山戰事緊張,我必須跟隨大部隊到更遠的地方去打游擊。我把你大哥托付給了你父親一個部下的妻子,他們夫妻倆就是井岡山當地人。從此以后,我再也沒有回過井岡山,幾十年來戰亂不斷,到如今,也不知你大哥是生是死。
“離開井岡山后,我們的處境極其艱難,國民黨調集湖南、江西兩省的優勢兵力對我軍進行前阻后追,我軍形勢異常嚴峻。此時,你父親已調任紅四軍第三縱隊黨代表兼軍政治部主任。要知道,這個第三縱隊可是紅四軍的主力部隊,是毛主席的重中之重,在此危急存亡之秋,你父親的這一職務改變,足見毛主席對他的倚重。后來部隊在朱軍長、毛主席的正確指揮下,全軍將士勠力同心,我們打了幾場勝仗,部隊終于走出了困境。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此時紅四軍內部卻出現了矛盾,由于毛主席正確的軍事主張得不到充分的肯定,加之又身患重病,他只好離開紅四軍到福建龍巖養病,并指導地方工作,我和你父親堅持要求與毛主席共進退,于是,我們也隨毛主席一起離開了紅四軍,到了福建從事地方工作。
“我們到福建地方后,你父親主要的任務便是協助閩西特委書記鄧子恢的工作。在此期間,我們和毛主席一同住在閩西大山深處一個叫蘇家坡的小山村,在那里我們與毛主席朝夕相處,一起度過了一段難忘的時光。后來,毛主席重返紅四軍的領導崗位,而我們卻被調到廈門,到設在那里的福建省委工作,從此開始了更為艱難的白區斗爭。
“我們在福建省委期間,你父親先后擔任福建省委秘書長、省軍委書記。1931年6月,省委機關遭敵人破壞,許多戰友被捕犧牲,我和你父親幸免于難。為了把黨的損失降到最低點,你父親勇于承擔,與我還有另外一位同志一起組建了臨時福建省委,我們在極端危險的環境中開展工作,使這里的黨的事業得以繼續。
“后來,中共中央決定在福建不再設立省委,而是成立廈門、福州兩個中心市委,你父親任福州中心市委書記,于是,我們由廈門轉戰福州。我們到福州工作后不久,你的第二個哥哥(小名“鐵牛”)出生了,你父親非常高興,工作之余抱抱孩子,享受著短暫的天倫之樂。然而,好景不長,你父親很快便被中央派來的巡視員圈定為‘有社會民主黨嫌疑’‘立場傾斜’的人物而被撤職,改任廈門中心市委巡視員,自此,你父親開始命運多舛。
“我們一家三口再次回到廈門時,廈門黨組織的處境極其艱難,由于經費奇缺,許多戰友都在挨餓。為了讓黨的組織不至于因此而受損,你父親同我商量后,我們便忍痛將你那出生才65天的二哥賣給了一位小兒科醫生,將所得的100塊大洋全部交給組織,以解組織燃眉之急,可不久,你二哥便身染重病夭折了。”說到這里,母親已泣不成聲。
母親理了理情緒,稍作停頓后繼續說:“新的打擊又接踵而至,你父親在負責小山城根據地的保衛戰時,由于軍事上的失利,再一次被‘極左’的市委領導召回廈門接受組織審查。他們將失敗的責任強加于他一身,給他戴上了‘機會主義’‘富農路線’的帽子,并在黨內開展所謂‘反蔡協民路線’,將其開除黨籍。我也因此被‘留黨察看’3個月。這一連串的迫害,最終導致我與你父親勞燕分飛,各奔東西,更慘的是你父親因失去了組織的保護而遭叛徒出賣,落入敵手……”
說到這里,母親停頓了好一會兒,才繼續說道:“在湖南華容老家,你的爺爺奶奶都還健在,你父親與結發妻子生的一對兒女如今都已長大成人,他們都是你的哥哥姐姐。你的哥哥叫蔡至平,他去年來武漢找我,我把他留了下來,讓他在武漢上大學,改天我讓他來與你見面。有機會你還要回華容老家去,去看望你的爺爺奶奶,也去看望你哥哥姐姐的母親。”
母親接著說:“孩子,既然你的父親已經為革命犧牲了,以后你就隨我姓曾,你是湖南華容人,又出生在春天,以后你的名字就叫曾春華好不好?”自此,“曾春華”這個名字便伴隨著我一生。
一個星期天,母親帶回來一個小姑娘向我介紹說:“春華,這是你妹妹陶斯亮。”這個時候我才知道我還有一個妹妹,盡管她是母親和繼父陶鑄(20世紀30年代初,曾志與陶鑄在福建廈門以夫妻名義開展革命工作,后結為夫妻,1941年生下女兒陶斯亮)所生,但我與她同屬一個母親,心里還是樂滋滋的。
因是干部子弟,我被工農速成學校退學
記得1950年“五一”節過后,母親決定讓我去一所學校念書。這是一所高級干部子弟學校,叫“華中育才子弟學校”,學校有學生200多人,設在漢口西郊,母親親自寫了一封信派警衛員送我過去。學校的副校長是鄧子恢伯伯的夫人陳蘭,她知道我是曾志和蔡協民的兒子后,便非常愉快地收下了我,把我編到二年級。
記得一個周末的下午,陳蘭媽媽突然來找我,讓我去一下她的辦公室。我跟著她到了副校長室,只見辦公室里坐著一位器宇軒昂的年輕人,他見我進來了,也連忙起身。陳蘭媽媽給我介紹說:“曾春華同學,這是你的哥哥蔡至平,你們哥兒倆都是蔡協民烈士的兒子。”哥哥緊緊地拉住我的手,十分動容,我也激動萬分。
回到家里,母親已經下班,正好家里還有幾個客人,見我和哥哥回來,于是她把我和哥哥拉到一起,然后對客人們說:“你們都來看看,這兄弟倆到底長得像不像?都是蔡協民的兒子。”
我們學校大多數是十一二歲的小弟弟小妹妹,十七歲以上的學生全校只有幾個,我是其中一個,還有一個叫鄧蘇生,是鄧子恢伯伯的兒子,因為我倆都是殘疾人,所以我記得很清楚。因為年紀偏大,在這里我小學沒有念完就主動退學了。
離開育才學校后不久,母親又送我去武漢一所工農速成中學讀書,這所學校是中南工業部主管的,是培養工農干部的一所文化學校,畢業后,可以直接送中國人民大學深造。我在這里學習得非常愉快,憧憬著美好的未來。但好景不長,校方提出說,我是干部子弟,不是工農兵干部,不符合條件,沒辦法,我只好又退學了。
這個時候,我哥哥已經結束了武漢中原大學的學習,被分配到了湖南湘潭電機廠工作,他知道我的情況后立即寫信給母親,告訴她湘潭譚家山有一所技工學校是培養社會青年和一般的工農兵干部的,比較適合我來學習。于是,母親給湖南省委書記黃克誠寫信,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不久,我便收到了該校的錄取通知書。
這所學校有1000多名學生,有兩個工農兵干部文化補習班。我報名學會計,但母親來信卻讓我先補習文化,以后再學專業,于是,我在這里學完了初中的全部課程。接著,學校又保送我到山西太原市中等專業學校深造,我所學的專業后來劃歸到了太原化工學校,這是一所屬軍工部主管的火炸藥專業學校。我在這里參加了共青團,1955年畢業后進工廠當了一名技術員,進而被評為工程師,一直兢兢業業工作至退休。
1995年母親生病了,聽斯亮妹妹說是淋巴癌。于是,我和妻子立即趕到了北京,準備好好照顧她老人家一段時間。我們每天去醫院陪伴母親,這是我們母子相處最長的一段時間。能陪母親走完她人生的最后一程,我感到很欣慰。
最難忘的是1998年4月4日,那是母親的最后一個生日。那天,我們兄妹4人都到齊了(曾志在井岡山生的大兒子蔡石紅,又名石來發,1953年才找到,一直住在井岡山,2002年去世),這種大團圓還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母親那天有點兒激動,她對我和大哥說:“我對不起你們,讓你們吃了很多苦,春華腿有殘疾,把石來發留在了大山里,但是當時我也沒辦法,那會兒我也還是個小孩子,每天都要行軍打仗,環境很苦,沒辦法帶養你們啊,因此,我要請你們原諒。”這是我第一次聽母親講這樣的話,這話可能在她心里揣了很久很久,如今,她試圖用關愛去補償我們。接著母親對我說:“春華,我給你辦了殘疾證,可你一直不用,說明你很有志氣,很有自尊心,這一點我很佩服你,不愧是我的兒子,也不愧是英雄的后代……”
1998年6月21日夜,母親永遠離開了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