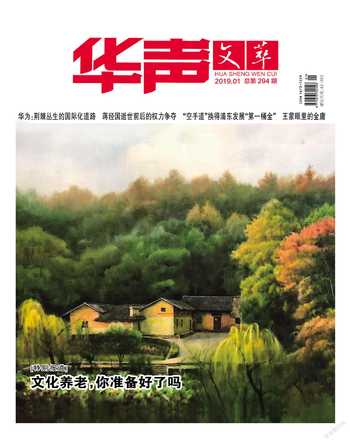“天才”的底牌
18世紀(jì)70年代中期的萊茵河畔,德國(guó)小城市波恩一棟破舊的居民樓里,夜半時(shí)分經(jīng)常會(huì)傳出一個(gè)男人的呵斥聲,有時(shí)還伴隨著一記響亮的耳光,接著便是一個(gè)小男孩的哀號(hào)和抽泣聲。
這個(gè)叫貝多芬的孩子只有4歲。他的父親,一個(gè)嗜酒如命的男高音歌手,一心想把他培養(yǎng)成像莫扎特那樣的音樂(lè)神童,因而不惜采取高壓手段。“苦練”確實(shí)帶來(lái)了實(shí)效,貝多芬8歲時(shí)就已開(kāi)始在音樂(lè)會(huì)上表演并嘗試作曲。為了使他看上去更像一個(gè)神童,父親謊報(bào)了他的年齡,說(shuō)他只有6歲。首次登臺(tái)的貝多芬獲得巨大的成功,被人們譽(yù)為第二個(gè)莫扎特,他的父親所期望的巡回演出和資助也陸續(xù)實(shí)現(xiàn)。
許多年過(guò)后,當(dāng)人們談?wù)摶蛸澴u(yù)貝多芬時(shí),正如我們所感受到的,更多的是這位杰出人物的天才展現(xiàn)和神奇光環(huán),而絕少提到他早年所經(jīng)歷過(guò)的魔鬼式強(qiáng)化訓(xùn)練。研究者發(fā)現(xiàn),貝多芬的記事本留下了他痛苦、煩惱的創(chuàng)作印記,他有時(shí)會(huì)在一篇樂(lè)章定稿前草擬六七份不同的底稿。有一次他曾對(duì)朋友說(shuō)道:“我會(huì)修改很多次,推倒重來(lái),如是再三,直到我滿意為止。只有這樣,我才能對(duì)自己的作品有個(gè)全面深入的把握。”
莫扎特本人的例子也頗能說(shuō)明問(wèn)題。他的音樂(lè)家父親發(fā)現(xiàn)他還在蹣跚學(xué)步時(shí)就對(duì)音樂(lè)特別敏感,于是就著意培養(yǎng)、指導(dǎo)和訓(xùn)練他。3歲時(shí),他已能登臺(tái)即興演奏;六七歲時(shí),他已開(kāi)始巡回演出,從貴族贊助人那里獲得不菲的收入,被看作家庭的驕傲和經(jīng)濟(jì)來(lái)源。他的早期才華在當(dāng)時(shí)極為罕見(jiàn)。
不過(guò),美國(guó)作家戴維·申克對(duì)此卻有這樣一番評(píng)述:在針對(duì)兒童的強(qiáng)化訓(xùn)練中,此類(lèi)成績(jī)的取得得益于父母和教師的付出,亦即:早期教育的結(jié)果、高水平的指導(dǎo)、不停地練習(xí)、家庭的培養(yǎng)。一般來(lái)說(shuō),神童還不是一般意義的創(chuàng)新者,他們只是非常嫻熟于某項(xiàng)技能。
莫扎特本人又是怎么看的呢?成年后在致父親的一封信中,他寫(xiě)道:“那些認(rèn)為我的音樂(lè)作品是輕松得來(lái)的人,犯了一個(gè)巨大的錯(cuò)誤。沒(méi)有人在作曲時(shí)能像我一樣花費(fèi)如此多的時(shí)間。”莫扎特的傳記作者也曾指出,當(dāng)莫扎特接受一項(xiàng)任務(wù)時(shí),會(huì)長(zhǎng)時(shí)間地進(jìn)行思考,在鋼琴上試奏各種組合哼給自己聽(tīng),冥思苦想如何使音樂(lè)思想(或主題)適合于對(duì)位法則,如何使其適應(yīng)特別內(nèi)容、表演者和樂(lè)器的特性。
近幾十年來(lái),瑞典心理學(xué)家安德斯·艾瑞克森等學(xué)者的許多獨(dú)立研究都得出一個(gè)同樣的結(jié)論:任何領(lǐng)域內(nèi)的高超技能,都是在超過(guò)10年且不少于10000個(gè)小時(shí)的訓(xùn)練之下獲得的(也就是平均每天3小時(shí)),亦有人稱(chēng)之為“一萬(wàn)小時(shí)定律”。而美國(guó)心理學(xué)家戴維·費(fèi)爾德曼則在對(duì)許多“神童”進(jìn)行研究后提出一個(gè)論斷:神童并非與我們普通人完全不同,他們只是在某些“特殊”領(lǐng)域的發(fā)展速度大大快于常人。“天才”的底牌還是“勤奮”。
(摘自《科技日?qǐng)?bà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