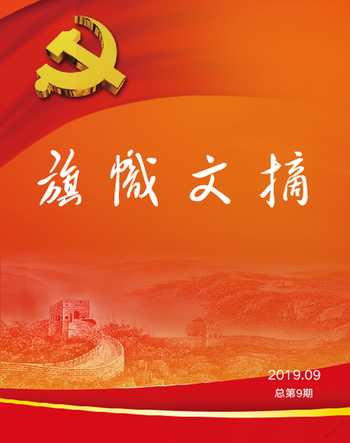秘境之秘
祝勇
紫禁城四大花園中,我獨喜寧壽宮花園,我們通常叫它:乾隆花園。
乾隆花園在寧壽宮區的西北角,是紫禁城中隱得最深的一座花園。在這座不太大(紫禁城中倒數第二大)的花園中,曲廊山石、崖谷洞壑連起二十多座樓堂館閣,交接錯落,“誤迷岔道皆勝景”。
假如說御花園屬于皇帝和全體宮妃,慈寧宮花園屬于那些“退休”的太后、太妃們,那么乾隆花園則完全屬于乾隆個人,透露出乾隆內心最幽秘的情感,他想什么、要什么,都通過這高墻內的花園得以體現。就像我小時候寫日記,日記的保密工作做得越好,里面的文字越真實;需要上交給老師的日記,則都打腫臉充胖子,清一色的豪言壯語。
那一重一重的院落,一幕一幕的風景,都只是乾隆花園的序幕而已,就像那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章回小說。但它真正的高潮部分,不在黃金分割處的符望閣,而在它的結尾處、花園的最后一座建筑——倦勤齋。
我寫過《故宮的隱秘角落》,其實乾隆花園不只是故宮的隱秘角落,更是乾隆個人心中的隱秘角落,而乾隆花園最北端的倦勤齋,則是秘境中的秘境。只有走進倦勤齋——這乾隆花園的最幽秘處,我們才可能真正認識乾隆,尤其是那個藏在“千古一帝”的光輝形象背后的乾隆。
倦勤齋是一座面闊九間的居室,縱然屋頂上覆綠琉璃瓦,黃琉璃瓦剪邊,廊前檐下繪蘇式彩畫,顯示出某些不同,但乍眼望去,還是平凡而低調,就像晚年的乾隆,假若不著龍袍站在我們面前,也不過是一個普通的老頭兒罷了。難怪有那么多的游客路過倦勤齋時,只是向它投去茫漠的目光,甚至連看都沒看上一眼,就被導游像趕羊一樣趕過去,匆匆奔赴下一個景點了。
但乾隆終歸是乾隆,他再低調,骨子里也是尊貴的,就像這倦勤齋,體量不大,貌不驚人,走進去,卻別有洞天——在這“九間”房屋的內部,分為“東五間”和“西四間”兩個區域。“東五間”又分隔成十余個小的空間,分別設有寶座床、書房、寢室、佛堂等,上下兩層,拼合成一個凹字形的仙樓。用以區分空間的紫檀木落地罩,使用了竹絲嵌玉技術(使用和田玉兩千多塊)、雙面繡技術(把針腳收納于圖案中,于正反面都看不見針腳)、竹黃貼雕技術(紫檀木壁板上鑲嵌有竹黃百鹿和百鳥圖案),這低調的奢華,專為乾隆私人訂制。
倦勤齋退居在花園的最末端,藏而不露,但它的低調,掩不住它的富貴榮華。它靜靜地打量著花園空間的層層遞進,就像乾隆本人,臨風站立在自己的晚年時光里,安詳地回望自己的一生。
有人問我,倦勤齋為什么要分隔成那么多小的空間?我想這純屬乾隆的個人偏好,同時也很符合人性,因為只有小的空間才會給人安全感,像一個溫暖的子宮,或者,一床緊裹著的錦被,給人以溫暖、安全。有一次,我陪法國朋友走過太和殿,他問,皇帝在這里睡覺嗎?我一笑,反問:你會在這里睡覺嗎?
太和殿太大,四周太空曠,反襯出人的渺小。在白天,太和殿上的皇帝并不渺小,眾臣的朝拜,襯托出帝王的偉大,但白天不懂夜的黑,在夜晚,再偉大的人晚上都要睡覺,而睡覺是一個人的事——最多是兩個人的事,不需要閑雜人等參與,因此,當白晝退場、眾人退去,巨大的空間只剩下一個或兩個人,這空間就不再凸顯出一個人的強大,而只能暴露他的弱小。夜色如潮水,漫過紫禁城,這宮殿里的人就成了荒島上的魯濱孫,孤立無援。
皇帝坐擁天下,但天下太大,幾乎大到了無邊無際、鞭長莫及。太和殿也大,宮殿的尺度與天下成正比。但作為一個人,需要的恰恰是小的空間,因為只有小的空間,給了他一個邊界,讓世界圍攏在自己的身邊,伸手可及,可親可近,讓自己成為這個世界真正的統治者。
大空間永遠是冰冷的,那種冷是心理上的冷,與取暖設備無關;只有小空間才是溫暖的。大空間是朝廷的、莊嚴的、儀式性的,小空間卻是個人的、私密的、文人化的——我認識的許多作家的書齋名,都在強調它的小,比如一位作家的書齋名叫“七步齋”,說房間只有七步,當然借用了曹植的《七步詩》之名,有以曹植自喻的意思;劉紹棠老師的書齋叫“蟈籠齋”,極言其小,還不乏京味兒;但這都不算小,從齋名上來看,最小的書齋(居室)應該是元代畫家倪瓚的“容膝齋”,書齋僅能容下膝蓋,算是夸張到極致了,從這齋名,我們可以想象倪瓚獨自盤坐,“容膝”其中的樣子。
乾隆少年時生活過的重華宮,明朝時就有,面闊五間,進深三間,原本并不算小,卻用雕工繁復的紫檀雕花槅扇,將宮室分隔成許多個小的空間;他登基后住的養心殿,同樣被分隔成許多小空間,最小的暖閣,就是“三希堂”了。下朝的乾隆,盤腿坐在炕上,在炕桌上展讀來自遙遠晉代的書法珍寶,看倦了,就靠在錦枕上,沉沉地睡去。在他心里,三希堂永遠是暖的,三希堂的原名也印證了這一點,它曾被叫作:“溫室”。有意思的是,三希堂東墻有一道小門,通向勤政親賢殿,勤政親賢殿后室中有一小室,叫“無倦齋”。但乾隆的生命太長——他是中國歷代皇帝中壽命最長的一個,所以,他終會“倦”的,因此,后來又有了“倦勤齋”,在乾隆花園的結尾處等著他,“耆期致倦勤,頤養謝喧塵”。
倦勤齋雖小,但它的容積并不小——就像乾隆花園一樣,“集殊香異色”于一身。在倦勤齋的每一個小隔間,密密麻麻地裝滿了乾隆喜愛的各種事物,像我這樣的觀者,很容易患上密集恐懼癥。太和殿上的寶座屏風、甪端香爐固然燦爛莊嚴,但它們是簡單疊加式的,猶如一個人說話,通過反反復復的形容詞來加強語氣,但倦勤齋的神奇是通過變化來實現的,猶如魔術師的寶盒,可以變出鴿子、拐杖、綢帶,變出種種意想之外的事物。是的,在那些宏大的意義之外,假若沒了意外的驚喜,生命會變得多么單調和無聊。
倦勤齋里的各個獨立小空間,有許多走廊相連,曲折狹窄的走廊,拉長了我們在倦勤齋內行走的距離,加大了倦勤齋的空間感,而且使倦勤齋產生了“移步換景”的效果。這樣起承轉合的空間敘事,讓腳步有了探秘感,讓目光不知疲倦。
還是回到倦勤齋吧,它的室內空間,不是一覽無余,而是曲曲折折,輾輾轉轉,像一支昆曲,或者“春秋筆法”的文章,幽幽咽咽,彎彎繞繞,就是不把話說明白。自明代以來,伴隨著城市的發展、土地的緊張,用于造園的“地皮”日益稀缺,園林開始“內向型發展”,不再追求場面宏大,不再簡單粗暴地橫向鋪展,而是注重內部“挖潛”,追求“巧于因借,精在體宜”,使空間關系走向立體,起承轉合、層疊錯落,成為“曲徑交叉的花園”。這樣的流行風,也吹進了皇家花園。在乾隆心中,倦勤齋的室內,像大腦溝回般的回環曲折,不是因為他拿不到地皮,而是體現了這座建筑獨具匠心的魅力。
小小的倦勤齋,真的像一個藏寶盒,藏著乾隆兒童般的想象力、少年般的頑皮和青春時代的激情。乾隆不喜歡一覽無余地開敞空間,而是喜歡曲徑通幽又豁然開朗的起伏感,喜歡賦予空間某種未知感,讓人永遠無法預想,在一個空間背后的下一個空間,究竟會是一個怎樣的佳境。
在我看來,倦勤齋里最神奇的部分,不是明殿中被裝修成上下兩層的仙樓,不是那一個個用紫檀花罩隔開的小隔間,也不是裝修中使用的手工絕活(在今天,那些絕活已成非物質文化遺產),比如竹黃貼雕、竹絲嵌玉、雙面繡等,而是這耄耋的主人好似一個少年,有著無窮無盡的好奇心。
去年(2018年)秋天拍攝《上新了·故宮》,演員蔡少芬一進倦勤齋就張大了吃驚的嘴巴,她說,她想不到乾隆的世界是這樣的,與她的想象,也與攝影棚里的世界大相徑庭。房子里有那么多的小機巧,不像是一個見太多大世面的乾隆大帝,倒是與她女兒的心性不謀而合。我由此可以明白,眾多兒女中,乾隆為什么那么喜歡精靈古怪的十公主。
乾隆花園的終結處,在倦勤齋;而倦勤齋的終結處,在西四間的墻壁。西壁上的通景畫,畫的是樹石藍天,讓小戲院的空間,延伸向(畫中的)高遠天際。但那只是虛擬的遠方,很少有人知道,在這終結之地,還藏著一個秘密,就是這層通景畫的背后,還暗藏著一扇小門。穿過小門,真的可以“破壁”而入,進入一條暗道,出來時,竟然站在竹香館里,又重新回到了乾隆花園。
乾隆在跟我們開玩笑嗎?一個空間的玩笑,或者,關于生命的玩笑。風聲中,我儼然聽到乾隆的聲音。他說:在這個世界上,沒有終結。所謂的終結,其實不過是一個新的開始,就像這生命與朝代,都無不通向生死興衰的無盡輪回。
竹香館以竹為名,透露出乾隆對竹的偏好。其實竹子這一意象,在乾隆花園四進院落的第一進就已經出場,像一個預置的伏筆,等待著下文的呼應。禊賞亭在第一進院落西側,緊依紅墻,亭前抱廈中有流杯渠,用來追慕晉人王羲之蘭亭雅集的風神,乾隆坐在那里,就可以呼朋喚友,約他心目中的“謝安”“孫綽”來喝兩杯,而一千多年前的那場風雅事,就是在“茂林修竹”的環境下完成的(詳見拙著《故宮的古物之美:書法風神》)。那些古老的竹,藏在王羲之的《蘭亭集序》里,也通過禊賞亭內外裝修所用的斑斑竹紋,得以重溫。
乾隆一生作詩四萬三千六百三十首,一人單挑《全唐詩》(《全唐詩》共收兩千二百余位唐代詩人的作品四萬八千九百余首),但沒有一首詩被人記住,可見他不是一個杰出的詩人。但假如你對乾隆這么說,那可要得罪乾隆。在乾隆心里,自己詩文書畫,無所不能,就像李白在《古詩十九首》里所寫:“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秋。”沒有這份自信,他也沒膽在歷代名畫上寫字,用他柔弱無骨的“面條字”,在前代大師面前瞎嘚瑟。
乾隆對竹子的一往情深,是根植于他的血脈的。他的父親雍正,就對竹有一種近乎瘋狂的迷戀。他的御制詩中,有不少寫到竹子,比如這首《竹子院》:“深院溪流轉,回廊竹徑通。珊珊鳴碎玉,裊裊弄清風……”我曾講到過故宮發現的《十二美人圖》(詳見拙著《故宮的古物之美:繪畫風雅2》)——十二幅真人大小的美人絹畫,畫上的美人面目個個不同,沒有人知道她們的身份,不知道畫者是誰,亦不知道為何而畫,我通過畫上的“圓明主人”印章和屏風上的文字,知道這些畫的背后,站著雍正(當時還只能叫胤禛),又發現這十二幅美人圖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上面都有竹,或者說,竹子是十二幅面目不同的美人畫里唯一的共同點。顯然,在康熙晚年,當皇位爭奪戰在眾皇子間如火如荼展開之際,沒有取勝希望的雍正只好隱居在圓明園,暫時收斂起自己的兇狠冷酷,以竹和美人(幾近于屈原所說的香草美人)自喻,表明自己不慕皇位、潔身自好、高風亮節,為自己猛灌心靈雞湯,順便也可以用這樣的“姿勢”來蒙蔽競爭對手。
因此,乾隆對竹的偏好,是文化熏陶的結果,也是遺傳的結果。但,令人意外的是,在乾隆花園里能看到的竹子并不多。竹香館前假山堆石,蒼松翠柏,卻不見幽竹。所以蔡少芬會一臉蒙圈地問:竹香館,哪有竹啊?我們都知道,竹子是南方植物,在寒冷的北方幾乎無法生長,竹香館外,也就沒有“竹香”可聞。追慕古人、以竹自喻的乾隆也只能面臨這樣的尷尬。但皇帝一向不喜歡尷尬,更何況乾隆不是一般的皇帝。沒有什么能夠改變他對竹子的一往情深。因此,乾隆花園里是必然有竹子的,在這一點上,乾隆早就胸有成竹。只不過那竹子不一定都放在表面上,猶如真正的有錢人,不一定都時時刻刻想著露出自己的大金牙——有涵養的人都是笑不露齒的。那些竹子被隱藏在某處,我們什么時候發現它,什么時候才算真正走進乾隆的內心世界。
庭院深深,我們始終沒有發現竹子。乾隆在和我們玩藏貓貓嗎?他把竹子都藏到哪里了呢?翻閱《清高宗御制詩》,發現清高宗乾隆曾站在他的花園里,“面對此情此景”,曾不止一次地“吟詩一首”。這花園里,也曾像王羲之的蘭亭一樣,竹影婆娑。院落第三進有一座三友軒,取松、竹、梅“歲寒三友”之意,軒外自當是種上松、竹、梅這三種植物的。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乾隆寫下《三友軒》一詩,在注文里證明了這一點:
軒中掛曹知白十八公圖、元人君子林圖、宋元梅花合卷,因以命名,而窗外亦植松、竹、梅三種。1
乾隆的詩稿,不止一次印證了花園里竹子的存在。他在《延趣樓自警》里寫:“豎橫峰嶺勢,颯沓松竹影”2;在《玉粹軒》里寫:“竹翠常搖籟,墻高因避風”3。竹香館前,他也是寫過詩的:“竹本宜園亭,非所云宮禁。不可無此意,數竿植嘉蔭。”4嘉慶也有《竹香館》詩,是這樣寫的:“歲晚花無韻,冬深竹有香”5。顯然,這些地方,有竹,也有香。
只是這些曾經茂盛的竹子,在帝國北方的寒風中搖蕩飄零,早已蹤跡難尋。故宮博物院近年對乾隆花園展開保護性調查,證明竹香館的土壤呈堿性,植物不易種植成活,因此目前這一區域并無竹叢存在。6
但在乾隆的地盤里,竹子斷然不會消失。但我們找不到它,這是乾隆花園留下的一個懸念。乾隆花園就像一部懸疑電影,不到終局,絕不揭曉謎底。
這謎底,就在倦勤齋。
一進倦勤齋,人們的目光立刻就會被“東五間”紫檀花罩上大面積的竹黃貼雕吸引。竹黃,是指毛竹的內皮,因其為黃色,稱為“竹黃”。竹黃貼雕,是將竹黃制成的竹片貼在器物表面,再在上面雕刻紋樣。倦勤齋“東五間”仙樓樓下的群墻上,貼雕的是“百鹿圖”,山石松林間,有百鹿穿梭,悠游嬉戲,各具姿態;樓上的群墻,貼雕的是“百鳥圖”,在樹叢花間,有群鳥棲落,在空林中發出悠揚婉轉的鳴唱。竹黃厚的地方,鹿和鳥毛發的肌理質感都無比細膩逼真,在窗子透射進的光線里,發出潤澤的光。
庭院里消失的竹子,在“東五間”明殿里,以竹黃的形式存在著。但這并非謎底的全部,因為像乾隆花園這樣的“大片”,謎底不是一次性揭曉的,而是“層層剝筍式”的。
在“東五間”明殿西側的落地罩背后,藏著通往西四間的走廊,拐到一個“鏡廳”戛然而止。“鏡廳”是一個小隔間,共有兩面落地鏡,一面是真實的落地鏡,另一面落地鏡同時又是一道暗門。推開這扇門,拐過一道窄窄的走廊,進入一個更大的空間,所有人都會眼前一亮,大吃一驚——
在這幽秘的倦勤齋內,竟然暗藏著一個巨大的方形劇場(戲院)。戲院的正前方(正西),是一座攢尖頂的方形小戲臺,皇帝的寶座在東面,背東面西,與戲臺對望。戲臺的北墻和西墻,有通天落地的“通景畫”,以西方透視法描繪山樹樓閣,利用視像的錯覺延伸了室內的空間,使畫上的風景與室內的布置融為一體。頭頂上則畫滿了紫藤花架,透射出寶藍色的天光,人在這小小的室內,有如置身開放的庭院里。
在戲臺的兩側,有金黃燦爛的竹籬藥欄鋪展彌漫。那些竹籬,一部分是真實的,一部分延伸到畫里,實物的竹與畫中的竹無縫銜接。
這里不是有竹嗎?
說乾隆花園沒竹的,只因他沒有走到乾隆花園最隱秘的角落。
這也正是我一直關注“隱秘角落”的原因。
但新的疑問又應運而生——竹子在北方(室外)無法存活,這些竹,雖在室內,以竹材做裝修,也很容易變形、開裂,如何能做皇家宮室的裝飾材料呢?
乾隆不管這套,他知道,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竹子圍出的世界,正是他熱愛的江南,是優雅的、屬于文人的世界,沒有竹子相伴,他就無法與王羲之、蘇東坡成為真正的朋友,他就永遠只是一個沒有文化的暴發戶。
皇帝很任性,后果很嚴重。后果是什么,我們就不必多介紹了。重壓之下,大臣們腦筋急轉彎,終于想出一個辦法,那就是以楠木仿制“竹籬”,雕出竹節的凸凹,再用彩繪手法表現竹子的色彩與斑紋。
兩百多年后,在我們拍攝的《上新了·故宮》綜藝節目中,一個名叫鄧倫的年輕演員把臉貼在竹籬上看,半天,看不出真假。
乾隆有家嗎?曾經,重華宮是他的家。那時他還是太子,住在紫禁城西路的重華宮,和太子妃富察氏一起,度過自己的青春歲月。小小的重華宮,載滿了他對未來的夢想,還有他與富察氏相敬如賓的日子。二十五歲,相當于今天許多年輕人研究生剛剛畢業,還沒有工作的年紀,他就找到了自己的職業,這職業是:皇帝。
皇帝以國為家,從未像明朝皇帝那樣怠惰早朝,經筵進講也延續了五十五年,從未中斷。他效法祖父康熙,六度南巡,數度北巡,既體驗到帝國巨大的空間感,也體驗到民生之多艱。但他的家太大了,以至于他那么容易就丟失了自己,以至于忘記了自己的家在哪里,哪里才是自己停靠的港灣。
三宮六院是他的家嗎?是,也不是。說是,因為東西六宮,住的都是他的嬪妃——他的法定妻子。但那些貌美的妃子,從未像富察氏那樣打動過他的心。蘇東坡說過一句話:我心安處即是家。三宮六院,是他的心安處嗎?富察氏死后,他的心,或許再也沒有安過,也無處可安。
他把自己與富察氏共同生活過的重華宮,原原本本地封存起來,“原狀陳列”,不許別人改動半分,自己還時而返回這曾經的居所,一點一點,味覺精細地,反芻已逝去的日子。而后,他會躲進三希堂,沉浸在古人的書法世界里。或許,只有在養心殿西暖閣這個不到八平米的小隔間,亦或許,只有面對千年以前的知己,他才能真正地放松下來。
乾隆喜歡小的空間,從三希堂到倦勤齋,延續了他一貫的癖好。
重華宮是乾隆永遠回不去的家。最愛的人死了,但他還活著,而且活了那么久。當乾隆已老,當他已“倦勤”,他就要為自己設計一下“未來”。他要給自己一個家。
太和殿是屬于帝國、朝廷的,自己坐在太和殿上,面南背北,坐擁天下,但反過來也可以說,是天下、朝廷征用了他的身體,他不過是這巨大布景下的一個演員而已。當他褪去化妝、洗盡鉛華,重新變回他自己,他需要一個屬于自己的空間,一個讓自己心安的地方。
春天花開的日子,他會打開倦勤齋所有的窗子,讓春風和花香充滿整個室內,而自己,會躺在榻上,舒適地睡去。
如米沃什詩中所寫:
這世上,
沒有一樣東西我想占有;
沒有一個人值得我羨慕;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
我都已經忘記。
2018年9月13日至2019年5月13日
責任編輯 石一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