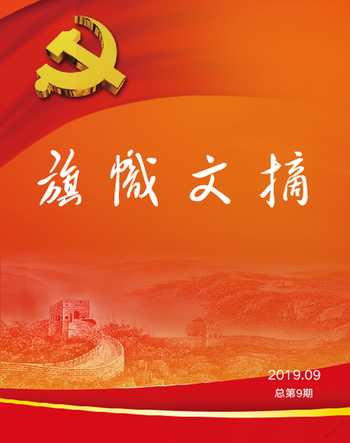撲朔迷離八角城
馬恒健
北出甘肅省甘南州夏河縣城,駕車行駛在茫茫的甘加大草原上,撲鼻而來的是清新無比的空氣,撲面而來的是一望無涯的碧野。在碧草間的小路上穿梭1個多小時后,一列灰白色山脈橫亙在前。山岡斷崖百丈、巖石裸露,形成了橫亙10余公里的摩天屏障,令人感覺山窮水盡。這是夏河第一高峰達里加山,主峰海拔4636米。它唯一位于中段的如天斧劈開的豁口,便是唐蕃古道由內地通往青海、西藏的咽喉要道。
佇立達里加山前的緩坡向南望去,一座中空十字形的城池在群山拱衛下躺在草原盡頭。百聞不如一見,八角古城的城廓是那樣完整,仿佛是穿越到古戰場;它的八個城角是那樣的奇異,感覺像來自天外;它的周邊環境是那樣的蒼茫寂寥,有著“一片孤城萬仞山”的意象。
離八角古城越來越近,空氣里漸漸有了牧民煨桑時焚燒的柏樹枝的味道,夯土城墻下、城壕里,懶散地游蕩著吃飽了青草的牛羊。八角城現在是夏河縣甘加鄉八角城行政村駐地。城外剛完工的偌大游客停車場空空蕩蕩,負責收費的一位中年男性村民守候在此,等待著慕名而來的游人。
2000年以來,八角城才逐漸為人所知。最早踏訪八角城的游客多是外國人,當時八角城象征性地收每人5元門票,并由村民給他們提供簡單講解。2006年5月,國務院公布八角城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后,國內外游客才逐漸增加。停車場由村民輪流值守,并兼收每位游客20元門票。相比國內其他知名度極高的歷史景點,八角城的游人寥寥。
八角城位于夏河縣城北35公里大夏河支流央曲河上游,海拔2100米。歷史學家初步推測,八角城即漢代的白石城、王莽時期的頃礫城、唐代的雕窩城。它曾經是絲綢之路河南道上的重要軍事設施,此后唐蕃古道在這一帶與絲綢之路河南故道重合,因此又成為唐代的軍事重鎮。八角城城內出土有大量唐、宋時期的建筑構件和文物,甚至新莽時期的貨幣。
如此重要的城池,關于在此發生的重大戰役以及重要歷史人物的足跡,史冊竟然沒有記載。不過,根據當年西北邊民吟唱的“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帶刀。至今窺牧馬,不敢過臨洮”的民謠,倒是可以確認這里是唐代的邊關要塞。而負責這一線邊防重任的,正是大名鼎鼎的唐代名將哥舒翰。當年的哥舒翰防區,東起今甘肅的臨洮縣、臨夏縣,西至今青海的貴德縣、湟源縣,而位于夏河縣境內的八角城剛好居中。唐貞觀初期,吐蕃王朝的松贊干布與唐帝國聯姻,唐蕃關系處于友好時期。松贊干布死后,吐蕃為了掠奪人口和牲畜,不斷寇邊。臨洮作為戰略要地,經常受到吐蕃騷擾,唐蕃之間的武裝沖突加劇,戰爭不斷。
唐天寶六年(公元747年),哥舒翰任隴右節度使(治所在今青海海東市),于公元749年攻克吐蕃在青海的戰略要地石堡城,取得黃河九曲之地。自此,唐軍在河西、隴右的戰場上占據了絕對優勢。到唐天寶十三年(公元754年),唐朝與吐蕃的分界線已經推進到青海湖以西,“是時中國盛強,自安遠門西盡唐境凡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在如今的臨洮縣城內,仍遺存著碑身高達4.25米的哥舒翰紀功碑,碑文的字體秀麗古樸,相傳為唐明皇李隆基御筆。因此,位于哥舒翰防區正中的八角城,戎馬倥傯的他一定多次巡視,甚至有可能在此地設過他的前敵指揮部。而當年的戰爭場景,只能從唐代詩人王昌齡的《從軍行》:“大漠風塵日色昏,紅旗半卷出轅門,前軍夜戰洮河北,已報生擒吐谷渾”中去領略了,洮河是黃河的支流,就從八角城附近流過。
另一個涉足八角城的著名歷史人物,有可能是眾人皆知的文成公主。西出長安城,甘肅的臨洮縣、臨夏縣至青海的貴德縣、湟源縣是唐蕃古道的主線,路程最短且路況相對較好。更重要的是,這條路線在進入吐蕃境內之前的地區,都在唐軍防區以內,可確保安全。因此,當地文史工作者推測,八角城應是文成公主入藏的必經之地。七十多年后沿文成公主原路入藏的金城公主,也應當路過此處。
八角城西,有一個拱形門洞,那是村民及游人進出的主要通道,也被認為是西城門。但它實際上并非八角城真正的西城門,而是近年為了進出便捷在城墻上掏鑿出來的“新城門”。
站在高處,能夠發現八角城整個城垣保存較為完好,城墻是由一層土一層砂石夯筑而成。根據文物管理部門測量的數據,城墻外圍周長為2540米,占地面積16.9萬平方米。現存城墻殘高6~13米,城墻底寬11~13米,上寬5~18米。八角城一反中國古代城池正方形或不規則圓形的形制構筑,十字形城廓的八個拐角突出,八角城也因此得名。在它的每個拐角上,建有突出于城墻的墩臺,墩臺與墩臺之間的距離,都在弓弩射程之內。因此,站在墩臺上的守軍,可以無死角地用弓弩射殺攀墻攻城的敵軍。
進得八角城,先沿著城里的主道直奔南城門。在已經坍塌無存的南城門外的城墻根,立著國家級文物保護碑。南城門有一座約8000平方米的長方形甕城,甕城的城墻高低不一的殘存著,城廓十分明顯。據推算,那應當是大都城的甕城,才有如此大的規模。關于甕城的功能大致有兩種,一是在于防備混雜的敵特,將眾多外來人安排在甕城內的旅舍居住;另一種觀點說,這是當年操練兵馬、誓師出征之地。
但一眼便可看出河床的輪廓。時值五月,一叢叢粉紅色的狼毒花在河坎上盛開,仿佛在憑吊一去不復還的輝煌。據考證,當年的護城河寬10米左右,深2米以上,河水從城北分兩支繞城向南流,后匯入央曲河。中國古代西北的城池,由于地理條件所限,很少有護城河,如嘉峪關、統萬城等。八角城城址的選擇如此慎重和嚴密,無疑彰顯著它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星移斗轉,世事滄桑,隨著時代的變遷,與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相距遙遠的八角城,不可避免地退出了歷史舞臺。自元代起,華夏大一統的局面形成,八角城也不再是邊陲之地,昔日的軍事要塞成了絲綢之路上的重要驛站。
清代初年,八角城遺憾地與登上歷史舞臺的機遇擦肩而過。乾隆初年,清政府準備在這里大規模開墾屯田,然而,大學士鄂爾泰于公元1743年(乾隆七年) 上奏折稱:“泉水既不足以灌田,而地土又難于開墾,兼之地寒霜早,不能必其成熟,徒勞民力……”于是,在此地開墾土地的計劃被放棄,到清末,八角城基本完全廢棄。
雖然八角城有百姓入駐的時間不過百年,但當地村民對八角城感情頗深。城墻上寬約4、5米的馬道,是年幼的他們玩耍打鬧的好去處。如今佇立護城邊,仰望因風吹雨蝕加速殘頹的城墻,只能看見孤獨的牧羊人蹲守在殘缺的城堞上發呆的身影。
八角城內并沒有想象中城池的街道,除了一條近些年修建的穿城而過的通鄉公路稍寬一點,其余均為東拐西彎的小巷。村民的住房除了少數一樓一底,其余均為平房,房前屋后的空地栽種蔬菜瓜果及花木,如果不是四周高墻環護,令人感覺像是置身于鄉村院落。
城內的中心位置,有一座小小的寺廟,這是村民的寄托。有一所寬敞整潔的小學,兒童們在這里學習藏、漢兩種語言。由于全村僅500多人,走遍全城,幾乎只看到一家賣日用百貨和零食飲料香煙的小賣店。據當地一位年近九旬的村民講,清代末年,八角城內尚無居民居住,只有少量的清兵留守。民國時期,當地漢、藏居民才開始入住八角城。現在這里的居民不到100戶,藏、漢雜居,以放牧為主,兼種一些莊稼。由于八角城地處甘加鄉盆地,草灘廣闊、谷溝寬敞、溪流縱橫,自古以來是天然的優質牧場,因此村民放養的甘加羊、牦牛、蕨麻豬等,是畜牧產品的優質種類。由于長年的駐軍屯田,如今站在城墻上放眼四望,八角城南方北郊廣闊的坡地上,仍可看到被撂荒多年、成型成片的梯田。
城內村民曾收藏有少量的屬于宋、明、清時期的金屬貨幣和少數民族銅飾牌,遺憾的是基本上被文物販子收購,只有紋瓦、勾頭滴水、吻獸及門枕石等不便移動的建筑構件,還在村民家中可見。從這個角度講,村民或多或少是八角城悠久歷史的受益者。但是,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對八角城的來歷知之甚少。而史學界對八角城身世的研究,則是眾說紛紜,各持己見。由于此城是歷代中央政權與吐谷渾、吐蕃、西夏、唃廝啰王朝劇烈爭奪的軍事重鎮,又是古絲綢之路交通要道,因此它到底由誰所建、建于何時,主要有以下幾種說法:一是如前述,由大漢王朝初建,名為白石城,此后在唃廝啰統治河湟時期所建成現有規模;二是初建于南北朝時期,宋代進行了完整的修筑,元代又進行了較大規模的修繕;三是吐蕃王朝所建的軍事重鎮,作為漢藏交界處的橋頭堡。
作為曾千年不衰的邊關重鎮,其身世的撲朔迷離,和它歸屬地的頻頻變換直接相關。這種變換不僅直接反映出了王朝的更替,更反映出中華民族大融合進程的復雜性和必然性。也正因為如此,八角城才有著獨特的魅力。
在距八角城僅幾公里路程的達里加山豁口處,也就是唐蕃古道由內地通往青海、西藏的咽喉要道旁,有一座頗有規模的白石崖寺。它是安多藏區比較著名的佛教修行地,建于十七世紀。在摩天接云如萬里屏風的達里加山脈映襯下,它顯得格外肅穆和神秘。如今白石崖寺的寺主是女活佛貢日倉,人稱“卡卓瑪”,意為“空行母”,是甘南眾多活佛中的唯一女性。與白石崖寺毗鄰的白石崖溶洞,以洞內石壁上有天然形成的藏文元音和輔音字而聞名,從而成為安多藏區佛教名勝。該洞深十公里,深邃崎嶇,通往青海境內。
八角城有過“風吹草低見牛羊”的祥和繁榮,更歷經“沙場烽火侵胡月”的腥風血雨。曾經滄海的它,如今隱于茫茫的甘加大草原深處,如同寵辱不驚的智者,安然、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