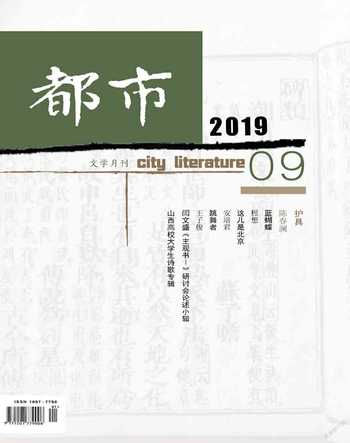“我是我批判的主觀的煙火”
2019-09-10 07:22:44劉階耳
都市
2019年9期
劉階耳
閆文盛《主觀書Ⅰ》“中卷”自《寡人只祭國與酒》以下計14篇,均從“寡人”云云,文白夾雜,話語辨識度極高;其中《關于夢境的記憶和修辭》一篇,與“上卷”中的《格調的修辭》相對讀,饒有意味,很有必要。面對閆文盛“主觀書”這樣的巨型文本,任何異于尋常的話語癥候其實都宜嚴肅對待,否則其話語“系譜學”屬性很難確鑿掌控了。
譬如說,閆文盛對尼采、佩索阿、卡夫卡推崇備至,自不待言;至于與之相頡頏的中華民族的優秀的代表人物,見之《主觀書Ⅰ》似乎只有一處,從反諷的語氣而講了一句:“李白、曹雪芹、魯迅也都是過時的”(《恥于談論的》),可若就李白、曹雪芹、魯迅風華標勁的文化抱負、與物神游的話語藻思、絕詣超邁的文體極境等方面來看,閆文盛所曾受益的著實一言難盡;像迄今只能在影視、戲劇中得聞其詳的“寡人”云云這樣的“敬辭”,竟然令閆文盛化腐朽為神奇,其實不失其一則旁證。為是我不禁聯想到閆文盛為“晦澀”正名的一篇文章;且不說閆文盛出生的歲月(1978)適值“今天”詩派橫空出世,因詩意的“晦澀”、“朦朧”而舉國關注的“新詩潮”艱難崛起,至少對我們還是記憶猶新;再往前追溯,倡導“美文”的周作人有鑒于“文學革命”的成就容易滑向玲瓏剔透、“玻璃球般”的明凈,繼而對“含蓄”或“朦朧”之類的“晦澀”情有獨鐘,甚至為當時因“晦澀”而遭詬詈的廢名不遺余力地辯誣、揄揚,且以“文章之美”來概括其弟子不俗的文體建樹,佳話一時,思之神往。熟悉這類文壇掌故,對理解閆文盛之所以也為“晦澀”正名可提供更深層次的“視野融合”的際遇或機會;……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甘肅教育(2020年8期)2020-06-11 06:10:02
文苑(2020年4期)2020-05-30 12:35:30
制造技術與機床(2019年10期)2019-10-26 02:48:08
電子制作(2018年18期)2018-11-14 01:48:06
小學生作文(中高年級適用)(2018年3期)2018-04-18 01:24:47
瘋狂英語·新策略(2017年8期)2017-05-31 08:13:46
小學教學參考(2015年20期)2016-01-15 08:44:38
人間(2015年20期)2016-01-04 12:47:10
少兒科學周刊·少年版(2015年4期)2015-07-07 21:11:17
語文知識(2014年10期)2014-02-28 22: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