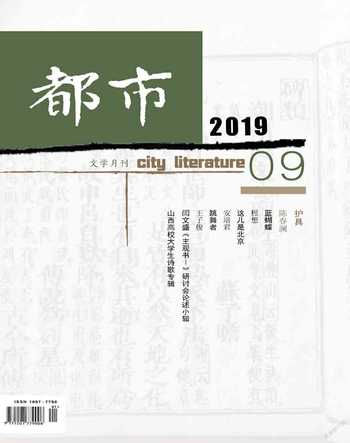無法抵達(dá)中的“震驚與發(fā)現(xiàn)”
金春平
首先,《主觀書》重新確立了“寫作”之于個人的思想、情感、生命和靈魂的藝術(shù)自發(fā)性意義。與費(fèi)爾南多·佩索阿《惶然錄》的不期而遇,以及靈魂氣象的某種相通性,促成了作者持續(xù)多年執(zhí)著于《主觀書》系列的抒寫與雕刻,這種寫作行為本身,構(gòu)成了一種極具個人實(shí)驗色彩的語言、文本與創(chuàng)造行為的一種外化表征,在作者寫作的預(yù)謀、過程、整理與反顧中,其思想經(jīng)驗、情感經(jīng)驗和生命體驗,巧妙轉(zhuǎn)化為一位拒絕外在“物”的牽制的靈魂漫游者和精神孤獨(dú)者,所進(jìn)行的語言狂歡、詞匯恣肆和言說迷幻,這一方面造就了《主觀書》作為一種獨(dú)特文體的開放,包括箴言體的哲思性、現(xiàn)代詩的詩意性、敘述體的虛構(gòu)性、語錄體的自白性、典籍體的訓(xùn)導(dǎo)性等等,由此賦予《主觀書》作為一種創(chuàng)造性文體的無限,兼容了諸類文體的思想或美學(xué)形態(tài);另一方面,與其將《主觀書》視為是一種刻意為之的文體實(shí)驗,不如說作者尋找到了一種契合自身的存在底色、生命姿態(tài)和藝術(shù)氣質(zhì)表達(dá)的自由文體,這種自由的寫作包含了對自我以及對自我與外在世界的多重“解放”,解放了必須恪守某種文類的言說姿態(tài)和言說范式的硬性規(guī)約,解放了寫作對外在事物或時間空間的理性邏輯的依附,解放了對自我乃至一切客體事相的強(qiáng)制確認(rèn),感覺主義、未來主義乃至超驗主義成為作者支配文字編碼的內(nèi)在邏輯,這是對主體寫作的一種高度自信,也是對主觀寫作的一種深度經(jīng)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