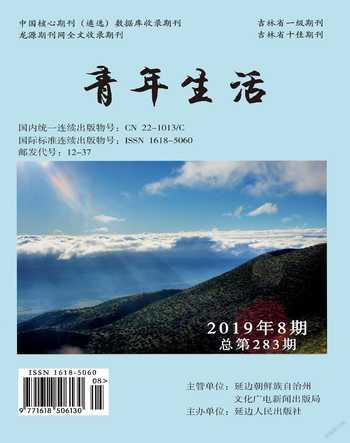淺析《安德洛瑪刻》中的情感表現
劉俏含 劉舒曼
摘要:拉辛在《安德洛瑪刻》中,再現了古希臘悲劇人物形象,在17世紀歐洲這一大背景下,用其特有的清麗筆法,描繪了四位主角之間的愛恨糾葛,本文從理性與非理性的抗衡,情感的循序漸進以及情感的歸宿出發,淺析《安德洛瑪刻》中的情感表現,通過它們我們可以窺見主人公豐富而細膩的內心,感受作者深刻的洞察力與強烈的表現力。
關鍵詞:情感轉變;理性;宿命
拉辛在《安德洛瑪刻》中,再現了古希臘悲劇人物形象,在時代大背景下,用其特有的清麗筆法,描繪了四位主角之間的愛恨糾葛,而在這其中的情感轉向,是真實且復雜的,通過它們我們可以窺見主人公豐富的內心世界和細膩的心理活動,感受作者深刻的洞察力與強烈的表現力。
一、理性與非理性的抗衡
當將四位主角置于同一時間進行對比,安德洛瑪刻的特別便得以體現,她被塑造為一個不畏強暴而堅貞不屈的苦難形象,雖亡國為奴,遭受侮辱與迫害,但為保護同亡夫的唯一兒子,在敵國忍辱負重,不惜以嫁給敵國國王卑呂思為代價,但準備在婚禮上自殺以保貞潔,從而既拯救了獨子又不會委身于卑呂思。她周旋于各種威脅和恐嚇之間,對卑呂思熾熱的情感和唾手可得的地位保持者冷靜的距離,這是一種極其理性的表現,不盲目、不沖動,有著明確的價值標準。 “拉辛刻意把這個行為提高到理性原則的高度來看, 并讓女主人公堅守到底, 對事關國家利益、丈夫榮譽和個人貞節的理性不作絲毫的讓步,這也是作者堅守理性的態度。”[1]
而與安德洛瑪刻不同的,劇中的其他三人則被感情所蒙蔽,隨心所欲,為個人欲望所支配,雖情感真摯濃烈,但他們的種種行為在拉辛的劇中顯然不夠理性。卑呂斯身為國王,卻棄國家不顧,一直追隨著安德洛瑪刻,為救她兒子不惜與希臘為敵,“大家怨恨他忘記了自己的血統和諾言,在他的宮廷里居然養育著希臘的敵人。”甚至在最后將衛隊調走保護她同赫克托爾的兒子,而這些近乎癲狂的情感也毀了他,卑呂斯身死,他的國家也隨之拱手相讓。愛妙娜和奧萊斯特也是同樣,愛妙娜愛英雄卑呂斯,而奧萊斯特卻愛著愛妙娜,他們的愛是偏執而帶有毀滅性的,愛妙娜因愛生恨,一時沖動讓奧萊斯特去殺死卑呂斯,而奧萊斯特也被感情所左右,同希臘兵士一起殺死了卑呂斯,最后因愛妙娜的死而發瘋。他們的不理性最終釀成了悲劇,三人最終非死即瘋,走向了毀滅之路。
拉辛處于十七世紀中后期,而在這一時期作者塑造了有著美好品質的安德洛瑪刻,以此來對抗卑呂斯等人,作者借助這兩類人物的對立,來折射現實社會,來表明對自己所屬資產階級的支持和對貴族社會的隱晦批判,“法國封建社會發展到極盛時期,宮廷的燦爛輝煌越發促使人欲橫流,這就是拉辛悲劇所折射的社會現象。”[2]
二、情感的循序變動
劇中每個人物的感情都有一個變化的過程,這些過程都并不突兀,有著作者對心理描寫真實性的思考和體悟。安德洛瑪刻在劇中是堅定不屈的,但她從劇作的開頭到結尾的情感態度依然有著微妙的變化,在卑呂斯被刺死之后,“安德洛瑪刻自己,本來對卑呂斯是那樣反對,現在倒為他盡一個忠實寡婦應盡的本分,下令叫人替他報仇。”在比拉德的陳述中,安德洛瑪刻此時作為“卑呂斯的寡婦”,與刺死丈夫之人為敵。而正是隨著卑呂斯的身死,擊碎了她對這位希臘英雄冷漠的心,而他也一定程度上取代了赫克托爾在安德洛瑪刻心中的位置。而這樣的情感轉變在前面也有展現端倪:她認為卑呂斯“性情暴烈,但他心地誠實。”在她決定自殺時,讓賽菲則告訴自己的兒子不要復仇。“對卑呂斯的好感是安德洛瑪刻的隱秘,是她決不會承認,不敢正視并竭力壓制的,她不斷深情地對丈夫亡靈起誓,時時把對丈夫的愛掛在口上,過于外露的感情往往是真情的表現。”[3]
而對于愛妙娜,則經歷了一個悲——喜——悲的過程,她對自己心目中英雄的愛是毋庸置疑的,從一開始得知卑呂斯同安德洛瑪刻親近時的怒氣沖沖,到卑呂斯答應娶她的雀躍高興,直至最后決裂的癲狂,唆使奧萊斯特殺死卑呂斯,她的全部感情都被卑呂斯所牽扯,而卑呂斯最后的道歉也使她拒絕收回命令,但當奧萊斯特聽從她的話殺死卑呂斯后,她責罵道:“你竟然如此瘋狂,斬斷了一個何等壯美的生命!”隨后也便自殺了。她其實仍愛著卑呂斯的,恨意不過是一瞬的情感,拉辛也將因愛癡狂的形象寫得真實而生動。而卑呂斯作為劇中不理性的代表,在劇中卻有著對戰爭的反思:“勝利同黑夜比我們更殘酷,它們刺激我們去屠殺,并使我們不分皂白地亂砍亂殺。”可見在拉辛筆下,他并不似古希臘戲劇中那樣暴虐無道。奧萊斯特的感情則是同愛妙娜綁在一起的,最后因愛妙娜的死發了瘋,他們的愛都是自私的,是一廂情愿而不顧全大局的,愛得痛快淋漓卻瘋狂,但那些都是真實的人性,是自然的情感轉向。
三、情感的宿命歸屬
奧萊斯特在一出場時便表示“誰知命運將要怎樣安排我的前途。”卑呂斯在奧萊斯特的質問下回答道:“命運——大家都遵從它的判斷的命運。”可見劇作籠罩著一層神秘的命運面紗,奧萊斯特來到愛比爾,見到了他一直愛著的愛妙娜,而也是正隨著他的到達,激化了劇作的矛盾,也堅定了他的決心,從而推動了故事的發展,最終愛妙娜指使奧萊斯特殺死卑呂斯。在這系列事件中,我們不得不感嘆造化弄人?愛而不得,卻又汲汲求之,似乎像是被詛咒般無力掙脫。而在追求愛情時,卑呂斯等人又是狂烈而無法自拔的,這也使他們走向毀滅。安德洛瑪刻在走投無路時去已故丈夫的墳前征求意見,而這里的魂靈也也起到了十分關鍵的作用,它同意了安德洛瑪刻的“純潔的妙計”,魂靈的出現仿佛是冥冥之中的安排,而它所發的指意也非人間的聲音,一切都在命運的安排下前進。“拉辛從命運觀念出發,導向悲觀主義。拉辛認為一旦激情侵入人物,他就完蛋了。他還認為沒有高尚的激情,迷住了人的愛情,事實上是一種災禍,它對受害者毫不容情,不讓他們有任何藏身之地,只讓他們走向死亡。”[4]拉辛從小經歷坎坷,自幼父母雙亡,而讓森派影響頗深,而在這個派系中有著濃厚的神學氣氛和悲劇色彩,歐里庇得斯劇作中的命運觀也影響了他的創作,他又身處于隱隱孕育著變革的十七世紀,對于一切的無力掌控感讓他對命運有著特殊的情感,而劇中人物的毀滅也代表了了他的思考和人生態度。
四、總結
在《安德洛瑪刻》中,作者并未對卑呂斯被殺這一場景做具體的描繪,而是將主要的筆墨放在人物的心理活動上,整部劇作有著澎湃的情感,真實地反映了人物的性格與變化,通過人物情感橫縱向的比較,我們可以發掘他們的不同個性與隱秘,被他們瘋狂而熾烈的愛所感染,被最后毀滅一切的悲劇所震撼。而我們從這些情感表達也可以窺見作者的內心及那個時代。在這部嚴格遵守了三一律,被布瓦洛稱為“標準的悲劇”的古典主義戲劇中,展現的是作者對人生和社會的思考與感悟。
參考文獻:
[1]袁素華.論古典主義的理性——兼比較高乃依與拉辛創作中的理性傾向[J] ,中山大學學報論叢,1998(03).
[2]鄭克魯.古典主義悲劇思想藝術的新高度——拉辛悲劇論[J],上海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08).
[3]李鴻泉.《安德洛瑪刻》藝術技巧探微,內蒙古大學報(社會哲學科學版),1991(01).
[4]鄭克魯.古典主義悲劇思想藝術的新高度——拉辛悲劇論[J],上海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