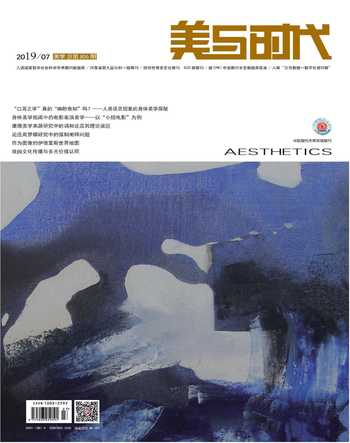作為圖像的伊德里斯世界地圖






摘 要:在地理學領域,地圖被認為是以數學和定量方式再現“客觀”地理的科學過程,但是這種觀點在當代遭受很大質疑。依據圖像理論分析西西里島伊德里斯1154年繪制的世界地圖,這張地圖是2018年湖南省博物館“在最遙遠的地方尋找故鄉:十三至十六世紀意大利與中國的跨文化交流”展覽的展品。學者認為地圖可以呈現有關知識生成、傳遞和演變的客觀歷程,地圖呈現的對邊界處境的認知,代表的并非地理界限,而是一種“文化建構”。
關鍵詞:圖像;伊德里斯;世界地圖;圖像理論
基金項目: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廳人文科學一般項目(SB170294)階段性研究成果。
伊德里斯世界地圖(復制品) 2018年1月26日和6月9日分別在湖南省博物館和國家博物館展出①,這件展品是目前保存下來的伊德里斯地圖中時間較早的,目前收藏在法國國家圖書館,寫本編號為MS.Arabe 2221(如圖1)。伊德里斯地圖顯示出中世紀阿拉伯地理學家在吸收希臘托勒密地理學知識的基礎上地圖圖像的創造。伴隨著蒙元帝國的文化交流,影響了元代之后的中國地圖圖像繪制觀念。
一、伊斯蘭世界的“圖像”語詞
在伊斯蘭的土地上,就像在中世紀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樣,不同視覺表現模式之間的界限并沒有嚴格的區分。因此,視覺表現的所有模式都有一個共同的語詞類。許多語詞被同時使用,有時相互并置,這些語詞中最常見的是源自阿拉伯語的(來自詞根“SWR”,表示形式、形狀)、rasm/tarsim(來自詞根“RSM”,表示繪圖)和naqsh/naqshah(來自詞根“NQSH”,表示繪畫)(如表1)。
表1.中世紀伊斯蘭語言中三個與圖像有關的語詞
序號 阿拉伯語 中文 英文含義
1 naqsh (pl.nuqush) 圖畫 to paint
2 形狀 to form,to shape
3 rasm/tarsim 繪圖 to draw,to sketch
naqsh來自波斯語,指中世紀阿拉伯寫本中的插圖,亦指肖像畫。例如菲爾多西的《王書》(亦稱《列王紀》)十四世紀伊爾汗時期至十七世紀薩法維王朝時期《王書》插圖本的圖像。本文討論的主要是ūrɑh,指形狀或圖像。中世紀伊斯蘭語言中沒有特定的“地圖”這一術語,但不能理解為伊斯蘭文明中認為地圖不重要。早期阿拉伯地理學家花拉子米借用托勒密的理念,使用 ūrɑt ɑl-ɑrd (圖像)這個通稱建立了一種世界地圖的類型。依據米切爾的圖像學理論,形象(Image)構成了形象譜系的頂層,本文研究的圖像可歸屬于形象家族樹的第一個分支——圖形的(Graphic)。
在中世紀伊斯蘭地理學發展中,一些語詞在建構伊斯蘭地理學的知識方面也起到關鍵作用。波斯語iklim,指氣候或者區域。在伊本曼澤的《伊斯蘭辭典》(Lisān ɑl-?Arɑb)中曾討論這個語詞。一般認為iklim來自希臘語的klimɑ,詞根Klm,指“傾斜”,iklim更確切地說是指地球從赤道到極點,引申為區域。Ibn Durayd提及iklim是七個氣候帶之一(ɑkālim),指地球的不同區域。氣候帶的思想源于古希臘托勒密的地理學傳統。與之拼寫相近,也被認為來源于希臘語κλιμα的阿拉伯術語iqlim (pI.ɑqɑlim),在阿拉伯語文本中具有與托勒密著作中相同的含義。波斯人認為世界分為七個區域,每個區域都有一個大帝國,這些地區,被稱為基什瓦爾(kishvars)。這種觀點被中世紀的伊斯蘭地理學家接受,他們改為阿基里姆(ɑqiilim),可能是因為他們相信后一個語詞是阿拉伯語。中世紀的伊斯蘭地理學家可能已經注意到希臘的κλιμα和波斯的kishvɑr都是七。巴勒希地理學派賦予這個語詞第三層含義:把它等同于他們劃分的世界地區[1]。
十七世紀法國學者赫爾勃婁(1625-1695)編著的《東方叢書》,是十九世紀之前歐洲關于東方的標準參考文獻。這本百科全書中有一項稱“伊斯蘭”,這是法語出版物中首次出現這個詞語,日本學者羽田正在專著中翻譯了這個詞條的主要內容:
穆斯林或穆罕默德教徒把自己擁有的地區(le pays)用阿拉伯語叫做Bilad al-Islām,……生于伊斯蘭歷385年(ca.995)的地理學家艾布德·阿魯阿爾迪(Ebd Aluardi)的時期,伊斯蘭范圍從馬瓦拉爾納赫爾地區的費爾干納城,或者說從位于阿姆河(阿拉伯語為Jay?un)對面的扎嗝臺河(le Zagathay)對岸開始,一直延伸到面向附近海洋的也門或幸福的阿拉伯海岸為止。[2]
羽田正指出十七世紀之前的歐洲,“伊斯蘭世界”沒有形成一個獨立的概念。那么,“地方性世界觀”這個在修辭上相矛盾的表述與伊德里斯的世界地圖體現的世界觀仍然是相對應的。
邁蒙尼德在《迷途指津》中使用希伯來文的t?elem(形象)一詞,來論證YHVH不與受造物任何相似,非形體、非物質、絕對獨一,沒有任何偶性屬性、沒有任何本質屬性的本質同一。與其相關的阿拉伯語是?anam:
形象這個術語用指自然形式,我是指這樣一個概念,一個事物可以借助于它而構成一個實體,成為它實在的樣子。……一方面指一個特定的形式,另一方面又指一個人造的形狀,還指一個在形態和外表上與這兩者相似的自然物體的形象。[3]
《迷途指津》中的t?elem作為一個概念,接近于希臘語的eidolon,因為它并不反映原初的意指或人,而僅表示自身的存在。與偶像禁令的思想有關,?almu(阿爾穆)無疑是希伯來《圣經》中第二誡的偶象禁令背后的原動力。阿卡德語的tam?ilu則描述整體事物的呈現或相似性。相似性作為圖像的一種理解方式,根源于神學信仰中關于“依上帝的形象和樣式”造人的文化傳統。圖像(image)一詞的希伯來語為“t?elem”,希臘語為“eikon”,拉丁語為“imago”,指抽象的、一般的、精神的樣式。通常在形象之后加上樣式,即指相似性(希伯來語demuth;希臘語homoioos;拉丁語simlitude),米切爾和法國學者雷吉斯·德布雷都在其著作中解為相似性,是靈魂的相似性問題。關于形象與相似性,柏拉圖在《泰阿泰德篇》中把記憶形象比作蠟板上的印象。亞里士多德在《論靈魂》中指出,“那么對于思想的靈魂而言,形象取代了直接的感知,而當它斷定或否定這些形象的好壞時,它避開或追逐它們。因此,靈魂在思想總是伴隨著精神形象”[4]。
這種相似性的理解被認為是向非圖像領域的延伸,是與圖畫再現、物質的形象、精神的圖像、語言圖像和感知相對立的。相似性是事物的一種普遍關聯,它可以在一切感性知覺的系統中起作用,并且可以和所有感性經驗相聯系。如果以福柯所述的十六世紀知識生成過程中起創建作用的相似性的適合——呈現出逐漸的鄰近形式的空間相聯系的相似性而言:伊德里斯世界地圖繪制則是這種相似性建構知識網絡的過程。相似性伴隨符號系統的出現被呈現和關注,不僅僅作為十二世紀知識生成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形式。
索緒爾認為語言是一個形式系統,語言表征中的施指(能指、語音形式)與所指(概念)之間是一種任意性原則結合在一起的,并沒有一個在先的,有著明確邊界的“現實世界”來與概念或者所指一一對應,是能指創造和構建了它的所指,而所指或概念使現實事物的邊界得以明晰。德國概念史學派的歷史學家科塞雷克在2006年出版的《概念史:政治社會用語的語義和語用研究》一書的導論部分指出,“(概念史)探尋由分析得出的,概念和語言之外事物的關系類型”[5]。關于“概念”的歷史性問題,科氏認為是特定時代、特定思想和事物發展之語境中生成的概念,進而關注概念在歷史上的顯著性,從而可以用來作為歷史變遷的表征。
文本對圖像的介入是無法被根除的。地圖作為圖像的理論假設:地圖是自然形象的符號化過程。米切爾則認為,“無論如何自然的形象都不是類似于人類語言中的語詞一樣的約定符號,而是一種視覺相似。”米切爾把語詞與圖像的關系看作是:
它是對一個問題的指稱,以及對一種不確定性的指稱。這種不確定性既是對視覺機制(視覺藝術、視覺傳媒、布展和觀展的行為)與語言機制(文學、語言、話語、聽、說、讀寫的行為)之間不規范、不固定的邊界的描述……
它包含了一系列關聯性和差異性的隱喻或象征的集合并存在于美學、符號學、直覺描述、認識交流以及媒介分析等領域。這是一種鮮明的復合形式,混合了文字和圖像的超文本。[6]
在形象譜系中看得見的、可以顯示的客觀的、公開空間里的圖形,例如地圖,都不是穩定、靜態或永恒的,“它們都不是專屬于視覺的,而是包含了多重感官的領會和解釋”。胡塞爾在現象學中也提出圖像顯現不是“普通的事物的顯現”,而是一種感知性想象。現象學所把握的圖像意識的本質結構有三種類型的客體:圖像事物、圖像客體、圖像主題。雖然我們具有一個感知立義(在胡塞爾現象學中,把它看作是一個“普通的感知”,它的相關項是圖像事物)。但通過感知立義而具有一個圖像形式的非感知對象。地圖可以界定為一種圖像客體的立義:“這個建立在感性感覺之上的立義不是一個單純的感知立義,它具有一種變化了的特征,即通過相似性來展示的特征,在圖像中的觀看的特征。”[7]由此,我們具有感性感覺和感知立義,但我們把這些感性感覺立義為某種展示性的東西。
郎西埃用圖像性的體制——圖像要素和功能之間的關系的體制,意指圖像是事物直接記錄在其身軀上的意指,是有待解讀的事物的可見語言。將語詞和圖像從可見物和可說物之間做區分[8]。
有學者認為,現代理論對圖像研究的不足之處是必須把圖像理解為一種語言。米切爾把語詞與圖像的關系看作是在再現、意指和系統的領域內反映我們在象征與世界、符號與其意義之間的關系。圖像是一種不易歸類的符號,偽裝成自然的直覺和在場。語詞則是人類意志的人為的任意的生產。通過時間、意識、歷史和象征性的非自然因素的異化介入,擾亂了自然的正常秩序。米切爾將語詞與圖像的相互聯系看作是“異質圖畫”和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圖像”有相似之處,語詞與圖像作為相互獨立的符號系統在符號學中得到了解釋。本文嘗試提出這樣的問題:地圖作為語詞與圖像相互關聯的圖像媒介,區別于其它媒介的特質是什么?
二、伊德里斯的世界地圖
如果說托勒密的地理學是給予人居世界的一種形式或集合秩序,伊本·胡爾達茲比赫著作的出現是伊斯蘭地理學家對已知世界的面貌和感知方式發生變化的反映,從希臘托勒密地理學傳統轉向阿拉伯傳統的自然地理學,而伊德里斯的世界地圖則是中世紀阿拉伯地理學中第一次嘗試將希臘、拉丁和阿拉伯學術傳統繪制在一部已知世界的概述中[9]48。1154年11月14日西西里的謝里夫·伊德里斯完成《渴望周游世界者的娛樂》(簡稱《魯杰羅之書》),這本書包含一幅世界地圖和六十九幅區域地圖。依據作者的觀點:“我們進入每個分區,其中包括村鎮、轄區和區域,這樣讀者就可以看到平時看不到或不了解,抑或由于路況險要或民族習性不同而無法親自前往的地方。讀者可以通過看地圖來糾正某些信息。”[9]49伊德里斯著作中提及的早期地理學家包括八世紀的波斯地理學家伊本·胡爾達茲比赫,九世紀亞美尼亞人地理學家艾哈邁德·本·雅庫布(al-Yaqubi),十世紀的基督教修士埃爾西奧·安蒂奧士,十世紀的阿拉伯地理學家豪蓋勒(Ibn Hawqal) 和馬蘇第和《珍異記》,克洛德(Claude)家族的托勒密[10]192。伊德里斯的地理學知識主要來自兩個傳統:希臘托勒密的地理學傳統和早期伊斯蘭地理學的巴勒希學派(如圖2)。
托勒密的《地理學》最早被譯為敘利亞文,十二世紀才譯為拉丁文傳入歐洲。Djughrafiya這個語詞的出現是與《地理學》在伊斯蘭世界的傳播有關。荷蘭東方學者德·胡耶1879年至1939年編輯出版的《阿拉伯輿地叢刊》(Bibliotheea Geographorum Arabicorum)收錄的馬蘇弟著作中,解釋為“大地的區劃”(qat’al-ard),并在《雅致的信札》(Rasa’il Ikhwan al-Safa)中第一次從“世界與各地圖繪”的意義上使用Djughrafiya(地理)這個詞。于阿爾在《阿拉伯文獻》中說“阿布阿卜達拉赫·薩里夫·埃德里奇(Abu’Abdallah as-sarif al-Edrisi),1099年生于休達(Ceuta),一個阿里先知后裔的家族,曾在科爾多瓦攻讀,做過長途旅行,后來到西西里諾曼國王羅杰二世的宮廷,1154年為國王撰寫了一部地理巨著,該書由A·若貝爾譯成法文,但譯文并非令人滿意”[10]191。
阿里先知的后裔指哈木德王朝,1016-1018年哈木德的兒子納西爾(Ali’al-Nasir)作為塞托(Ceuto)統治的繼位者,1016年分別在馬拉加(Malaga)和科爾多瓦建立都城。卡西姆(’Al-Qasim al-Ma’man)于1018年至1023年在科爾多瓦執政。最后一位家族統治者為伊德里斯二世的兒子穆薩塔·里(Muhammd II,al-Musta’li)1054年至1056年執政。伊德里斯在科爾多瓦接受的教育,這個時期的科爾多瓦,伊斯蘭教、基督教和猶太教學者享有相對的自由,學術上對抗巴格達的阿拔斯王朝。
A·若貝爾這位出生于法國艾克斯普羅旺斯的東方學者,曾擔任拿破侖在埃及時期的翻譯。德·胡耶1866年出版的《伊德里斯關于非洲和西班牙的描述》一書的緒論部分,指出了若貝爾一些錯誤的觀點。關于伊德里斯的身世,存世資料很少。這位曾離開他出生地的學者在基督教國王的宮廷中尋求庇護,被視為是對穆斯林的背叛。在整個作品中,他敢于作出魯杰羅瞻仰的悼詞,雖然是對基督教做出的公正評價,但是在這個巴勒斯坦十字軍東征和西班牙的卡斯蒂利亞時期,他的做法激怒了穆斯林的統治者,使穆斯林信徒認為他的名字應該被遺忘。
魯杰羅在宮廷建立了一個地理學術團體,伊德里斯作為主要成員,十二位學者中十位來自穆斯林世界。魯杰羅去世前的伊德里斯世界地圖的拉丁文和阿拉伯文版本已制作完成,目前保存的主要寫本共有十處,時間較早的是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收藏的1300年編號MS.Arabe 2221和1344年制作編號為MS.Arabe 2222的兩個寫本,其中1300年的寫本繪制有地圖。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收藏的兩個寫本為十六世紀制作,均有地圖,其中編號為Pococke 375的寫本圖像保存完整,共計七十幅插圖。本文主要研究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收藏的編號為Pococke 375的寫本圖像(如圖3),這個寫本1553年在開羅制作,其中與中國有關的地圖共有八幅(如表2)。
伊德里斯可能沒有接受過天文學方面的訓練,在《魯杰羅之書》的序論部分只是附和了希臘和伊斯蘭的地理學資料,提到:“在超過十五年的時間中,無中斷的,不停的自行審查所有的地理問題,尋求解決辦法并確定事實的準確性,以便完全獲得他所希望的知識。”書中最值得稱頌的地方,即是他處理魯杰羅派人搜集來的多樣化信息的方法。
伊德里斯使用了托勒密《地理學》中分七個緯度氣候帶的方法,地圖以南方為上,區域地圖的城鎮標識盡可能詳細,以便于能夠正確認識朝圣麥加的準確方向。第一氣候帶貫穿赤道非洲至朝鮮,“第一氣候帶始于西海之西,也稱作陰影之海。因為在它以外,沒有人知道存在著什么。海上有兩個島嶼,稱為幸運島,托勒密從這里開始計算經度和緯度”[9]48。中世紀的拉丁文作者保羅·倫德(Paul Lunde)在他的論著《海格力斯之柱》(Pillars of Hercules)中提到大西洋,認為是黑暗之地(Mare Tenebrosum),阿拉伯語稱大西洋為Bahr al-Zalamat(黑暗之海),常用的書寫為al-Bahr或al-Mahit。
伊德里斯的地圖中雅朱者和馬朱者出現在中國北方(如圖3),在“亞歷山大邊墻”后面有一塊銘文,寫著“屬于包圍雅朱者和馬朱者的庫法亞(Kufaya)山脈”。邊墻有門,大門處標識了亞歷山大的阿拉伯名字杜爾—卡奈因(Dul-Karnai)。
九世紀中期的阿拉伯文獻《薩剌姆東使記》記載黑衣大食的“通事”薩剌姆前往東方的情況:
此城與邊墻之間有三天行程,其間有一些戍堡和村鎮,到第三天將走到邊墻跟前。那里是一座環形山。人們說雅朱者一馬朱者居住在其中。雅朱者與馬朱者是兩種人。雅朱者人比馬朱者人身材高些,他們身高約1腕尺至1.5腕尺左右。[11]
這部阿拉伯文獻是薩剌姆前往東方的旅行記。當時阿巴斯王朝人傳聞,“雅朱者和馬朱者”沖破亞歷山大大帝在東方建造來阻擋他們的邊墻“亞歷山大邊墻”,進入了文明地區。薩剌姆奉阿巴斯哈里發瓦西格之命前往東方,調查這個消息的具體情況。十世紀阿拉伯地圖上以雅約吉·瓦·梅杰(Yajoj wa Majoj)的身份開始出現雅朱者和馬朱者的標識,他們以同樣的名字出現在伊德里斯的1154地圖上。
伊德里斯的世界地圖區別于以耶路撒冷為中心的中世紀歐洲“T-O”世界地圖,也不同于以麥加為中心的巴勒希地理學派的世界地圖(主要描述伊斯蘭之境的神圣地理學),而是對自然世界的自然主義描述,這恰恰是伊德里斯地圖最有價值的所在。
三、從四海到七海
公元九世紀的伊斯蘭地理學家阿布澤德(Abu Zayd)在著作中提到:
在魯姆海(地中海)的克里特埃米爾國,發現了印度柚木的船板,它們被穿孔和使用椰子樹纖維縫合。他們是被海浪摧毀的船只,被海浪拋到了此地。只有阿比西尼亞海[印度洋]有這種類型的船只,因為所有魯姆海和西邊的船只都是使用鐵釘固定,而阿比西尼亞海的船只卻沒有用鐵釘固定,因為海水能溶解鐵。因此,阿比西尼亞海的人們用纖維代替釘子,船上涂了油脂和石灰。這證明海洋是連接在一起的,中國附近的海在土耳其人的周圍,穿過環繞海洋的海峽到達了地中海的西部。
中世紀阿拉伯地理學家馬蘇弟在其著作《黃金草場》(Muruj al-dhahab wa-mdadin al-jawhar)提到的七海指:波斯灣、坎貝灣、孟加拉灣、馬六甲海峽、泰國灣、南海和中國海[12]。
伊德里斯文本第五十九頁:
……中國人便將其貿易轉向阇婆格及其附屬島嶼,與阇婆格島民頻繁接觸。
法國學者費瑯注釋說:原文中常將“Zabag(阇婆格)”誤寫為“Zanag”。在伊德里斯的記述中,非洲東部的僧祇海岸相對的則是阇婆格諸島,這是依據了托勒密對印度洋的觀點,即印度尼西亞的爪哇和蘇門答臘諸島位于非洲東海岸的對面。
伊德里斯文本第六十三頁:
本節和前一節所提到的海乃阿曼海,其印度語哈爾干海。
費瑯注釋說其記述是錯誤的,哈爾干海應指孟加拉灣。
伊德里斯文本第七十八頁:
該節包括對取名中國海的印度洋部分以及取名達拉爾維(Dārlāzwl)海的描述。
伊德里斯文本第八十七頁:
繼印度海和中國海之后,便是穆賈島(Mūdja)、蘇馬島和馬伊德島(Māyd)。
本節包括上述東方這些有人煙之地區,再往東便是一無所知了。中國海又名漲海,也有人稱其為占婆海,乃黑色海之一部。實際上中國海也的確如此,一向受強風影響,咆哮沸騰,晝夜不停。
伊德里斯文本第一百九十一頁:
從魯金沿印度斯坦海岸到哥古羅(Kakula)七日行。哥古羅位于一條河沿岸,此河流入印度洋的巴赫納克(Bahnak)。這里的居民普遍養蠶。此乃一種哥古羅絲綢和一種哥古羅布的來歷。從哥古羅到克什米爾十日行。[10]216
地圖圖像之間的并置和比較研究,體現了地圖作為一種媒介形式在知識生成、傳遞和演變的客觀歷程中的重要作用。將中國(和朝鮮)輿圖中的相關部分與伊斯蘭同時期的地圖圖像作比較,例如《大明混一圖》和《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中的意大利半島,李軍教授認為,“完全可能是因為摹寫者對伊斯蘭原圖中巴爾干半島上那道山脈產生誤讀,把它當成河流或海洋之一部分來加以釋讀的結果”。
甚至于中國和朝鮮地圖中非洲大陸為什么朝南的問題,也可以得到圖形學或藝術史方面的解釋。把非洲南端表現為朝東,是同時期伊斯蘭地圖的普遍做法;上述二圖把非洲大陸表現為朝南,確乎是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大部分中國學者傾向于將此看作中國繪圖者的偉大成就或者“先知先覺”,但實際上,這極可能是一個圖形與方位因素變異而導致的偶然結果。[13]
《元史·天文志》載:“其制以木為圓球,七分為水,其色綠;三分為土地,其色白,畫江河湖海脈絡,貫穿于其中,畫作小方井,以計幅員之廣袤,道里之遠近。”[14]七分為水,則指七海,其意則為環繞陸地之海的分布。元代初期七海觀念已進入了中國人的視野。
四、結語
作為一種圖像媒介,地圖是視覺性和空間性的。由此,它主要作為描述的特征而非敘事的特征顯示自身。時間性的記憶本身就是形象性的,形象性與空間性是記憶的根本性特征。語詞和圖像的關系既不能理解為一種相互獨立的符號系統,也不能獨自作為圖像來對待,因為圖像的解釋是借助于語言來進行的。語詞和圖像在圖畫中是相應相合和互補合作的關系。地圖作為圖像是一種始終存在著彼此介入的“異質圖畫”。
地圖作為圖像不能局限于“注視的邏輯”的視角,同時也是對于世界的“自然”視覺經驗的研究,這更接近于胡塞爾現象學的圖像意識,觀看則是圖像意識被主體化的過程。地圖是一個一般概念,它分化出各種具體的類似物,用“知識圖形”把世界整合在一起。
注釋:
①本文是2018年1月26日湖南省博物館“在最遙遠的地方尋找故鄉:十三至十六世紀意大利與中國的跨文化交流”展覽展品的個案研究,感謝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李軍教授給予的指導。
參考文獻:
[1]David Woodward.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7.
[2]羽田正.“伊斯蘭世界”概念的形成[M].劉麗嬌,朱莉麗,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63.
[3]邁蒙尼德.迷途指津[M].傅有德,等譯.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8:23.
[4]苗力田.亞里士多德全集(第3卷)[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251.
[5]方維規.概念史八論——一門顯學的理論與實踐及其爭議與影響 [J].東亞觀念史集刊,2013(4):101-170.
[6]米歇爾.圖像學:形象、文本、意識形態 [M].陳永國,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50.
[7]倪梁康.圖像意識的現象學[J].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01(1):32-40.
[8]朗西埃.圖像的命運[M].張新木,陸洵,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76.
[9]布羅頓.十二幅地圖中的世界史[M].林盛,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48.
[10]費瑯,輯注.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M].耿升,穆根來,譯.北京:中華書局,1989:192.
[11]劉迎勝,主編.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第26輯)[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118.
[12]Aloys Sprenger.The Meadows of Gold and Mines of Gems [M].1841:311.
[13]李軍.圖形作為知識——十幅世界地圖的跨文化旅行(上)[J].美術研究,2018(2):68-77.
[14]宋濂.元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6.
作者簡介:焦占煜,四川工商學院藝術學院教師,主要從事設計史論、藝術史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