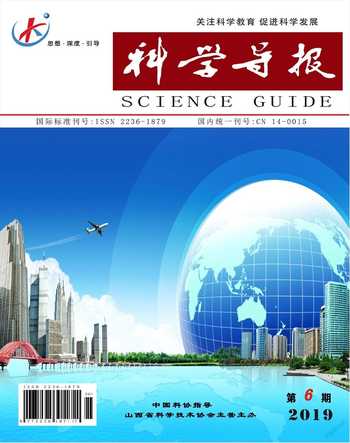鄉土回歸與絕望重現
摘 要:《野草》是魯迅創作生涯中的唯一一部散文詩集,整體意蘊較為沉重,所體現的自我解刨、自我反思的個人勇氣,是來自靈魂深處的吶喊,因而《野草》依舊延續“反抗絕望”的主題。但《雪》、《風箏》、《好的故事》卻在絕望中回憶故鄉,帶有濃濃的溫情與愛意,不僅成為《野草》集中的“異類”,與其他鄉土小說也存在巨大差異。而《雪》、《風箏》、《好的故事》內部的共通性以及與《野草》其他文章的互聯性,又是《野草》集內在統一性的體現。
關鍵詞:魯迅;《野草》;故鄉;絕望
魯迅通過《野草》與自我對話,觀照內心最隱秘的區域,讓我們看到了他孤獨、冰冷的內心,文本語言和意象具有復雜性與多義性,增強了文本意蘊容納量,眾多學者對其進行解讀,可謂眾聲喧嘩,研究涉及方方面面。
本文基于對《野草》的閱讀感受,引發疑問,在整體意蘊較為沉重的《野草》中,《雪》、《風箏》、《好的故事》在絕望中回憶故鄉景與人,帶有濃濃的溫情與愛意,那么,魯迅為何要用大量字符,極盡瑣碎地描寫故鄉,為何將這三篇文章收入《野草》。因而此次研究將《雪》、《風箏》、《好的故事》視作一個整體,以下簡稱“三篇文章”,從三篇文章的鄉土故事的書寫方式以及故事背后的絕望命題的呈現兩個方面試圖回答以上問題。
一、鄉土故事的書寫
分析《野草》中鄉土故事的書寫,從敘事學的角度講,必然涉及情節、人物、環境以及它們的構成狀態。由于其書寫重點沒有放在人物塑造上,因而這一章節將著重論述三篇文章的鄉土故事中關于情節與環境的書寫方式以及書寫意義。
《野草》在文體分類中,屬于散文詩,不以故事情節的高潮或懸念的設置取勝,三篇文章中的情節性較弱。《雪》開篇由“暖國的雨”引出“江南的雪 ”,接著描述江南雪景,突然插入孩童們與父親一起塑雪羅漢的溫馨片段,且占用了兩個自然段的字符,另外,在這兩自然段中,百分之四十的字符是對雪羅漢外形的描寫;《好的故事》不過是“我”睡著進入夢境,醒來夢境破碎,可見《雪》、《好的故事》并沒有多少情節因素。而《風箏》被認為是這三篇文章中情節性最強的,人物動作因素比重最大,相反,“故事中非動作因素比重增大是情節淡化的一種極端形式”了。
相反,魯迅在對鄉土故事的書寫過程中,環境因素在文本中最重,《雪》、《風箏》、《好的故事》三篇文章中均有大段的環境描寫。
那些溫潤美好的文字時,使人不自覺地聯想到《彷徨》、《吶喊》、《朝花夕拾》中的某些篇目,《雪》讓我們想到魯迅坐在故鄉酒樓上,遠遠看到幾株赫赫的開著紅花的山茶,《風箏》讓我們想到我的“小兄弟”少年閏土,《好的故事》讓我們想到同樣色彩斑斕的百草園,那里有“碧綠”的菜畦、“紫紅”的桑葚、人形何首烏、小珊瑚般的覆盆子,這一切都如此美好溫馨,樂趣無限。而其他篇目是絕不會產生類似的聯想。
情節的簡單化處理與大量帶有故鄉色彩的環境描寫,兩者互為表里,共同打造了一個別樣的帶有鄉土氣息的藝術世界,那都是魯迅對故鄉印象的再次書寫,不可避免地加入自我理想家園的模樣,加之這個書寫的過程本身就是再創造的過程,細細讀來就會覺得魯迅將現時的生命體驗以及希望寄托藏于其中,在閱讀的過程中,我們的情感曾處于那不可多得的溫暖之中,因而才會不自覺得聯想到其他同樣書寫故鄉,帶有同樣溫情色彩的《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故鄉》等文章。
三篇文章在《野草》整體較為壓抑、灰暗的氛圍中,對鄉土故事的書寫成為《野草》中的“異類”。同時,不注重情節的構建和人物的塑造,與他一貫的鄉土小說的敘事模式產生了較大的區別,這也正是散文詩與小說在文體功能上的區別,因而三篇文章中獨特的藝術世界,不僅是《野草》中的“異類”,也是魯迅文學世界中的“異類”。
二、絕望情感的重現
翻閱魯迅的書信集,發現魯迅與蕭軍的通信中曾提及《野草》:“我的那一本《野草》,技術并不算差,但心情太頹唐了,因為那是我碰了許多釘子之后寫出來的。”。在此種創作心理下,使用大量字符,近乎瑣碎地描寫故鄉,有何用意呢?
魯迅傾盡心力將如詩如畫的故鄉融進三篇文章之中,使得它們呈現出同一個主題——“歸鄉”。可魯迅并沒有完全留戀故鄉的景與物,在《雪》、《風箏》、《好的故事》三篇文章的最后,魯迅都會把思緒從對故鄉記憶的書寫中抽離出來,將目光投向現實。
《雪》中的雪羅漢,連續的晴天消釋了它的皮膚,終究不能舊存,“雪羅漢的消融,標志著魯迅精心營造的“故鄉”與“童年”記憶又重歸虛無,而《雪》之篇章行文的情感氣脈似乎也就此戛然而止。”魯迅緊接著把目光轉向朔方的雪,他看到了朔方的雪的蓬勃的生命力:
“永遠如粉,如沙,他們決不粘連,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在晴天之下,旋風忽來,便蓬勃地奮飛。”
朔方的雪與暖國的雪的狀態雖然是完全不同,但無非是雨在低溫狀態下的兩種存在狀態,一種滋潤美艷,一種蓬勃奮飛。,魯迅在這種“斗爭式”寫作方式中十分關注人的生命狀態,來反思人的存在方式、價值與意義,或許他希求的是中國新一代青年的生命也如朔方的雪一般堅韌。
但當他回憶起“‘我’禁止小兄弟玩風箏”一事后,表面上看,他是希求小兄弟對他的寬恕,實際上他希求的是兒童能充分釋放天性,得到童年歡樂。就像魯迅在《雪》中回憶的故鄉的孩子堆“雪羅漢”時那樣。而“我”則以長子的身份,限制小兄弟玩風箏,對其實施了“精神虐殺”,將兒童最正當的行為視作笑柄。魯迅認為孩子要有區別于成人的獨特的生命存在方式,成人應承受孤獨,直面嚴寒,而孩童應自由自在的,活潑自然的成長,成年人要主動去保護、支持其發展。
接下來,魯迅帶著這些美好希求,進入到《好的故事》中,他捏著《初學記》,半仰在椅背上,不自覺地進入了一個美麗的“幻境”,那里有“許多美的人和美的事”,但夢境很快結束,好的故事也隨之消失殆盡。
“魯迅的藝術力量似乎有一種罕見的品行,他能夠把一股強烈的生命氣息灌注到作品描繪的那些獨特而真實的性格和情境中,使他們超越了自身的現實狀況而達到一種形而上的境界。”。在前兩篇文章中,魯迅被眼前的雪和風箏,勾起兒時故鄉的回憶,在故鄉景與物的敘寫中,滲透著對“人”生命應當如何存在的哲學式理解。但魯迅在現實世界中,找不到健康的生命的存在,只能在腦海中,虛構一個適宜孩童和青年人生存的幻境,然而就連幻境最終也被撕破了……“至此,作者完成了他的全部的構思和命意:昏暗的現實給予他的只有絕望和虛無,孤獨和寂寞。美的東西只存在于短暫的夢境中。”
在魯迅“鄉土回歸”主題的最底層,我們看到的卻是深深的恐懼與絕望,“在虛無的過去與虛無的將來之間,用現實的生命活動(‘走’)筑成了‘現在’的長堤,從而使自己成為生命和時間的主宰,誕生出‘反抗絕望’的哲學主題”。
因此,“希望—絕望”所形成的張力一直存在于《雪》、《風箏》、《好的故事》三篇文章中,其實這也是整個《野草》的內核所在,從開篇之作《秋夜》開始,魯迅就進入到了一個悲傷凄涼的夜晚,但他并沒有放棄希望,而是在絕望中苦苦尋求光明。因而《雪》、《風箏》、《好的故事》不僅在這三篇文章中存在內在連貫性,與整個《野草》也存在了一定的內在聯系。
結語
《野草》是魯迅在中年時期與自我對話、自我反思的結晶,是“獨語體”的代表之作,語言較為隱晦,多義性強,因而此次研究,更加注重文本的分析和整合,發現《雪》、《風箏》、《好的故事》以故鄉為底色進行書寫,故將其視作一個整體,納入到魯迅一貫的“鄉土回歸”的主題創作之中。但這三篇文章與散文詩集《野草》的關系并不是割裂,這三篇文章的存在反而使得《野草》的主題“反抗絕望”的主題更加深刻、完整。
參考文獻:
[1] 魯迅.《魯迅全集》[M],第1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
[2] 胡亞敏.《敘事學》[M],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3] 汪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4] 汪暉.《魯迅小說的精神特征與“反抗絕望”的人生哲學》[M],《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論》(第1卷),東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
[5] 李哲.“雨雪之辯”與精神重生魯迅《雪》箋釋[J].文學評論,2017(1):171-185.
[6] 孫玉石.現實的與哲學的(連載六)──魯迅《野草》重釋[J].魯迅研究月刊,1996(6):17-29.
[7] 李玉明.魯迅生命的兩種形態及底色——《雪》新論[J].東方論壇,2018(2).
[8] 李玉明.《風箏》:尋找精神家園[J].山東社會科學,2011(1):150-152.
[9] 李玉明.《好的故事》:心靈上的“回鄉”[J].山東社會科學,2011(1):153-154.
作者簡介:
張曉晗(1997-8)女,漢族,山東日照人,現就讀于青島大學文學院,全日制碩士研究生,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