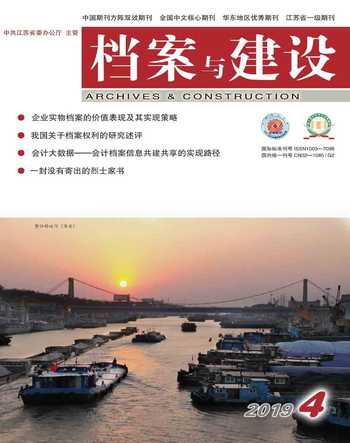中國大運河:一項概念史研究
李玉巖 潘天波
[摘要]中國大運河是中國南北交流需求不斷深化的產物。從春秋戰國時期開始至今,中國大運河積淀了豐厚的文化資源,積累了厚重的精神產品,形成了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本文以概念史作為中國大運河研究方法,從時間、空間、功能上闡述運河概念的演進。隨著歷史的變遷,中國大運河概念內涵不斷豐富,其價值意義不斷被深化。
[關鍵詞]中國大運河概念史運河文化
一、南北往來之中國大運河
中國大運河是人工開鑿的通航河道,與自然水道或其他運河相連,用以溝通地域、水域區間。中國大運河主要有三條:隋唐大運河、京杭大運河和浙東運河。隋煬帝因長安城不能適應其發展,遂遷都洛陽。隋唐大運河以洛陽為中心,北經焦作、新鄉、鶴壁、安陽、邯鄲、邢臺,達北京(古稱涿郡),南通鄭州、開封、商丘、淮北、宿州、常州,至杭州(古稱余杭)。隋煬帝動用百余萬百姓,于605年至610年疏浚古時開鑿的舊河道,修成隋唐大運河。京杭大運河是世界上最長的古代運河,連接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長約1797千米,南起杭州,流經嘉興、湖州、蘇州、無錫、常州、揚州、淮安、宿遷、徐州、棗莊、濟寧、泰安、聊城、德州、衡水、滄州、天津,到北京。春秋末期,吳王夫差為北伐齊國,于公元前486年開始,引長江水入淮。后不斷向北向南延長,經隋、元兩朝大規模擴展、整治,京杭大運河基本形成。浙東大運河即杭甬運河,由西到東經杭州、蕭山、紹興、寧波。春秋時開鑿紹興山陰故水道,西晉時開挖西興運河,后與曹娥江形成西起錢塘江,東至東海的完整運河水道。南宋時期,浙東運河因南宋建都臨安,成為最重要的航道。
中國大運河是京杭大運河、隋唐大運河、浙東運河的總稱。2006年,京杭大運河被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2年隋唐大運河和浙東運河被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4年,中國大運河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中國大運河由南向北,一路匯集多條自然河流。“吸納了京津、燕趙、中原、齊魯、淮揚、吳越等六大文化帶的文化資源,沿線積淀了豐厚的文化資源:漫長的河道,無數的碼頭、船閘、橋梁、堤壩及沿岸的衙署、鈔關、官倉、會館、廟宇和驛站,厚重的精神產品:文學、藝術、民俗、史學等,還有運河沿岸各種文化節慶及帶來的品牌符號,形式多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1]
概念史又稱歷史語義學,即一種史學類型,最早出現于黑格爾《歷史哲學講座》。李里峰認為:概念史研究各種文化中重要概念及其發展情況,并展示特定詞語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的語境和聯想。其獨特的歷史視角、考察維度模式不同于實證主義方式的研究。“‘語境’、‘概念’和‘修辭’是其思想史研究的三個關鍵詞,其中‘概念’既是思想觀念的核心和內涵,也是研究思想觀念的重要載體和基本‘單位’。”[2]研究中國大運河的目的,并不是為了慎終追遠,而是探尋中國大運河流域的互動關系。研究中國大運河不能被現在的知識制度、觀念視野、思維習慣等禁錮,而是從不同的維度出發,對其進行闡述。可通過中國大運河概念的遷流,對其背后的歷史環境、社會背景進行新角度、全方位的解讀。
二、中國大運河概念之演進
中國大運河概念史的研究對象是運河,那么怎么定義運河呢?普遍觀點,人工開鑿的用于運輸的河流稱為運河。中國大運河概念是一個變化的過程:大運河起初被界定為貫通于隋朝的隋唐大運河;元代以后,大運河指貫通于元代的京杭大運河;為申報世界遺產,提出包含整個大運河工程體系的中國大運河概念。
(一)從時間上看中國大運河概念
根據時間維度,中國大運河概念的演變可以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春秋戰國時期“邗溝”之概念。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戰事頻發。吳王夫差要北上伐齊,爭霸中原,但齊國路遠艱險,道路不暢,依靠陸地運輸戰事所需軍糧和輜重等物資不切實際。當時吳國擅水,其優勢即水軍和先進的造船、開河、航運等技術。那時長江與淮河之間并不互通,走海路又風疾浪大,風險甚大。因此,公元前468年,吳國利用長江三角洲至淮河間天然河湖港汊密布的自然條件,就地度量,局部開鑿,連接幾個湖泊,通了由今蘇州經無錫至常州,北入長江到揚州的“古故水道”,自揚州向東北經射陽湖,再向西北到淮安入淮河,即為邗溝,從此貫通長江與淮河。此之為邗溝,蓋因此運河以南端古邗城為起點。邗溝是淮揚運河的前身,中國大運河最早開鑿的河段,中國大運河的重要組成部分。后秦、漢、魏、晉和南北朝繼續延伸河道,先后開鑿了大溝與鴻溝,從而連通江、淮、河、濟四大水系。
第二階段,隋朝至宋朝時期“漕河”之概念。隋朝出現漕河之名,宋朝延續隋之說法,漕河被廣泛使用,同時運河一詞開始出現,《四庫全書》中,宋代使用運河之名的文獻多達90余種,有“運河之大利”的說法。南宋江南運河河段首次出現“大運河”之概念。很長一段時期,黃河流域一直是經濟重心,北方比南方經濟進步。到魏晉南北朝時,四百多年的混亂,使得社會發生深刻變化,北方經濟受到重創和沖擊,南方經濟則發展迅速,成為了國家經濟的重心。隋煬帝即位后,由長安遷都洛陽,經濟主要依賴江淮,格外重視江淮地區,但其政治中心不能隨經濟重心的變化而南移,因此隋需加強對南方的管理,洛陽需與江淮富庶經濟區域溝通,北方需南方糧食物資供應。同時,長時間的分裂割據,使得國家南北交流被阻斷,但隨著生產力水平的上升、經濟的發展,這時迫切需要加強南北經濟、貿易的聯系。公元587年,隋興兵伐陳,從今淮安至揚州,改造邗溝,稱山陽瀆,又整改取直,不再繞道射陽湖。公元605年,隋煬帝征集百萬民工,開鑿通濟渠。通濟渠又名汴渠,是漕運的干道,西起今洛陽,引谷、洛二水入黃河,經板城渚口引黃河水入汴河,繼商丘、宿縣、泗縣等入淮河,直接溝通黃河和淮河。公元608年,又征發黃河以北民工,開永濟渠,引黃河支流沁水入今衛河至天津,北通涿郡。公元610年,由今鎮江經無錫、蘇州、嘉興到杭州,通錢塘江,開通了江南運河。至此,基本建成以洛陽為中心,由永濟渠、通濟渠、山陽瀆和江南運河相連組成,北通北京,南至杭州,全長2700余千米的漕河(隋唐大運河),形成多枝形運河系統。唐宋朝時,對其作過一些修整,浚河培堤筑岸,以利漕運纖挽。
第三階段:明清時期“運河”之概念出現。明清時期的運河多指京杭大運河,此時“運糧河”這一概念多在北方流域使用,明朝正史文獻雖稱之為運河,但《明史》記載多為漕河,此時其他地方志、專書等亦多用漕河之名。清朝設置“北運河”之管理機構,通常使用通惠河、北運河、南運河及江南運河之稱呼。明、清兩朝皆建都北京,在元運河的基礎上,對其進行擴建重修。明朝疏浚淤廢的通惠河閘壩,在山東河段進行黃運分離的開泇口運河、通濟新河、中河等運河工程,恢復通航。1411年擴建改造會通河,引水修柜,解決其水源問題,并增建船閘。為避免受黃河泛濫影響,改經沛縣、徐州入黃河的原泗水運河路線為經夏鎮、韓莊、臺兒莊到邳縣入黃河的今韓莊運河線。為保障運河通航安全,在洪澤湖、高郵湖一帶修建運河西堤,運河東堤修建平水閘,用來調節此段運河水位。清朝,在黃河東側,今駱馬湖以北至淮陰開中河、皂河,北連韓莊運河,南通今里運河。至此,運河線路與黃河河道完全分開。明清兩代,國家高度重視運河之漕運,設置漕運總督及河道總督,掌管運河漕運管理和運河水利管理,運河沿岸城市因漕運而迅速發展、繁榮。運河(京杭大運河)即南北方交通的重要脈絡。
第四階段:建國以后“中國大運河”之概念。建國后分別于1953年、1957年修建船閘,對大運河進行部分恢復和擴建工作。1959年后,結合南水北調系列工程,重點擴建徐州段至長江段的運河河段,采取擴大沿岸灌溉及排澇面積等措施。申報世界遺產時,發現京杭大運河不能包含整個大運河工程體系,于是提出了中國大運河的概念,但是此時的中國大運河只包括隋唐大運河和京杭大運河兩條線路。2009年,從文化遺產保護及國家政治、經濟、文化戰略入手,浙東運河被加入到中國大運河概念中。由此,中國大運河概念得到科學系統、完整的定義。中國大運河是由申報世界遺產應運而生的一個新詞匯、新概念,應從世界遺產的視野出發,以《中國大運河申報世界遺產文本》中對中國大運河的科學、系統、完整的界定為依據,解釋中國大運河的概念:“中國大運河是世界唯一一個為確保糧食運輸安全,以達到穩定政權、維持帝國統一的目的,由國家投資開鑿、國家管理的巨大運河工程體系。”[3]中國大運河在英語中,表達為“The grand canal”。
(二)從空間上看中國大運河概念
根據空間維度,中國大運河指自春秋時期開鑿邗溝以來,以洛陽為中心的隋唐大運河、以北京為中心的京杭大運河及浙東運河的總稱。中國大運河概念包括以下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隋唐大運河。此因隋朝修建,唐朝完善得名。古書記載:“北至涿郡,南至余杭。”其以洛陽為中心點,北通焦作、新鄉、鶴壁、安陽、邯鄲、邢臺、衡水、滄州至北京,南經鄭州、開封、商丘、淮北、宿州、常州、無錫、蘇州、湖州、嘉興到杭州。隋唐大運河跨越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河南、安徽、江蘇、浙江等八個省、直轄市,地跨十多個緯度,縱貫華北平原與東南沿海,是古代中國南北交通的重要脈絡,亦是中國古代勞動人民建設的一項偉大的水利建筑工程。隋唐大運河由永濟渠與通濟渠兩大水線組成,貫通南北。大業四年(公元608年),隋煬帝征召百余萬民工,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今北京),其疏浚前面王朝開鑿遺留下的人工河道和自然水道。今河南武涉至汲縣段運河,即沁水、衛河連接而成;汲縣達館陶段運河,即曹操遏淇水入黃河古道白溝所成;館陶及滄州段運河,由漢代屯氏河和西漢大河故瀆相通;滄州到涿郡段,利用漳水,經獨流口與漳水相離,另辟新道,再與漯水相接。唐朝則不懈地對隋唐大運河進行了數度開鑿、疏浚、整改和修繕。可以概括為:“四疏汴渠,五浚山陽瀆,三治江南運河,二鑿丹灞水道,三治褒斜道,疏浚嘉陵江故水道,治理靈渠,黃河汾水道。”[4]這里的次數只是大型疏浚整頓的次數,實際上,運河通塞不定,疏浚與整治是經常而頻繁的。唐朝對隋唐大運河的開鑿、整治、疏浚是窮盡其力的,因此運河沿岸的干流和支流得以通暢,漕運事業得以興旺。通濟渠又名汴水,將黃河與淮河相連,是重要的中原渠道。由于連接黃河,所以河水含沙量較大,容易造成淤泥堵塞。"塞長茭,決沮淤",是每年初春必須的工程,否則河道淤積,阻斷漕運,不良于航。隋唐大運河的概念代表著連接長江、淮河、黃河、海河、錢塘江等水系的水利工程已經形成,加強了中國南北經濟的溝通與交流,代表著沿岸城市借助大運河繁榮發展。
第二部分:京杭大運河。此為連接北京與杭州的運河河道。由杭州經嘉興、湖州、蘇州、無錫、常州、揚州、淮安、宿遷、棗莊、濟寧、泰安、聊城、德州、衡水、滄州、天津至北京。流經天津、河北、河南、山東、江蘇、浙江等省、直轄市,連接海河、黃河、淮河、長江和錢塘江等水系。京杭大運河對中國南北區域之經濟、文化的發展與交流起到重要作用,特別對沿岸城鎮的興起與工農業經濟的發展起到推動性作用。京杭大運河沿岸區域,是中國最富庶工農業區之一。兗州、棗莊、滕州、沛縣、徐州、淮安等皆有大中型煤礦,蘇州、揚州、淮安、宿遷紡織業發達。京杭大運河建成于隋朝,此時運河全線貫通;繁榮于唐宋,發展運河河道;取直于元代,溝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等五大水系;疏暢于明清,對運河河道之淤泥黃沙進行疏浚疏通。前后共經歷了三次大型整修活動。唐代皮日休在《汴河懷古二首·其一》:“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近代時期,興建鐵路、公路,導致京杭大運河的作用逐漸減小衰落。建國后,國家對淤泥堆積河段進行疏浚,部分河道擴寬加深,裁彎取直,建設現代化碼頭、船閘,改善航道條件。京杭大運河亦是漕運要道,其在南北文化交流與融合、南北交通與中央集權統治、江南地區經濟建設、南糧北運等方面有著重要的作用。
第三部分:浙東運河。此為浙江東部的運河,又被稱為杭甬運河,西起杭州,跨曹娥江,經紹興,東至寧波。據《越絕書》:山陰故水道起于范蠡修建山陰大城東郭門,終于上虞東關練塘,長20千米。由此可知,春秋時期就已開鑿當時的“山陰故水道”。西晉開挖西興運河,形成西始錢塘江,東及東海的運河線路。隋朝寧波經余姚、曹娥與杭州相連,寧波事實上成為大運河的南端終點。南宋浙東運河成為重要的航運主道。清朝乾隆年間,朝廷制作的《大運河全圖》第二部分即有從紹興經杭州的河段,可證明浙東運河為中國大運河的南端起點。建國后,浙東運河經過多次疏浚整治,新建附屬設施。浙東運河河段自然河流較多,為維持不同水域水位差,修建很多堰壩、碶閘和橋梁,組成了重要的運河遺產。眾多瓷器、漆器、紡織品、茶葉等貨物,通過浙東運河運往日本、朝鮮及其他海外地區;其短途航運亦十分發達,河岸城鎮多通過浙東運河進行貿易交流、文化溝通等。浙東運河最初目的,即便于灌溉兩岸農作物。浙東為古代重要的漕糧征發地,鹽米及其他物資由此運往其他各地,因此浙東運河承擔著漕運的任務。由于上述原因,浙東運河被認為是中國大運河重要的一部分。
(三)從功能上看中國大運河概念的演進
從功能視角出發,中國大運河是一個工程體系,解決了古代中國南北社會、自然資源極度不平衡的狀態,以時間和空間維度展現農業文明時期人工開鑿運河的技術發展水平,是工業革命前水利工程的重大成就。“它實現了在廣大國土范圍內南北資源和物產的大跨度調配,溝通了國家的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促進了不同地域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在國家統一、政權穩定、經濟繁榮、文化交流和科技發展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5]中國大運河千百年歷史中,在修筑、疏浚、整治的過程里,流經的各個城市賦予了不同的功能價值。其一,從經濟層面看,中國大運河為南北經濟的交融,推動北方經濟,江浙經濟帶動沿岸其他城鎮經濟方面,有著助力的作用;其二,從政治層面看,中國大運河加強了統治階級中央集權的政治,有利于都城對其他地區的管理,改善了上令下達的溝通條件;其三,從運輸層面看,中國大運河增加了南北運輸通道,減少了運輸成本,為南北商品貿易的交流與發展提供了渠道;其四,從農業層面看,中國大運河為農植物的灌溉提供了便利條件,提升了農作物的生產條件,提高了沿岸居民的務農效率;其五,從文化風俗層面看,中國大運河加強了南北方文化的交流,擴大了各地風俗影響,積淀了地區文化底蘊,促進了思想層面的互動與溝通。“運河文化是人類在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通過跨自然水系的通航、漕運,促進運河流域不同文化區在思想意識、價值形態、社會理念、生產方式、文化藝術、風俗民情等領域的廣角度、深層次交流融合,推動沿運河流域的社會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的全面發展而形成的一種跨水系、跨領域的網帶狀區域文化集合體。”[6]中國大運河經過了千百年的發展,為后世留下來無數物質文化、非物質文化。
三、中國大運河內涵之變化歷程
中國大運河代表著被傳承的運河歷史、地理環境、風土風俗、文學藝術、思想觀念乃至價值信仰等。其有別于其他河道的內涵特征是人工開挖,其社會屬性是貫通南北。但是,中國大運河概念內涵是隨著社會時代的不同而變化的。中國大運河的內涵演變經歷了軍事、漕運、文化這三個方面,層層遞進,愈加深入。
(一)中國大運河內涵之軍事
中國大運河不僅是一條運輸交通線路,更是一條重要的軍事戰略河道;其不僅是南北交流、溝通、互動之通道,亦是區域矛盾、沖突的高峰地帶。春秋戰國時期,吳王為爭霸中原,及時補給軍事物資,憑借其先進的水軍及開河、造船、航運之技術,利用長江與淮河間河湖繁多之便利,就地開鑿,局部深挖,將其連接起來,運送軍事所需物資,為其遠征伐齊做準備。隋朝時,南部地區經濟地位不斷提高,作物產量亦比北方先進,隋煬帝為向南部地區顯示其中央集權之力量開通濟渠,為北上向高麗用兵開永濟渠。隋朝結束了古代中國近千年的分裂割據的局面,實現了全國統一,為鞏固其政治權力,積極有效地統治這片幅員遼闊之疆土,需要一條連接南北之通道。明朝朱元璋北伐,即沿運河進軍,打至開封,繼續北上,與運河運輸軍糧密不可分。明成祖靖難之役即沿運河一路南下。清朝后,外國軍隊從長江涌進,封長江和運河口岸,割斷揚州與鎮江之脈絡,迫使清政府簽訂“城下之盟”。八國聯軍攻占大沽炮臺,占領天津,沿白河水路前往北京東大門通州,即中國大運河之北方端點,從這里直接進攻北京城。“如果鎮江、大沽不保,無法保證大運河的安全,大運河通往北京的路線就中斷了;如果海路遭到封鎖,大運河尚可作為備用航道,但如果大運河衰敗不通,則清朝南北重載運輸通道就完全失效,這在甲午戰爭中不幸成為現實。”[7]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八國聯軍侵華等重大戰爭,或直接發生在中國大運河沿線,或間接與之關聯。回看歷史,中國大運河對封建統治者中央集權,鞏固發展政權,保證軍事所需的大量糧草等作出重要作用。由此,中國大運河與軍事有不可忽視的聯系,是一條比較安全的軍事戰略通道,具有很高的軍事戰略價值。
(二)中國大運河內涵之漕運
中國大運河為歷朝歷代漕運之要道。漕運為古時中國特有的一種水運模式,指“封建王朝通過水路將各地的糧食等物運至京城(或其它指定地點),以滿足官俸、軍餉和皇室的消費。”[8]秦漢時期,漕運已有之。隋朝大運河以洛陽為中心,北至北京,南至杭州,“商船往返,船乘不絕”。中國“政治重心長期位于黃河流域中原地帶,這一地區由于連年戰亂,田園荒蕪,無法就近滿足朝廷和京都的需求。而南部長江流域因自然條件較好,加上春秋以來大批黃河流域居民因逃避戰亂南遷,使這一帶的農業和手工業發展較快,形成國家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相脫離的局面。”[9]唐宋以后,經濟重心南移,漕運愈發重要,更是運河輝煌的時期,這時的大運河截彎取直,大大縮短了其里程。明代漕運進入一個新階段,“自成祖遷燕,道里遼遠,法凡三變。初支運,次兌運、支運相參,至支運悉變為長運而定制”。明成祖開通運河段會通河后,依托京杭大運河,將之前的海運改為漕運,在其沿線設置糧倉,各地將漕糧送至就近糧倉,由軍官、士兵分段運送,每年四次。明朝亦極重視中國大運河漕運的組織與管理,遂成定制,此時漕運支撐著明王朝財政收入之半壁江山。清朝中國大運河漕運成為南北通航之干線,京城王室、官員、官兵之糧食供給,全都依靠漕運,漕運量猛增,運河沿岸城鎮逐漸成為漕運要津。因此清對漕運之制度制定得更為細致。清朝末年,由于中國大運河河道淤積,漕運長期積累的弊端使其陷入危機,漕運官員貪腐嚴重,軍事廢弛以及社會矛盾的激化、社會動蕩之問題,導致漕運制度的衰落至被廢除。康有為有言:“漕運之制,為中國大制。”尤其是封建社會后期,因為社會經濟之變化,漕運發揮著多種社會功用,刺激著商業經濟的發展。漕運的興衰決定著一些城鎮的興衰。德州因糧而建,因運糧而興,漕運刺激著德州之經濟繁榮,亦因漕運的衰敗而衰落。可以說,幾千年的漕運就是大一統中國政治之基石。東漢李尤《舟楫銘》曾云:“舟楫之利,譬若輿馬,載重歷遠,以濟天下。”漕運在歷代王朝的發展中均有突出之作用。“漕運制度伴隨著大運河發展而日趨完善,并成為歷代封建帝國的根本。”[10]運河作為南糧北運的脈絡,是維護中央集權、國家統一的戰略線。漕運與古代封建社會同步,又與社會經濟變遷相呼應。由于中國大運河的開鑿,交通便利,漕運促進運河沿線城鎮的經濟交往,成為其商業繁榮的重要因素,從而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漕運文化。漕運作為中國大運河的概念內涵,具有活態多樣性,不僅顯現了古時中國水利的科技水平,更體現了民間智慧和人民的生活藝術性,是獨具一格的精神、物質財富。
(三)中國大運河內涵之文化
中國大運河之文化,是其在開鑿和通航過程中,長期積淀而形成的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的結合,是其流經城鎮居民所創造、遵循、延續之文化,是以時間、空間、功能輻射層面為演變特征之文化系統,是跨區域、綜合性之文化體系。中國大運河文化是一個寬泛的范疇,標準不同,其文化類型亦不同。其有著明顯的運河特征:開放性、溝通性、區域性、互動性等。中國大運河將黃河和長江連接起來,架設一條溝通南北的通道,利用其交往融合,體現了其包容性、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特點。對中國大運河文化之理解,可以從兩方面入手:其一,以大化小,將其拆分分析。強調中國大運河文化的多學科組合,即拼盤文化,如其涉及的各門類文化:建筑文化、飲食文化、曲藝文化、商貿文化、觀念信仰、民俗風情等。其二,化零為整,將其整合分析。中國大運河歷史文化是一個整體,其文化并不是現象或想象,而是以人為本,即人之行為及全部影響人之行為的因素。由此,中國大運河文化是其流經區域人所創造的文化及人與文化互動之過程,經過長時間的遵循并得到延續的總和。對中國大運河文化意義之追尋,可以從文化遺產、知識體系、民族精神等層面的傳承入手,具體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中國大運河是文化的載體。中國大運河是一種文化符號,承載了物質、社會、精神等層面的內容。這里的載體主要指中國大運河河道及其建筑物、水利工程等,也就是中國大運河在人們觀念中的固有印象、具體的“事物”形象。中國大運河是文化的載體,意為其對文化的催生、傳播、聚合等作用的發揮。中國大運河的開放性、流動性、包容性、互動性,加強了區域間文化的融合性,使各類文化相互吸收、融合、涵化,在相互交流、互動中各自拆分又合并,發生內容與形式的變化,又在共性的基礎上形成新文化。中國大運河載體功能體現在不同文化交流、碰撞、融合的過程,在此,中國大運河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地域概念,而是中國大運河及其政治、經濟、觀念、思想等相互作用的統一體。
其次,中國大運河是文化聯系的紐帶。中國大運河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區域性,連接了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河南、安徽、江蘇、浙江等省和直轄市,串聯了燕趙、齊魯、中原、江南等文化帶,將南北相接,形成經濟、文化交流、傳播的紐帶。運河沿岸的城鎮都受到運河文化的滋補,帶著運河人獨有的氣質及文化內涵,回報著運河之哺育,又一代代傳承著運河文化。中國大運河與其它自然河流一起,構建了文化聯系的格局。
最后,中國大運河文化是一種生活方式。中國大運河的開鑿、通航所形成的環境和條件,成為一個體系,使漕運組織、商人、河工、沿岸居民形成了獨特的生存和生活方式,由此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風俗觀念。生活方式不會因為中國大運河的衰落而消逝,亦不會在時代潮流中一成不變。中國大運河具有最真實、生動、活力的生活場景和生活情態,并在人們日常生活的勞作、娛樂、禮儀、交往等方面得到傳承。
*基金項目:江蘇省研究生實踐創新計劃項目“江蘇段大運河文化建設的問題與對策研究”(項目編號:SJCX18_0695),江蘇省社科基金專項“古代沿江蘇大運河傳播的工匠文化研究”(2017YBZXM033)研究成果之一。
參考文獻
[1]徐歐露.打造大運河文化帶金名片[J].瞭望周刊,2017:(36).
[2]李里峰.概念史研究在中國:回顧與展望[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05):92-100.
[3]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中國大運河申報世界遺產文本.2013年.
[4]中國古代那些學者之水利類.http://www.sohu.com/a/ 145909183_99890854.
[5]姜師立.運河學的概念、內涵、研究方法及路徑[J].中國名城,2018(07).
[6]王永波.運河文化的運動規律及其啟示[J].東南文化,2002(03).
[7]王健.近代大運河的軍事國防價值——大運河衰敗對兩次鴉片戰爭、甲午戰爭的影響[J].中原文化研究,2015,3(04):85-90.
[8]中國建筑史編寫組.中國建筑史.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1990.
[9]何為剛.略論京杭大運河的過去和未來[J].濟寧師專學報,1997(03):95-99.
[10]莫修權.漕運文化與中國城市發展[J].華中建筑,2003(01):7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