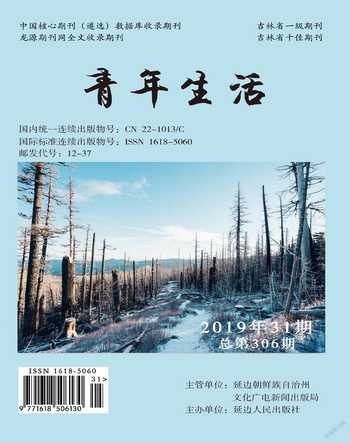時代變局中的通經致用
王碩
摘要:乾嘉學派的興起促進了“通經”與“致用”的第一次疏離,且在此期間“通經”的重要性得到凸顯,相比之下“致用”一途卻漸受阻塞。然隨著社會危機的日漸深重,再加上統治者政策的調整,“通經”與“致用”再一次得到并重。鴉片戰爭以后,一方面越來越多來自西方強權勢力的壓迫促使時人將眼光聚焦于“致用”一途,另一方面,西學的日漸涌入亦為早已捉襟見肘的“通經”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在這一時期,經世與致用已成為時人的根本目的,在這種目標的指引下,“通經”緩慢而艱難的發生著根本性質的轉變。
關鍵詞:通經;致用;西力東漸
顧名思義,“通經致用”便是指通曉經術以求致用。這里的“經”主要是指以“六經”為代表的儒家經典,而“用”則是指通過經術來完善自身,經濟天下。“通經致用”正式成為一種思潮是在清初,之所以形成此種思潮的原因是陽明心學極盛而弊,學者們常常流于玄學、空談心性,自宋以來形成的理學體系已經產生很大的弊端,不再能作為維系整個社會信仰的核心。在這種情況下,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人紛紛著書立說,以求能糾王學之流弊。他們大肆倡導兩漢經學,鼓勵學者們擺脫理學束縛,直接儒家原典。他們還將“通經”與“致用”緊密結合,提倡從儒家經典中尋求治理時務的方法。然而好景不長,由于清政府對言論的嚴格把控以及文字獄政策的實施,學人們于“致用”一途漸受阻塞,故把目光集中到“通經”上來,漸漸形成了以文字訓詁為主的考據學派。與這一過程相伴而來的便是“通經”重要性的凸顯及“通經”與“致用”的分離。《左傳》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由此可見,從立德到立功再到立言乃是儒家自古以來就有的價值體系序列。可是到乾嘉學派,此種價值序列發生了相當顯著的變化。戴震的言論就已初露端倪,他說:“六經之文,邃深而博大,學焉者各有所至,或履之為德行,或抒之為文章,或措之成豐功偉績。”“文章”既在“豐功偉績”之前,換句話說也就是立言高于立功。王引之亦言:“吾治經,于大道不敢承,獨好小學。”王鳴盛更是直接指出:“貪鄙不過一時之嘲,學問乃千古之業。”“立言”在以往的儒家學者眼中常常是因不得已退而求其次的選擇,且其根本目的仍在于立功與德性。可是在乾嘉學者的眼中,立言儼然已成為最重要的價值觀念,學者們僅為通經而通經,為學問而學問,學術本身便是他們的最終目的。
不過在這種變化背后亦潛藏著一股再變的潛流。以學術層面而言,乾嘉學派“崇古尊漢”傾向的背后其實暗含了一種越古越好的邏輯,按照這種邏輯來推演的結果便是:融入佛道元素而任意闡釋經義的宋學需要懷疑,疑似劉歆為王莽篡權而提倡的古文經學也未必值得信任,相對的,經秦遺儒口耳相傳的今文經學乃至先秦諸子之學當更有提倡的價值。正是受此種邏輯推斷的影響,常州學派應運而生,并且相繼涌現了莊存與、劉逢祿和宋翔鳳等杰出的學者。他們共尊《公羊》,拉開了清代今文經學的序幕。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下,后來的龔自珍、魏源甚至到康有為在批判社會黑暗,呼吁統治者改革時才有豐富的思想資源。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康乾時期,中國社會呈現出一幅相對穩定繁榮的狀態,但是盛世之下亦潛藏著危機,各種社會矛盾日漸趨向于激化。乾嘉更迭之際爆發了規模盛大的白蓮教起義,成為清朝由盛轉衰的重要節點。此后,土地兼并、賦稅加派愈演愈烈;吏、軍、河、漕、鹽、幣諸大政弊竇叢生。中國在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諸多方面都開始江河日下,嚴重的社會問題急需解決;與此形成對比的是,西方國家相繼確立資本主義制度,大力發展工業。為搶占原料產地和新市場,他們更是把眼光瞄向中國,并為打開中國大門做出了種種嘗試,最后,英國挑起鴉片戰爭,迫使清政府訂立城下之盟。面對如此嚴峻的社會現實,國內的有識之士紛紛從故紙堆中脫離出來,加入了今文學派的大營,并利用“微言大義”抨擊時弊,倡言經世致用。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通經與致用都得到極大的重視,并且再一次形成緊密的聯合。龔自珍當屬其中最具特色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借用今文經學中的變易思想,在揭露批判時弊的同時倡言社會改革,并且明確指出:“一祖之法無不敝,千夫之議無不靡,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孰若自改革?”即使是當時的最高統治者道光也曾指出:“士不通經,不足致用,經之學,不在尋章摘句也,要為其用者。”由此可見,通經致用在嘉道時期已經再一次成為主流思潮,并且這種思潮的背后還有統治階級力量的支撐。然通經致用思潮首要便為“通經”,主要是從“古已有之”的經驗里面去汲取知識應對社會現實。嘉道年間雖因社會危機的加深二者再次緊密聯合,然也正因為這“千古未有之變局”,“通經”漸難以在變革的時代發揮“致用”的作用,故而“通經”與“致用”開始發生第二次疏離,“致用”的重要性也日益凸顯。鴉片戰爭以后,經世致用更是逐漸成為時人的根本目標。然經世之世既已改變,經世之學自然也有變的必要,在此內在動力的支撐之下,再加上西學的大量傳入,傳統的經世之學開始向所謂的新學轉變。
自中國邁入近代社會以來,其主流思想的發展演變便一直受到內外多重因素的影響。就內部而言,我們不能否認儒家傳統的“入世”精神為時人們尋求改革,挽救國家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內在動力。然而吊詭的是作為中國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的通經致用雖然具有強烈的經世濟民精神,但是其本身所固有的學術文化結構,卻也是十分穩定與強固的。這種結構是中國傳統社會生活長期演變下的產物,其所包含的學術、道統、以及六部分類等內容,
參考文獻:
左丘明撰;蔣冀騁標點:《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岳麓書社,1988年12月
戴震著;趙玉新點校:《戴震文集·鳳儀書院碑》,中華書局,1980年12月
龔自珍:《龔定庵全集類編·工部尚書高郵王文簡公墓志銘》,中國書店,1991年6月
昭梿:《嘯亭雜錄》,中華書局,1980年12月
龔自珍:《龔自珍全集·乙丙之際箸議第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2月
《宣宗實錄》,中華書局,1986年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