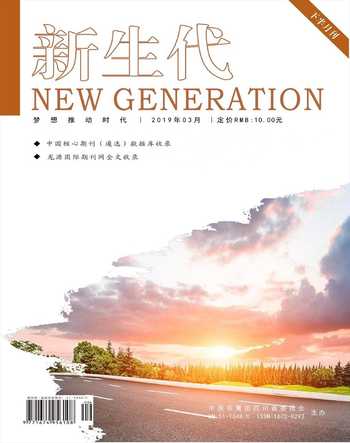抗戰時期翦伯贊的中華民族觀與民族史敘述
【摘要】:抗日戰爭時期,顧頡剛的文章《中華民族是一個》引起了一場關于“中華民族”概念的大討論,在討論中顧頡剛的弟子白壽彝還表達了重新敘述中國民族史的期望。翦伯贊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及民族觀參與了這場論戰,提出了有別于顧頡剛等人的基于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原則上的“中華民族”概念,同時正視歷史上民族之間的戰爭,為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和中國民族史的深入研究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關鍵詞】:翦伯贊 中華民族 民族史
一、關于民族和中華民族概念的討論
“中華民族”這一概念與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出現密切相關,可以說它是近代民族主義誕生的“標志”,同時也是近代民族認同的核心環節。“中華民族”這一概念的由梁啟超首先提出,至民國建立后廣為流傳。到20世紀30到40年代,受到抗日戰爭的影響,關于“中華民族”的討論再次興起。
這其中影響最大的是1939年2月顧頡剛在《益世報》的《邊疆周刊》上發表的《中華民族是一個》,該文開明宗義就說:“凡是中國人都是中華民族”,中華民族不能再分出什么民族,緊接著從歷史中尋求依據:“就因為我們從來沒有種族的成見,只要能在中國疆域之內受一個政府的統治,就會彼此承認都是同等一體的人民。”然后從血緣上和文化上說明:“而且各種文化也自有其相同的質素,不是絕對抵觸的。從這種種例子看來,中華民族是渾然一體,既不能用種族來分,也不必用文化來分,都有極顯著的事實足以證明。”最后把“中華民族是一個”的觀念與抗戰建國緊密結合起來:“我現在敢對他們說:我們所以要抗戰的是要建國,而團結國內各種各族,使他們貫徹‘中華民族是一個’的意識,實為建國的先決條件。”
《中華民族是一個》在刊出后,各地報紙紛紛轉載,學術界的反響十分強烈,《益世報》收到了不少相關討論文章,例如白壽彝的來函(后附顧頡剛的按語)、馬毅的《堅強“中華民族是一個”的信念》等。這些文章大多贊同顧頡剛的觀點,,大家基本上認為顧頡剛這一觀點對于加強民族團結、共御外侮是有著積極意義的,特別是從當時的抗戰形勢著眼。
1940年4月,從長沙轉移到重慶后不久,作為一名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從事統一戰線、理論宣傳和史學研究工作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翦伯贊也參與了這場爭論,他在《中蘇文化》雜志上發表了《論中華民族與民族主義——讀顧頡剛續論“中華民族是一個”以后》。當這場論辯在昆明《益世報》上不斷展開時,翦伯贊正在千里之外的長沙主持《中蘇》半月刊雜志,因此,他很有可能并沒有看到爭論雙方的所有文章。當然,也許是因為1939年的討論高潮已經過去,顧頡剛對于翦伯贊此文似乎并沒有做出回應。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翦伯贊這篇名為《論中華民族與民族主義》【1】的文章,乃是少數民族(維吾爾族)出身的他關于當時中國學術界非常關心的“民族”、“中華民族民族”,以及民族觀與歷史學的關系等問題的批判性思考。
翦伯贊認為顧頡剛提出的問題非常重要,但他將“中華民族是一個”作為對中華民族認識的出發點和結論是不正確的。顧頡剛根據當時歐美學界流行的對“民族”界定為“一個有團結情緒的”“能同安樂、共患難的”人群的定義,認為民族“是由政治現象(國家的組織強鄰的壓迫)所造成的心理現象(團結的情緒),他和語言,文化及體質固然可以發生關系……但民族的基礎,決不建筑在言語文化及體質上,因為這些東西都是順了自然演進的,而民族則是憑了人們的意識而造成的”,因此語言、文化和體質都不是構成民族的條件,構成民族主要條件的只是一個“團結的情緒”。翦伯贊指出,在民族問題的認識上,顧頡剛出現了兩個錯誤:“把‘民族’與‘民族意識’混同起來,并且把‘民族意識’當作‘民族’”;把民族與國家混同起來,認為民族與國家是同時發生的。
從對“民族”的理解上,翦伯贊認為顧頡剛有幾個可能造成有害影響的錯誤:
首先,翦伯贊依據斯大林關于民族的定義,認為“民族”不是一種純粹的觀念性的概念,與經濟和文化密切相關:“民族是歷史上結合而成的一個有共同言語,有共同領土,有共同經濟聯系,以及有表現于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狀態的固定集團。”顧頡剛將民族與民族意識混淆不清,認為構成民族的條件不是“語言、文化、體質”,而是“精神的”“主觀的”“團結的情緒”,這樣一來民族變成了主觀的意識和抽象的概念,并沒有客觀的存在和物質的基礎作為支撐。顧頡剛認為民族只是一種“團結的情緒”,且與言語、文化、經濟利益等無關,是不正確的,因為想把中國國內一切不同語言、文化與體質的少數民族,消解于一個抽象的“團結的情緒”的概念之下,而觀念地造成一個中華民族,但這樣的中華民族也只是一種觀念上的“中華民族”。
其次,顧頡剛認為,在秦以前中華民族就已形成,秦統一后,朝代雖有變更,種族雖有進退,“但‘一個民族’總是一個民族。任憑外面的壓力有多大,總不能把他破裂,新加入的分子,無論怎樣多,也總能容受”。翦伯贊批評說:按照顧頡剛的意見,必須有統一的國家才能形成統一的民族,然而他另一方面又說在秦統一前,中國早已有統一的民族,這是自相矛盾。
再次,在翦伯贊看來,顧頡剛混淆了民族融合與民族消亡。顧頡剛認為中國歷史上只有外族加入漢族,而沒有漢族加入外族,因此漢族“如雪球一樣,越滾越大,遂得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大民族”。翦伯贊認為,民族的融合不是片面的而是相互的。不是所有的外族與漢族接觸后便消滅,或同化于漢族。在融合過程中,既有外族加入漢族的,也有漢族加入外族的。即便漢族文化在中國乃至在東方都在領導著文化,但只能給予各民族以文化影響。翦伯贊還批評說顧頡剛對“種族”和“民族”概念的理解存在誤解:“民族是種族的變質”,“從種族到民族不是一種生物學的原理,而是社會學的原理”。
最后,翦伯贊認為解決民族問題的最好方法是民族平等:“主要的是要承認各民族之生存乃至文化的平等關系,以兄弟的友誼相互結合,則‘自殺的慘劇’自然可以消滅,真是的民族大團結也才能實現。【2】”
從翦伯贊的這種歷史觀和民族觀來看,顧頡剛等人所謂的中華民族自秦朝就已經初步形成,之后逐漸吸收其他“少數民族”成分而不斷擴大,通過書寫這樣的“中華民族史”來證明“中華民族是一個”,不但在實踐上不具可行性,而且在理論基礎上也不“科學”。因為這樣的民族史,不僅脫離了具體的歷史階段,還不自覺地反映出“大漢族主義”,反而會有害于現實斗爭。
二、歷史上民族戰爭的敘述問題
在1939年“中華民族是一個”的大討論中,顧頡剛的學生白壽彝訴說了他親身經歷過的“歷史敘述”:“聽到某民政廳長公開對民眾演講,說過去我們是怎樣亡國于蒙古,亡國于滿洲……到了另外一個省區,刺目的事情更多了。在這個地方,‘八月十五殺韃子’成了正式的宣傳材料。這算什么話!這是作的抗戰工作?還是作的分化工作?……現在的國賊是叫作什么。他們是同行全國的被稱作‘漢’奸啊!”白壽彝覺得“非常的氣憤”,認為這是“心理上的不健全,總需加緊掃除!”。他希望顧頡剛用“中華民族是一個”的觀點寫一本新的中國史。顧頡剛認為寫出這樣一部書“在短時確是做不了”,如果能夠搜集到更多蒙文、藏文等非漢文史料,“等到了有這樣一天,一部偉大的書就會出現。”【3】
1940至1949年,在翦伯贊的中國史研究中,有一系列文章都涉及到民族關系或民族史,而且所敘述的都是民族矛盾尖銳或民族之間戰爭的時期:《西晉末年的“流人”及其“叛亂”》,《南宋初年黃河南北的義軍考》,《元代中原人民反對韃靼統治者的斗爭》,《遼沈淪陷以后的明史——紀念“九一八”九周年》,《論南明第二個政府的斗爭》,《桃花扇底看南朝》,《南明史上的弘光時代》等等。
在這些文章中,翦伯贊的歷史敘述仿佛就是白壽彝所批判的“典型對象”。比如《西晉末年的“流人”及其“叛亂”》開頭便是“從西晉末起,終東晉之世,百余年間,這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邊疆民族大侵入的時代,也是一個中原漢族大移動的時代。”【4】通篇文章還有“及至西北諸族侵入,種族仇殺,尤為駭人”“則又大半死于諸族之屠殺”等類似的敘述;在《兩宋時代漢奸及傀儡組織》開頭是:“中國歷史上最慘痛最恥辱的一幕,是宋代的歷史……所以這一段歷史,對于目前正在抗戰中的中國人民,是一個最好的教育材料。”【5】,把劉豫、張邦昌稱為“公開賣國之傀儡漢奸”,而“漢奸中最有反動作用的還是秦檜”,把汪精衛的叛國與秦檜的投降相提并論,最后總結為“深信,不但兩宋的悲劇不會重演,而且兩宋的慘痛歷史,將成為我們今日爭取民族解放徹底勝利的啟示。”而在《元代中原人民反對韃靼統治者的斗爭》中,光看小標題就可見一斑:“韃靼統治者對漢族人民的的種族壓迫”“韃靼統治者對漢族人民的經濟掠奪”“彌漫黃河南北的‘彌勒、白蓮教匪’”“相挺而起的‘江南群盜’”。
同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范文瀾在《中國通史簡編》中也表現出與翦伯贊相似的兩種傾向:第一,將北方民族對中原的武力占領和統治稱為“侵入”“侵略”行為,并譴責這些行為給中原地區人民造成的災難。范文瀾將兩晉之際看做是“塞外野蠻民族,大量流入黃河流域,落后低級的生活,殘暴嗜殺的惡性,破壞華族二三千年發育滋長的經濟和文化”的“外族大侵入”時代【6】。同樣也將金、元、清等政權看作是由落后民族入侵中原后建立起的政權。第二,歌頌反抗外族“侵略”和壓迫的民族英雄,譴責投降妥協,鞭撻漢奸。在北宋部分的結語中,他認為北宋的外交“完全采取屈辱忍恥、納幣求和的政策”,批評北宋統治者為了保持政權,“對外恥辱并不以為可恥”【7】。《中國通史簡編》在描述反侵略歷史時不吝筆墨,用大量的篇幅描寫了民間熟知的岳飛抗金,同樣用了大量筆墨(8個小節)描述了讀者未必耳熟能詳的清初各地人民反抗清軍的斗爭。
關于中國歷史上民族矛盾和民族之間的戰爭,以及中國歷史上的民族英雄,新中國建立以后進行過討論,學界有著不同意見。現在的主流觀點是,不能把古代中國境內不同民族之間的戰爭等同于近代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顯然,翦伯贊和范文瀾的看法并不完全如此。他們雖然沒有直接將北方民族政權和中原漢族政權之間的戰爭,與近代外國對華侵略戰爭相提并論,但卻使用“入侵”“侵略”等語詞,明確定義了這些戰爭的性質。
大多數學者認為翦伯贊和范文瀾的這一系列敘述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與抗日戰爭的特定歷史背景有關。部分內容具有明顯的“影射史學”色彩,是為了宣傳抗日救國,同時也比較隱蔽地宣傳了中共的敵后戰場,比如有相當的篇幅對“淪陷區人民的斗爭”“人民自發的斗爭”“義軍”“民兵”等進行了較為細致的敘述,對他們進行了高度的贊揚。當然,這些文章一方面有著強烈的“影射”和致用性,另一方面也不能簡單地認為此類歷史敘述是為了宣傳抗戰和中共,還是要從對于歷史上與現實中的“中華民族”概念有著不同的理解。
白壽彝之所以對此類歷史敘述“非常的氣憤”,是因為他認為這會傷害到除漢族外其他各族人民的感情,在心理上造成隔閡,帝國主義者很可能會借此挑撥離間,最后會對中華民族的“一體性”造成重大損害,進而威脅到抗戰的前途。從另一方面來看,當時正是國民黨頑固派掀起反共浪潮,對日妥協之聲甚囂塵上,我們可以對翦伯贊和范文瀾的這些表述,以及關于歷史上民族戰爭的判斷,有更多的理解。
除了現實斗爭的需要,翦伯贊也不認為此類歷史敘述會有“傷害感情”“破壞各族之間的關系”之類的后果,因為一方面正如前文已經論述過的,他認為民族意識并非憑空產生,不只是一種“團結的情緒”,而是有一定物質基礎的,民族內部團結的基礎是共同的經濟利益,解決民族問題的最好方法是民族平等;另一方面,翦伯贊并不認為掩飾和隱諱歷史上的民族沖突是一種正確有效的方法,這種觀點在新中國成立后發表的《關于處理中國歷史上的民族關系問題》、《關于歷史人物評論中的若干問題》等文章中有更加充分的表達。
【參考文獻】
【1】翦伯贊:《翦伯贊全集》第5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128頁。
【2】翦伯贊:《翦伯贊全集》第5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128-139頁。
【3】白壽彝:《來函》,昆明:《益世報》副刊《邊疆周刊》第16期,1939年4月3日.
【4】翦伯贊:《西晉末年的“流人”及其“叛亂”》,《翦伯贊全集》第3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89頁。
【5】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范文瀾全集》第7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頁。
【6】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范文瀾全集》第7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頁。
【7】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范文瀾全集》第8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45頁。
作者簡介:王棟(1994.03-),男,漢族,籍貫山東淄博,云南民族大學在讀研究生(應屆畢業生),方向中國近現代學術史,65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