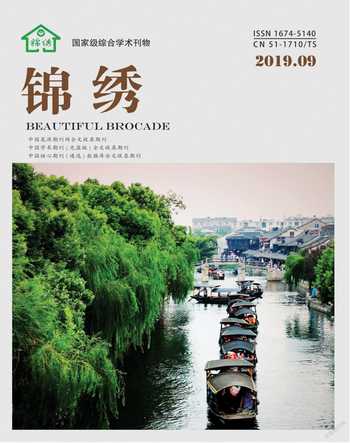《世說新語》中的文學故事觀照
張純
摘 要:魏晉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段“文藝復興”,尤其是文學藝術的繁榮發展,在歷史的長河中熠熠生輝。《世說新語》作為一部記載了這一時期文人士大夫言談舉止、風流軼事的名著,生動地反映了這一時代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方面的具體風貌,自然對也會文學領域進行描寫與記錄。本文就主要對《世說新語》中的文學故事分別進行分析與研究:文學故事絕大部分集中在了《文學》一篇當中,于是便將此篇劃分為了“學”與“文”兩類故事,第一類主要是一些有關具體學術的故事,第二類是一些有關具體詩文創作與鑒賞的故事。本文旨在對《世說新語》中文學故事的具體分析以觀照魏晉時代中的文學文化現象并擷取其中精華以獲啟發。
關鍵詞:《世說新語》;魏晉時代;文學故事
魏晉六朝時代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特殊的時代,它承受著社會動亂、國家分裂的苦痛,卻同時在思想靈魂與文學文化方面容光煥發。要想一睹魏晉時代文學卓越發展的盛況,南朝劉義慶編纂的《世說新語》正是開啟了一個恰當的窗口。《世說新語》中的文學故事主要集中于《文學》一篇。清代學者李慈銘將《文學》一篇的劃分進行了較為明確的說明:“案臨川之意分,此(按:謂第66條)以上者為學,此下為文。然其所謂學者,清言釋、老而已。” ①意即根據更深的內在聯系,《文學》可以被劃分為兩部分:第1至65條為“學”的部分,講述關于注解經文的軼事;第66至104條為“文”的部分,記載了有關詩文創作的軼事。
一、文學之“學”,學術之“學”
《文學》篇中的前半部分是“學”的部分,是有關具體學術的內容,主要涉及了玄學、經學以及佛學。其中玄學占比重較大,大多數故事都會涉及玄理。魏晉時期玄學方興未艾,在漢末封建倫理綱常遭到極大破壞的時代背景下,士人們重新審視了先秦諸子百家,在又一次的“百家爭鳴”中,出現了對《莊子》《老子》和《周易》的研究熱潮,道家被引入儒學,由此而開啟了貫穿整個魏晉六朝時期的一代玄風。《文學》篇中“學”的部分就有許多對這一社會思潮的鮮活記錄。比如有描寫眾名賢集會談玄或名士互相辯論的故事:“何宴為吏部尚書郎”一條講述了去何宴家清談的賓客常常座無虛席,而年紀輕輕卻小有名氣的王弼講玄理頭頭是道、在座無人能及的故事;“殷中軍為庾公長史”條,殷中軍等眾多名士在王導家集會大談玄理直至“三更”,那清談之盛況在我們面前呈現;“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條記載了孫安國與殷浩之辯論過于投入以至于飯菜來回熱了多回還未被沉迷于清談的主賓吃掉……
對于從西漢開始就占統治地位的經學在魏晉時期已經走向了衰落,但沒有衰亡,《文學》篇中仍然可以找到它的身影。這一時期的經學以大儒鄭玄為主角,因為他以古學為宗,兼采今學,融通今古而統一了經學,從《文學》前三則先列鄭玄之事跡可見其地位之高。第一則記載了鄭玄才智出眾、學識淵博,馬融對他的學成歸去有“禮樂皆東”之嘆,可見鄭玄在經學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第二則講述了鄭玄因服虔所注《左傳》之意大致與自己相通而將自己的注解送給服虔助其完成了《服氏注》的故事,凸顯了鄭玄一心為了經學發展的無私奉獻的大家精神;第三則記載了鄭玄家連婢女都熟讀經書,能夠隨口引經據典,可見這位儒學大家對身邊人的良好影響。
除了我國本土的玄學與儒學,外來的佛教也要一湊熱鬧,名士們用佛學哲理補充和豐富了玄學清談的內容。比如“殷中軍見佛經”、“殷中軍讀《小品》”、“殷中軍被廢東陽”以及“殷中軍被廢”這四則都講述了殷浩潛心研習佛經、從中發掘玄理的故事;“有北來道好才理”一則記載了支道林與竺法深均精研佛學經典《小品》;“三乘佛家滯意”講述了支道林為對佛經充滿求知欲望的人們講解佛教教義中難解的“三乘”部分……
二、文學之“文”,文章之“文”
《文學》篇中“文”的部分記述的是有關具體文學領域的一些故事,比如詩文的創作與鑒賞故事。袁行霈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曾提到:“所謂文學的自覺有三個標志:第一,文學從廣義的學術中分化出來,成為獨立的一個門類。第二,對文學的各種體裁有了比較細致的區分,更重要的是對各種體裁的體制和風格特征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第三,對文學的審美特性有了自覺的追求。”② 那么由此看來,魏晉南北朝文學近乎達到了自覺的程度,因為《文學》篇中“文”的部分就已經將這三個標志閃亮地展現了出來。第一,漢代時所謂的文學指的是學術,特別是儒學,而到了南北朝時期,“文學”與“文章”常常混用,“文章”之意已經成功打入了“文學”意義的堡壘,這時的文學已不再局限于學術,它包含著某些學術的內容但不再完全是學術,而是具有了新的獨立于學術的地位,所以《世說新語·文學》中的“文學”既包含了“學術之學”又包含了“文章之文”。第二,《文學》篇中“文”的部分故事中所涉及到的文章體裁高達九類之多,如此細致、精到的體裁分類,恐怕是“前無古人”的高度:“賦”如“庾子松作《意賦》”;“詩”如““夏侯湛作《周詩》”;“文”如“司空鄭沖馳遣信就阮籍求文”;“表”如“將讓河南醫,請陸岳為表”;“檄”如“令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露布文為檄文一種)”;“頌”如“劉伶著《酒德頌》”;“贊”如“羊孚作《雪贊》”;“論”如“王敬作《賢人論》”;“誄”如“孫興公作《庾公誄》”等。這些文學故事明確記載著各類文體,說明已經對各類文體有了較細致的認識與明確的區分,而不同文體的風格特征也可以在一篇篇精煉的故事中一窺究竟。第三,對于美的追求是從古至今人們永恒的追求,而對文學審美特性的追求則在這部分文學故事中體現得尤為明顯。于民在《中國美學思想史》中說:“在晉代不論與人與文,可以說無清不妙、無清不工、無清不新和無清不美了。不同歷史時期的巨大變化,也以不同的審美崇尚浮現出來。” ③以“清”為美的審美崇尚在《文章》篇“文”的部分展現了出來:孫興公評“潘文淺而凈,陸文深而蕪”,潘岳的文章雖然淺近但潔凈,陸機的文章雖然深刻但蕪雜,這看似并列平等,實際上感情傾向十分明顯,文章即使深刻又怎樣,一旦蕪雜那還不如淺近卻潔凈的文章;還有羊孚所作《雪贊》,將白雪的清氣灑滿全詩,讀來令人神清氣爽,難怪恒胤將此詩寫在扇子上,那清氣似乎能夠消退暑熱、清涼一夏。
《世說新語·文學》篇中“文”與“學”的部分雖然被明確地劃分為了兩部分,但二者絕非互不相關,也非相互排斥,而是統一于“文學”大主題之中的兩種有機展示,帶給了我們無盡的遐想與啟示。
參考文獻
[1]張晨.《世說新語·文學》之“文學”辨析[J].東南大學學報,2004(4)
[2]袁行霈.中國文學史(第二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于民.中國美學思想史[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