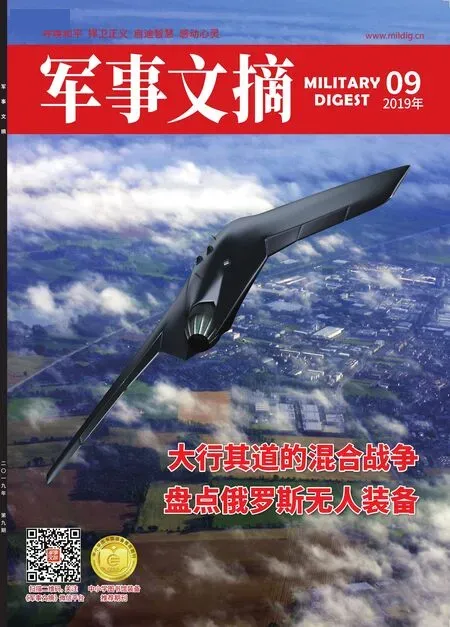無意義的流血:1915年伊松佐河戰役
鴻 漸
眾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眾多戰役都以驚人而無謂的人員損耗為普遍特征,發生在歐洲西線戰場上的凡爾登會戰和索姆河會戰都是如此,而在歐洲南線戰場上亦曾有過類似的無謂交戰,而且其殘酷和無意義的程度較西線諸役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就是發生在意大利和奧匈帝國之間多達12次的伊松佐河戰役。

1915年一支奧地利步兵部隊的著色照片
必須采取行動
一戰爆發后,意大利一度猶疑觀望,到1915年5月終于決心加入協約國陣營參戰,不過仍有所保留的只對奧匈帝國宣戰,希望集中力量從后者手中奪回的里雅斯特和蒂羅爾這兩處“失地”。由此便在伊松佐河畔、多洛米蒂山脈和的里雅斯特附近的山地之間發生了一系列交戰。
志在搶攻的意軍在當年六七月間連續發起第一次和第二次伊松佐河戰役,結果損兵折將而毫無進展,伊松佐河畔的兩軍由是陷入了僵持狀態。在吃了兩次苦頭之后,意大利陸軍總參謀長路易基·卡多納將軍本不急于發動新的進攻。他已經意識到意大利的資源和這個國家的雄心壯志不成正比,就眼前的形勢而言,他至少需要足夠數量的重炮和炮彈。而據卡多納估計,就算全意大利的武器制造商集中一年時間來生產,恐怕也填補不了前線的火炮缺口。
可是卡多納扛不住來自羅馬政府的壓力,政要們高調宣稱在年底前必須取得一場“巨大的勝利”。就算夢寐以求的城市的里雅斯特不能入手,那么戈里齊亞總可以吧?戈里齊亞是亞得里亞海岸的一座美麗城市,也屬于意大利人眼中的“失地”。
更大的壓力來自同一陣營中的盟友。保加利亞于1915年9月宣布加入同盟國,接著塞爾維亞就被奧匈帝國和保加利亞兩面夾擊,生存岌岌可危。與此同時,英法軍隊在法國的攻勢亦陷入困頓,他們強烈要求意大利采取行動。這樣一來,卡多納肩上的進攻責任就變得不可推卸了。
數月以來,意軍不斷向伊松佐河地區調集火炮和炮彈,參謀人員也擬制了進攻計劃。總體來說,雖然的里雅斯特仍然可望不可及,但是戈里齊亞已被認為是可以攻取的目標。誠然,戈里齊亞并沒有什么戰略價值,不過它離意大利前線只有幾千米遠,看起來進攻難度不會太大。
按照計劃,由弗魯戈尼將軍指揮的第2集團軍進攻戈里齊亞以北的托爾曼和普拉瓦,以及附近的波德戈拉和薩博蒂諾山地;而奧斯塔公爵的第3集團軍則攻擊戈里齊亞以南的圣米克爾山,以兩面包抄之勢拿下戈里齊亞。
經過對前兩次戰役的總結,意軍總參謀部確定了新的進攻戰術,冠其名曰“有條不紊的前進”。具體來說:炮火準備既要猛烈到足以摧毀敵人前沿陣地的程度,可也不能持續太長時間,以免敵軍增援部隊有時間進抵一線地區。為了減輕主攻方向上的阻力,應該在多個方向上同時發動牽制性進攻。步兵進攻時,炮火要向前延伸,一來打擊敵人后方,二來阻止其增援企圖。
鑒于奧軍在其山間陣地上密布鐵絲網,參謀們還設計出了應對方案,那就是在進攻前一天的晚上,派出“破壞分隊”在鐵絲網上打開缺口。這些分隊由4到5人組成,每人配備一把鋼絲剪、數枚手榴彈和一具爆破筒。意軍的爆破筒參考英軍的同類裝備,筒身長約2米,點火索像蠟燭芯一樣向前探出,據稱在引爆后可以在鐵絲網中開出直徑3米到5米的大洞。

奧軍山間陣地一景
30次沖鋒毫無成果
10月18日,一個寒冷的秋日,1300多門意大利大炮在50千米長的戰線上猛烈開火,第3次伊松佐河戰役打響了。炮擊的聲勢遠遠超過了前兩次戰役,不過由于重炮數量不足,意軍炮兵主力仍是75毫米野炮,這種火炮在壓制作戰中的威力是相對較弱的。
盡管卡多納曾主張縮短炮擊時間,但炮擊還是持續了好幾天,意大利步兵直到10月21日才離開他們的戰壕向前進發。意大利人滿心期待著重大勝利,可是等著他們的卻是苦難。在意大利逃兵的“幫助”下,奧地利人已經對意軍的計劃了如指掌,他們加固了陣地,補充了機槍,等著敵人上前。
奧軍擁有靈活的戰術。白天,士兵們都在戰壕里伏低身子,留下狙擊手向不知如何隱蔽自己的意大利人開槍,炮兵則退到意軍的炮火范圍之外。到了晚上,奧軍士兵則不斷開火,他們向意軍陣地上空打出探照燈,引導已經向前移動位置的炮兵猛烈開炮。
奧地利軍隊在伊松佐河沿線的山區布置有3道防線,其相對獨立而又彼此呼應的格局簡直是教科書式的。這些防御系統的深度足以吸收敵人取得局部突破時的沖擊力,在意軍實施炮擊時,第一道防線內幾乎空無一人,士兵們都轉移到了后續防線中。而當意軍步兵開始上前時,守軍也就迅速進入第一道防線,同時還能很快就得到第二線部隊的加強。
而在意軍這方面,戰場的實際和參謀部事前的預想大不一樣。炮擊的準確性很差,沒有空中偵察手段,炮火觀察員就算站在教堂的塔頂上也無法看清遠方。步兵和支援炮火之間的協調低劣,炮彈供應不足,不少火炮又因為過度使用而炸膛。
以鐵絲網為目標的破壞分隊的成效也不佳,爆破筒的導火索很容易受潮而失效,就算成功引爆,在鐵絲網上開出的孔洞也很窄,只有集中使用大量爆破筒時,才會在鐵絲網上開出較大的通道。不過當意大利士兵從其中擠過時,卻形成了致命的瓶頸—他們成了送給敵人機槍手的禮物。
意大利第2集團軍猛攻托爾曼,但毫無成果。此地的一個焦點是俯瞰著普拉瓦的383高地,那里的奧軍陣地堅不可摧。指揮著位置最靠前的那個軍的軍長路易吉·卡佩羅將軍在利比亞的意大利殖民戰爭期間獲得過“屠夫”的綽號,他催動部下發動了多至30次沖鋒,但每一次都被奧地利人擊退。卡多納將軍一直很欣賞“屠夫”,但這一次也對他近乎野蠻的打法產生了懷疑。
就算意軍在局部取得了突破,也很快就會在敵人的第一次炮擊、手榴彈的狂潮或反擊部隊的刺刀沖鋒面前而瓦解。奧地利人發現在反擊中打退意大利人并不是什么難事,奧軍士兵已經習慣于艱難困苦和嚴苛紀律,他們能夠熟練地使用步槍、手榴彈、刺刀、尖刺棍棒和匕首,相比之下,意大利士兵粗枝大葉、經驗匱乏、軍紀不嚴。
當轉入防御時,意大利人吃到的苦頭一點也不比他們進攻時少。意軍士兵沒有在山間開辟戰壕必不可少的鑿巖機和炸藥,他們只能把石頭和沙袋堆起來保護自己,于是許多士兵淪為奧地利神槍手的標靶。當下級士官和士兵要求組織“合理防御體系”時,許多意軍軍官對此表示蔑視,稱這不符合意大利人“勇敢的性格”。
如是一來,和意軍總參謀部在戰前判斷的完全相反,奧匈軍隊在戈里齊亞附近地區毫不動搖,第3次伊松佐河戰役可謂開局不利。
要不惜一切代價
經過最初幾天的戰斗,交戰的重心移向了戈里齊亞以南的圣米克爾山一線。意軍和奧軍在這片戰場上反復拉鋸,控制權從一邊轉移到另一邊,意大利人一度壓過奧地利人的陣地,但很快又在后者的反擊下退卻。
在圣米克爾和蒙法爾科內之間,連綿山地的懸崖上下起伏,令人望而生畏。意軍投入了善長山地戰的錫耶納旅,經過連續惡戰,這個旅到10月25日奪取了一處奧軍堡壘,其時該旅的3個團已經全部投入交戰。
可是意大利人的喜悅是短暫的,就在那天晚上,奧軍發起了兇狠的反擊,迫使已無預備隊可用的錫耶納旅又回到了他們最初出發的位置上。第2天清晨,交戰雙方達成了一小時停火協議,用來收集和掩埋死者,因為戰場上的死尸已經太多了。
在圣米克爾山的北坡,意軍拉齊奧旅的第132步兵團也準備采取行動。這里的山勢很陡,從270米突然攀升到900米,此地的奧軍擁有完整的防御工事,多排帶刺的鐵絲網和機槍據點得到后方炮臺的支持。
第132團的進攻從10月21日開始,其第一個目標是北坡上的124高地。士兵們試圖用鋼絲鉗和爆破筒來開道,但努力歸于失敗,進攻一方不可避免地遭受了重大損失,經過連續10天的戰斗,第132團損失了26名軍官和707名士兵。制服濕透的幸存者躲在泥坑里,筋疲力盡,神志不清。

手握手榴彈的意大利士兵
然而在10月31日晚上,該團接到命令,要求他們在第2天早上重新發動進攻。團長維奧拉上校決定抗命,他向旅長沙納迪將軍報告稱:大雨使山坡濕滑不堪,面前的3排鐵絲網完好無損,敵人的炮火把進攻變成了毫無意義的屠殺,在這種情況下發動進攻是不可能的。
沙納迪知道維奧拉是一個勇敢的軍官,沒有充分的理由是不會拒絕執行命令的,于是他打電話給他的師長馬拉齊將軍,指出只有在相鄰的維羅納旅及時給予支持的情況,第2天的攻擊才會有成功的可能。
在距前線2千米的斯達盧西納,馬拉齊發出警告說:士兵們的“極端勇氣”可能會被指揮官的虛弱感所削弱,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千方百計地猛擊,勝利就屬于我們了。”馬拉齊說。
其實,馬拉齊是受到了軍長莫羅恩將軍的壓力,而后者則在電話里剛剛被集團軍司令奧斯塔公爵罵了一頓。在距離前線16千米的切尼亞諾的司令部里,公爵對行動“沒有帶來明顯的結果”感到遺憾,他要求參戰部隊的“每個人都要不惜一切代價,拼到最后”。
不管怎樣,第132團在11月1日沒有發起進攻。這樣一來,整個指揮鏈條上的壓力層層下傳,沙納迪將軍嚴令維奧拉上校必須在11月2日13時發動強攻。維奧拉上校發出抗議,稱不會眼看著屠殺上演。
到了2日的13時,第132團還是原地不動。軍長馬拉齊打電話給沙納迪:“如果再不進攻,就地解了維奧拉的職務!”維奧拉這才勉強下達了前進的命令。戰斗開始后,他像往常一樣從前面帶隊。第132團發起了多輪沖鋒,但敵人的火力壓倒了一切。19時左右,該團撤退了。第二天,維奧拉準備再度行動,但是暴雨讓第132團哪兒也去不了。

意大利軍官們在山地上觀察形勢
炮擊“玫瑰之城”
在維奧拉上校時而抗命、時而從命的同時,托爾曼和普拉瓦方向上的意軍也陷入了困頓。有幾支山地部隊占據了數處奧軍的戰壕,并在那里打退了敵人的反攻,但是這些在付出巨大努力后取得的“成功”,在地圖上幾乎小得無法顯示。
惡劣的天氣籠罩著整個地區,到11月初,戰壕里到處泥濘一片,大小道路幾乎無法通行。3日那天下了初雪,那一天的戰斗也非常血腥,僅這一天就有4000名意大利士兵傷亡。號稱精銳部隊的卡坦扎羅旅在那時已經損失了70名軍官和2800名士兵,幾乎占到編制數的一半。
在絕望的籠罩下,意軍各部隊都失去了繼續戰斗的動力。到了11月4日,卡多納將軍“暫停”了全線的攻勢,第三次伊松佐河戰役實際上到此結束。羅馬官方宣稱意大利軍隊贏得了勝利,實際上這場戰役的收獲是微不足道的,意大利人僅僅奪取了普拉瓦以南的一些沿河地帶,以及波德戈拉西面的兩座山丘。意軍距離主攻目標戈里齊亞的距離,僅僅比戰役開始之前縮短了一百米!而為了這些“成就”所付出的代價則是6.7萬人陣亡、負傷或失蹤。
意軍總參謀部對戰役進行了總結,指出事前精心安排的炮兵和步兵協同戰術沒能得到有效貫徹。高層軍官把戰役“只取得部分成功”的主要原因歸結為前線中下層軍官對部隊的控制不力,對于中下層軍官反映的戰場通信不暢的問題,則沒有人過問,這真是一次可悲的戰術總結。
11月10日晚上,連日來持續不斷的降雨升級為傾盆大雨,伊松佐河岸的山谷地帶完全被云霧所籠罩,塹壕陣地被水淹沒,道路變成了泛著白沫的溪流。很多人都認定在這種天氣下不可能采取什么敵對行動,然而卡多納將軍卻不這么想。
他一直認為,經過第三次戰役的沖擊,由馮·博伊納將軍率領的奧匈第5集團軍已處在崩潰的邊緣,意軍要做的就是再加一把勁。卡多納知道24個新兵補充營將在一兩周內到達伊松佐河地區,于是他下令在11月11日就展開對戈里齊亞的新一輪攻勢,這就是第四次伊松佐河戰役。
就這樣,千辛萬苦的士兵們僅僅經過一周的喘息停頓,就又被投入了血肉磨場。意軍仍以炮擊開局,然后步兵們以其最大的努力向被鐵絲網和機槍密集保護的托爾曼、普拉瓦、圣米克爾山等地的堅陣發起沖鋒。
奧地利守軍在上一次戰役中也損失頗大,而且沒能得到有效的補充,不過他們在山地上居高臨下,憑借著鐵絲網和機槍,硬是擋住了力量三倍于己的意大利軍隊的推進。戰場上大雨不斷,而且氣溫下降,然后在11月16日開始下大雪,許多倒地的人很快就被白雪完全覆蓋了。
在已經變得司空見慣的屠殺過程中,意軍在11月18日采取了一個特殊行動:炮擊了戈里齊亞城區3個小時。到那時為止,雙方的火力基本上都很注意回避平民,炮擊戈里齊亞被不少人認為是“全面戰爭”的開始。
戈里齊亞被稱為奧匈帝國的尼斯、“玫瑰之城”或“紫羅蘭之城”。由于此地在冬季也比較溫和,后有大山,前有伊松佐河,因此被塑造成哈布斯堡王朝治下一個田園詩般的所在。城市街道的兩旁滿是富麗堂皇的別墅,中心的公共花園非常漂亮,山丘上的中世紀城堡壯美如畫。雖然城內的3萬居民在奧地利同意大利的戰爭開始后很快減少了一半,但因為有數萬名士兵進駐,所以仍保持著戰前的人口水平。
曾經有人建議奧軍指揮官博伊納將軍疏散城中居民,不過他沒有這樣做,也許他覺得戰火不會直接光臨此地。至于卡多納將軍在明知不可能攻下戈里齊亞的時候還要下令炮擊當地的動機,也無法解釋。有人指出,也許是持續不斷的流血瓦解了這位總參謀長內心文明的克制吧。

意大利陸軍總參謀長卡多納將軍

這是伊松佐戰場上的意軍戰壕
一無所得
炮擊美麗的城市自然無助于意軍在戰場上的突破。第四次戰役進行幾天之后,那位人稱“屠夫”的卡佩羅將軍給第2集團軍司令弗魯戈尼將軍發出了這樣一份報告,可以說是全面概括了意大利士兵所處的困境。
他在報告中指出:“浸泡在泥漿里的步兵得不到充足的熱口糧,也就無從恢復他們的力量。我的部下在沒有食物的情況下走了兩天多,與其說他們是士兵,倒不如說是行走的泥巴。他們缺乏的不是前進的意志……他們缺乏的是體力。甚至連預備隊都在水里和泥里呆了好幾天,因此不可能指望他們來使一線部隊重新煥發活力。”
在圣米克爾山的北坡,在戰役間隙僅僅得到兩天假期的第132團重新發起了沖鋒。11月22日,那位敢于抗命的維奧拉上校在戰場上陣亡,當時他帶領部下再度沖擊124高地,這次沖擊再度歸于失敗。
就在維奧拉戰死的第二天,意大利陸軍總司令部下令對在多個方向上集中力量發動最后一次進攻。這道命令完全是脫離現實的。那時大量普通士兵都已經不能再穿靴子了,因為凍傷流行,他們的雙腳腫得可怕。雨雪天氣總算放晴了,但也帶來了新問題,軍服上沾滿了泥巴,干涸后,泥層就像木板一樣僵硬。
卡多納將軍是看不到這一切的,他身在距離前線足有40千米遠的烏迪內,被報喜不報憂的參謀們籠罩,午餐是熱咖啡、烤肉和水果。按照他的嚴令,第四次戰役又持續了幾天,一隊意軍在11月26日打下了圣米克爾山的一處高地,但是奧地利人一通反擊,就又把意大利人趕回原位置了。
馬拉齊軍長終于來到了前沿陣地,看著到處飛舞著手榴彈、石塊、木棍,甚至是裝滿糞便的罐子的景象,他感到無比震驚。據說他后來對一位來自羅馬的高級參謀官喊道:“你們不就是想要我這里死更多的人嗎?看吧,這正是你們想要的!”
12月的第一個星期,大雪再次覆蓋了一切,軍事行動終于漸次停止。到了12月9日,卡多納將軍叫停了第4次伊松佐河戰役。這一次意大利人的收獲比上一次戰役還要小,同時增加了4.9萬名傷亡者,而在這兩次交戰中,奧地利軍隊分別損失了4.2萬人和2.5萬人。
意軍總參謀部再次總結經驗教訓,并歸納出了新的戰術思想,時光在延續,還會有更多次類似的戰役。從1915年6月到1917年11月,一共上演了12次伊松佐河戰役,這些沒完沒了的戰斗血腥而無意義,雙方都難從中獲益,最終導致大約70萬名意大利士兵和35萬名奧匈帝國士兵喪生,誠然是一戰中最可怕的往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