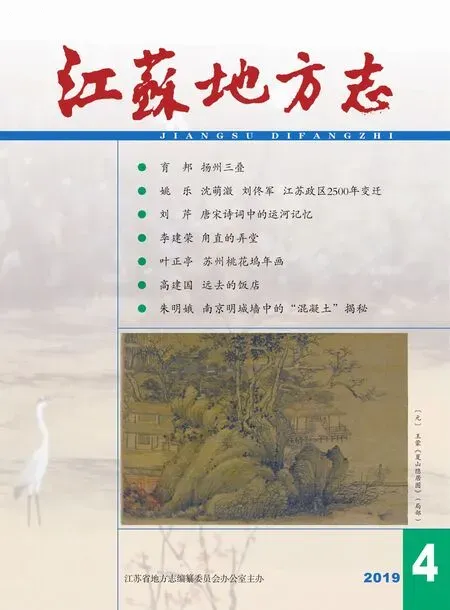試探江蘇地區早期聚落的形成與發展
◎ 周宇嫽
江蘇歷史悠久,是中華先民最早繁衍生息的地域之一,在南京湯山發現的“南京直立人”的頭蓋骨化石顯示了早在30多萬年以前江蘇就有原始人類的活動蹤跡。在今宿遷泗洪的太湖三山島、順山集、東海大賢莊等一批舊石器時期文化遺址則說明江蘇地區在整個舊石器時代聚落的分布十分廣泛,是中華大地人類文明的發祥地之一。正是這些遠古先民,揭開了江蘇早期歷史的神秘面紗。
一、聚落的形成
形成之前
眾所周知,原始人類沒有屋舍,借助自然提供的樹木或洞穴等而形成穴居、巢居、半穴居等居住形式。這在許多古籍中皆有追述:《莊子·盜跖篇》“古時禽獸多而人民少,民皆巢居而避之,晝拈稼粟,暮棲樹上,故名已曰有巢氏之民。”早期人類的居住方式與其他大部分陸地上的動物一樣,并沒有什么特別之處,人與鳥獸生活在同一方天地之下,為遮風霜雨雪棲居在同樣的洞穴之中。《易經·繁辭》中記載有“上古穴居野處,圣人易之以宮室”,穴居、巢居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后逐漸發展成為半穴居和地面建筑。
這個時期的人們將粗笨的石頭用作武器進行自御和捕獵,過著十分簡單的采集和漁獵生活,每日吃食全靠運氣,朝不保夕,因此人們求生比較困難,存活率極低,有考古記載曾在一個舊石器時代的洞中發現有38個人體,其中大部分都為15 歲以下的孩童,此外在同一個洞穴中還發現不少不同性質的動物骨骼(董鑒泓,中國城市建設史[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4:
1-3)。這是由于原始人類求生的困難程度致使人獸同居、命數不定。三山島遺址位于原吳縣(今吳中區)東山西南的太湖中,由大山、行山、小姑山相連而成。該遺址于1985 年5 月發現,南京、上海、蘇州、吳縣的考古工作者于年底聯合進行發掘,面積36 平方米,出土了大量舊石器時代的打制石器5000 余件和大量哺乳類化石。據考古分析,三山島舊石器遺址是當時人類制作石器的制造場和季節性居住營地,遺址的發現,第一次揭示了太湖地區一萬年以前舊石器時代人類生活面貌,三山島遺址也是迄今所知蘇州歷史文化的最早源頭。江蘇境內目前發現的最早的人類遺址——5 萬年前的下草灣遺址,淮河中下游地區重要的新石器時代中期遺址——8000 多年前的韓井遺址,都是在泗洪發現。泗洪縣城向北30 里,梅花鎮大新莊順山集遺址,是一個8000 多年前的人類遺址,是迄今江蘇境內所知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這一發現將江蘇文明史向前推了1600 年至1800年。據相關考古資料,順山集遺址面積約5 萬平方米,考古已清理墓葬92 座、灰坑26 座、房址5 座,出土陶器、石器、玉器、骨器400 多件。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長林留根說,順山集遺址的環壕長1000 米,寬6 米至24 米,先民建起如此規模的環壕,非常不容易,堪稱“天下第一壕”。北京大學教授李伯謙認為,遺址現場發現的約10 厘米高的方形陶灶,按年代計算,可以說是“中華第一灶”。東海大賢莊遺址,采集到一批重要的石器,并鑒定其時代為舊石器晚期,距今16000 ~10000 年。
形成之初
原始社會后期,隨著人類生產力的逐漸提高,種植農作物以持續生產出人類所需糧食成為可能,這是一種古老原始的農業耕作方式,農民們披荊斬棘,放火燒荒,開辟出一塊塊田地,再用棍子或者鋤頭挖掘出一個個小坑,投入農作物的種子,埋上土,依靠焚燒后的枝干灰燼形成的自然肥力來養殖作物。這種農業方式在如今的南美洲、非洲等地依舊十分常見。然而在當時,這作為一種十分先進的行為在長江中下游地區很快傳播開來,并與畜牧業和狩獵業分開,正式成為一種生產方式。同時這時期人類開始可以制作較精致的石器和多種骨工具,生產力也有了一定的提升,于是地理空間上開始形成很多以農業為主、以農地為核心的范圍較大的固定居民點,正式步入原始聚落階段。
自此人類擺脫純靠運氣的采集經濟,進入穩定的種植經濟。這也是人類結束頻繁的遷移生活而得以定居的前提條件。真正意義上的聚落階段得以開始,人們選擇適宜農作物生長和適宜人類生存的地域圍聚而居、修屋建舍,水資源豐富、土壤肥沃的江蘇地區成為原始人類的首選地之一,因此從商周時期開始就開始不斷發掘有原始聚落的遺址(鄧先瑞,吳宜進,長江流域住區的形成與發展[J],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12]:50-54)。這個階段人類的手指更趨于靈活,可以制作更精細和多樣化的石器、陶器,還發明了弓箭、投矛器等生活工具,原始手工業開始出現。
二、聚落的發展
到了新石器時期,太湖流域的文化以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聞名于世,三者在時間上有承接關系,與同時期黃河中下游的仰韶文化、半坡文化、龍山文化各成體系,各有各的地域特色。
在馬家浜文化時期,江蘇境內多以水稻為主要農作物,蘇州草鞋山遺址中發現的文化水稻田是中國歷史最悠久的有灌溉系統水稻田,相應配有水井、水塘、水溝等灌溉設施,遺址中出土的炭化稻被考古證明為人工種植稻,意味著稻作農業在6000 年前已日趨成熟,稻作生產已經普及。同時在遺址中發現野生葛纖維織成的羅紋葛布殘片以及眾多史前琮璧玉器則反映了手工技藝精湛程度遠超同期其他地區。由此證明,當時太湖流域江蘇地區的遠古文明已位居全國前列。除草鞋山遺址外,吳越文化范圍還有昆山綽墩山遺址、澄湖遺址、越城遺址、上海馬橋遺址、無錫仙蠡墩、浙江吳興錢山漾、杭州水田畈等都有稻粒發現。不僅如此,還發現有古稻田遺址,昆山綽墩山遺址在距地面一百厘米的馬家浜文化層土層發現了二十多塊稻田,距今3000 年。有了水稻人工栽培,原始聚落的定居成為可能。
從將軍崖巖畫考證,將軍崖巖畫位于江蘇連云港市海州區錦屏鎮桃花村錦屏山南麓,南北長22.1 米、東西寬15 米的一塊混合花崗巖構成的覆缽狀山坡上,是中國迄今發現的最古老巖畫,也是東南沿海地區首次發現的巖畫,距今約7000 年。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稱之為我國最早的一部天書,內容反映了原始先民對土地、造物神以及天體的崇拜意識,是中國目前發現最早反映農業部落社會生活的石刻畫。
到了新石器時代晚期,大量聚落在江蘇大地上如雨后春筍般涌現,馬家浜文化在走向崧澤文化的同時,江蘇局部地方出現更具小區域特色的北陰陽營文化、龍虬莊文化等遺存(穆東旭,區域交流影響下的文化趨同與社會發展—東山村遺址崧澤文化墓葬的啟示[J],東南文化,2018[3]:70-79)。但江蘇大體都在相同的地域和社會環境背景下發展,手工業較之前有了長足進步,陶器制作掌握了新的技術并且日趨專業化,同時制玉和金屬冶鑄開始成為新興的工業部門,釜形鼎、盆形鼎發展成為主要的炊器,手工業的發展致使社會財富急劇增加,開始出現貧富不均的現象(王榕煊,太湖流域新石器時代聚落形態與社會復雜化研究[J],文物鑒定與鑒賞,2018[17]:44-51)。在江蘇張家港東山村崧澤遺址中發現有馴養家豬的隨葬,這被考古界認為是私有財產的象征,說明當時聚落出現等級分化的趨勢,社會已逐漸貧富化。母子合葬、父母孩子三人合葬、男女合葬墓的出現,表明當時已有家庭出現,持續了幾萬年的母系社會正在走向父系社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到了良渚文化時期江蘇地區已經呈現出明顯的聚落等級分化現象。據考古記載,在江蘇境內發現的良渚時期大型聚落的遺址數量多于崧澤時期,然而基層聚落的規模相較崧澤時期有變小的趨勢,數量卻較之前翻了一番。這個現象說明,此階段江蘇的聚落等級劃分越來越細致,規模大的聚落日愈增大且數量增多,小的聚落也越發似星星點點般遍布。
在經歷新石器時代漫長的發展之后,江蘇地區史前文明已經高度發達,然而璀璨的良渚文明在距今4000 年前后戛然中斷,并未繼續發展而上升為中國文化的主流,據研究是由于這一時期全球性的氣候變化引起了海平面上升,海水浸沒了良渚居民的家園,迫使他們遠徙異鄉,融入到華夏民族發展的洪流之中。數百年之后,海水退落。當先前的人們重返這片沿海低地時,這里又回到了洪荒時代。江蘇連云港市曾經發現的藤花落遺址,位于南云臺山和中云臺山之間的沖積平原上,占地面積30 萬平方米 。直到商周之際,周族的一支部落遷徙南下,在江南與當地居民融合,共同建立了吳國,改進生產方法,提高生產力水平,十余世之后,時至春秋中葉,原先不為世人注意的吳國開始壯大,登上歷史舞臺。
而連云港曾經發現過藤花落遺址有內、外二重城墻結構,外城平面呈圓角長方形,由城墻、城壕、城門等組成;內城位于外城內南部,由城垣、城外道路、城門和哨所組成。藤花落遺址是中國龍山文化城址之一。龍山文化,泛指中國黃河中、下游地區約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一類文化遺存,屬銅石并用時代文化。這一時期文化的最顯著的特征便是城址的發現。
三、影響聚落形態的因素
自然環境因素
人類的生存有賴于周圍的自然環境,在持續地與自然的接觸中,人們了解自然、認識自然,并提升成對待自然的態度和理解。而在現實的生產和生活中,則表現為不斷改善自己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以期最大限度地與自然環境相適應。
最初,人們只是利用自己熟悉的自然材料、運用已經掌握的簡單工具,予以營造能遮風擋雨的茅舍。這些屋舍經歷了長期的實際使用和自然界的風雨考驗,一些功能不甚健全,結構不太合理的逐漸被淘汰,留下的是適宜人居和環境要求的屋舍,便開始為更多人模仿,更廣的傳播開來(雍振華,江蘇民居[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9;36-38),江蘇居民的居所與聚落當然也在這特有的自然環境影響下呈現出自己的風格與特征。
在我國廣袤的疆域中,江蘇的自然環境堪稱得天獨厚。我國第一大河長江經此注入東海;第二大河黃河也曾改道江蘇;淮河則從此橫貫入海。江蘇地區水體密集,交織如網,雖然人類難以在水中生存,但日常生活之中卻須臾不能離開水。遼闊平和的湖畔、寧靜流淌的河邊成為人類理想的生活環境,因此江蘇先民自遠古時代就依托河、湖之利而在此繁衍生息,成為全國最早形成長久定居的人類聚落之地。
多水的特定自然環境,影響著無數人的生產生活,也影響了他們聚落居所,從而顯現出地方特色。江蘇先民從幾千年前開始的定居聚落中多以木材來構建房屋建筑,普遍采用防潮、排水設施以適應南方多雨潮濕的自然環境。如:泗洪縣的順山集遺址是目前江蘇境內發現最早的史前人類文明遺址,泗洪縣處于淮河中下游地區,水患較多,遺址內發現的房子多為半地穴式和淺地穴式,但無論是什么形式,房屋內部居住面都會高于正常水位線,以此來防止水患煩惱。在遺址中發現的環壕也是為防止水患,排水防洪所用。海安青墩遺址四面環水,代表了江淮東部地區獨特的原始文化。遺址中發現有不少保存尚好的建筑木構件和柱洞遺跡,大概能夠推測先民們在地表打上柱洞,插入木樁,而后在木樁上鋪設木板形成居住面,在上構建木制房屋。這種干闌式的建筑以木材為基礎搭建平臺,人生活在離地一米多高的木制構架基臺之上,既可適應多雨的江蘇地域環境,又可防御蟲蟻野獸的侵襲。
氣候條件因素
與自然環境一樣,氣候也是條件影響人類文明的重要因素之一。從社會群體的層面看,氣候的差異直接決定了他們的生產方式,進而影響生活方式乃至社會結構;對于人類個體,氣候的變化刺激他們的感官而使軀體做出反應,以至于直接采取增減衣物、完善居宅等措施予以應對。江南絕大部分地區屬于北亞熱帶濕潤季風氣候區,春、夏季節由東南海洋吹入的暖濕氣流,帶來充沛的雨水。呈現出光照充足,四季分明,氣候溫和,雨量豐沛,無霜期長的氣候特征。因此居住在溫暖水鄉地區的人們常表現的溫和委婉、勤勞善良,宅弟建筑也因地制宜,形制符合地形地貌、氣候條件,更加精致細膩。
然而在江南境內,仍有小范圍的氣候相異,以淮河為界,淮河以北例如江蘇北部的徐州等地春、秋兩季較短,冬、夏季較長,春季天氣多變,夏季高溫多雨,冬季寒潮頻襲。淮河以南地區四季分明,氣候溫和,雨量充沛,雨熱同季。這些微小的氣候變幻影響了民居營建時建筑細部和組合方式的形成。蘇北聚落民居因要抵抗頻襲的冬季寒潮,門窗洞口的開口面積都較小,單體建筑也以三面嚴封為多。連云港市傳統民居在保證夏季要抵抗海洋濕熱氣候的前提下,將貝殼等作為建筑原材料,具有隔熱蓄熱功能,同時還能兼顧冬季建筑內部的保溫效果。而江南地區的營建中居室墻壁高,開間大,前后門貫通都是為了應對炎熱潮濕的氣候特點。為便于防潮,建二層樓房多,底層是磚結構,上層是木結構。
因而在江南這樣一個地形地貌大致相近的區域,由于氣候條件的不同而使得小區域中的聚落和民居也呈現出了相宜風貌。
四、小結
聚落不是天生存在的,而是人類文明進化和進步的必然產物,江蘇地區聚落從無到有,不僅與江蘇特定地理環境相適應,更是因為地域環境的獨特性才演化出與中原文明、西部文明所不同的江蘇文明。探究江蘇早期聚落不僅可以了解該地區早期人類文化進程和物質文明,對于研究中國歷史起源也有著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