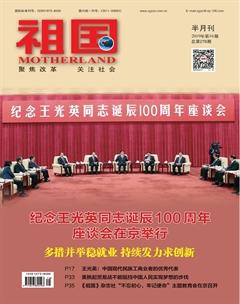論文身現象的合理性根據
摘要:作為考古史上最古老的藝術形式之一,文身現象的存在是有其重要的合理性根據的。而從古到今,文身的象征意義和存在意義也在發生著改變。第一,獲得認同感的心理需要。它包括自我認同和社會認同,文身不僅是一種自我接受和肯定的表現,還是被某一群體或社會認同接受的標志。第二,逃避心理的影響。為了規避某種危險或逃避某些壓力,文身成了保護自己、釋放自己的一種方式。第三,美化自我的一種手段。追求美麗是人的天性,文身作為身體裝飾的藝術有美化的作用。第四,作為一種精神期待與紀念。通過文身圖案來表達對平安、好遠、健康等的追求或表示對某人某事的紀念和祝福。本文運用人類學和社會心理學的視角增加對文身現象的闡釋力度,力圖較全面的分析文身現象的合理性根據。
關鍵詞:文身? ?認同? ?逃避心理? ?美化自我? ?期待與紀念
自原始社會以來,我國民族傳統文化就與文身有著密切的關系。近來文身常現身于體壇、影壇的明星身上,引發媒體大眾的廣泛關注。文身是考古史上最古老的藝術形式之一,文身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也被賦予了愈來愈多的形式和意義。它不僅僅只是一種藝術的表達形式,更是社會建構中的一種“變相”的反映。另外由于文身從開始的刺刻制作到完成后的表現形式的獨特性,不可忽視的一點便是文身的污名化始終存在,這種以文化進化論的觀點對文身的評析,也在文身的演變發展研究中產生了深遠持久的影響。然而,按照進化論的說法,在高度發展的當代社會,文身現象應該是逐漸消失的,這顯然與當下文身不僅沒有退出歷史舞臺反而又轉向時尚潮流發展之勢是相違背的。這也表明將文身的偏向負面的特征刻板印象化,并由此掩蓋其他特征是失之偏頗的。
其中早期的文身曾被做為一種刑法,在中國和日本等都一度視為處罰手段,鑒于文身作為刑法的存在已消失,本文將摒去文身的該歷史作用,同時力圖改變固化的價值觀念和文化偏見。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獻研究法。查閱相關的研究文獻進行文獻綜述,發現相關文獻研究的優點和不足。深刻理解文身這一藝術形式存在和傳承發展的內在根據。
從世界范圍內來看,文身的形式和象征意義多種多樣,但上升到人類學的角度來看,則大致歸于四個大類中。
文身產生的第一類原因是體現一個群體的象征作用。蘇丹喀士穆的土著居民視文身為自身部落的標志;而在新西蘭的毛利人文化中,文身圖案用來表明個人社會等級和判斷所屬集團。因為文身可以使自己的特性顯示出來并受人尊敬,故而是值得驕傲之物,(利普斯,2010:45)。不論是標示著成年與否,用來區分敵友,還是對在紡織狩獵乃至打仗中表現優異之人的褒獎,都是體現了一種認同感,這種認同感既包括社會認同也包括自我認同,是一種承認和肯定。而通過文身這一方式恰恰可以表現出來。文身者即是通過文身來標榜自己的群體身份,反映個人身份,是對其群體身份與地位的正向的認知評價以及情感價值體驗。同時,一個群體接受該者的表達方式亦是允許其文上本群體的標識或圖案。認同感在文身的體現時至今日依然存在。
文身產生的第二個原因是為了避免傷害。文身的習俗在古書中多有記錄,如《漢書·地理志》中談到 “(越人)文身斷發,以避蛟龍之害” 。應劭注:“(越人)常在水中,故斷其發,文其身,以像龍子,故不見傷害也” (班固,1990: 卷八十二下)。這些文字說明了人們之所以要文身,是為了規避走獸的襲擊傷害而選擇通過紋飾裝扮達到恫嚇和凝聚的作用。 德國人類學家利普斯(2010:45)認為,在皮膚上畫上圖案的顯著效果是作為一種心理武器,從而引起敵人的恐懼;古代不列顛人在打仗中以藍顏色涂抹身體,以具有可駭的外貌。這其實也是印象管理中的一種策略: 恫嚇。通過給別人造成恐怖印象使別人由于害怕而接受控制或不敢挑戰,由此達到自己的目的。 文身恰好充當了制造印象的手段,這是一種印象建構。海南島黎族婦女的文面也說明了這點,長期處于矛盾沖突狀態下的黎族婦女常常成為被擄掠的犧牲品,婦女的弱勢地位使她們以紋面來自我保護,以期望改變被擄走的局面,進而尋求安穩安全的生活。 這時文身就成了自我保護、抵御外侵的手段。無獨有偶,我國獨龍族婦女文面的淵源也同黎族類似。婦女為避免慘遭擄掠,將臉刺染上一種黛墨青紋,令人觀之而感到恐怖 (方鵬,2005: 104-106)。 這種逃避心理也賦予了文身存在的重要作用,以改變印象來增強或減弱自身存在感從而應對危險實現安全。
文身產生的第三個原因是為了審美的需求。通過把作為自然物的人體添加某些象征性的符號從而轉化成為表現文化的對象,人體裝飾就是為了滿足一種審美的需求(馬廣海,2003:378-379)。這種以審美為動機的文身形式豐富多彩,古老的塔斯馬尼亞文化采用疤痕文身,即圖案的刺紋和斑點不著顏色而形成,在今天的非洲大陸上仍然流行。另一種涂色文身手續更為細致、圖案繁縟布局調和華美,這種文身手法在新西蘭的毛利人中有著極好的效果。現代社會出現的文身圖紙、水晶紋身等裝飾性暫時性的文身也緩解了追求美麗而又對永久性文身彷徨不定者的顧慮(霍發水,2007:56-57)。而以審美為動機的文身圖案極具美感和吸引力。卡都衛歐族族人的臉有時候是全身都覆蓋一層不對稱的蔓藤圖案,中間穿插著精細的幾何圖案。畫畫使用的母體相當簡單,螺旋形、S形、十字、鋸齒形、希臘回紋、卷軸形等等,但都把這些母題結合成使每一個臉孔圖案均具原創性(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2009:223)。現代社會中,文身圖案愈來愈豐富,花草蟲魚、飛禽走獸、仕女武士,以及新時代誕生的新奇圖形、文字語言等等,都成了可以被文在身體上的圖形,極具創新性和個性。
文身產生的第四個原因是為了精神寄托,以表達文身者的期待、紀念或祝福。古時在北方民族中,以事巫祝事務的人物,往往也有繪面現象。這些人常常在身體上繪許多奇異紋樣,如圓圈曲線、嘴、眼睛等樣紋,由此并借助多方能力與機巧,行祛病、除邪、攘災之事,敏于通神、卜貞吉柞之機宜。在另外一些民族中,活著的人為表達對死者的撫慰、亡魂的一種恐懼,在舉哀過程中,就是通過繪身為主要媒介形式實現的。夏威夷人有他們的傳統的被稱為‘kakau的紋身藝術。他們的紋身不僅適合裝飾和易于區別,而且具有保衛健康和精神幸福的作用。波利尼西亞的人們相信一個人的精神力量和生存能力是通過紋身顯示出來的(周燕玲,2007:158-160)。卡都衛歐婦女的圖畫藝術解釋為是一個社會的幻覺,一個社會熱烈貪婪地要找一種象征的手法來表達出那個社會可能或可以擁有的制度,但是因其利益和迷信的阻礙而無法擁有。婦女以她們身體的化妝來描繪出整個社會集體的幻夢,用化妝來贊頌那個黃金時代。
綜上所述,文身的存在是有其合理性根據的。從社會認同、自我認同,規避危險釋放壓力,美化自我到作為精神寄托的期盼紀念,在社會層面和個人層面闡釋了文身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參考文獻:
[1]愛德華·泰勒.人類學——人及其文化研究[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
[2]班固.漢書[M].中華書局,1990.卷八十二下
[3]方鵬.關于海南島黎族婦女紋面的幾個問題[J].貴州民族研究,2005,(02):104-106.
[4]方文.學科制度和社會認同[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5]霍發水.痛苦造就的美——中國文化中的文身現象[D].石家莊:河北大學,2007:56-57.
[6]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憂郁的熱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223.
[7]利普斯.事物的起源[M].貴州:貴州教育出版社,2010:44.
[8]馬廣海.文化人類學[M].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3:378-379.
[9]馬廣海.社會心理學[M].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0.
[10]泰勒.原始文化[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
[11]于志勇.新疆地區考古發現的繪身和紋身[J].西域研究,1995,(03):98-103.
[12]鄭重.一種特殊的符號語言:文身刺墨——人類對美的追求的多樣性[J].藝術生活——福州大學廈門工藝美術學院學報,2012,(03):52-54.
[13]周燕玲.探析古代紋身藝術的地域特征及符號學內涵[J].藝術與設計,2007,(05):158-160.
(作者簡介:杜今,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