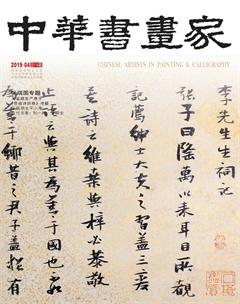現場問答
問:您剛剛提到了法家,請進一步談談您對法家的看法。
答:天寒地凍的冬天會給人以安定和冷酷的感覺,生機斂藏、萬物閉伏,世界籠罩在一種簡單而冰冷的秩序之中,單調而寂靜。這似乎就是法家有些冷酷的心靈。我一直覺得,當一個人的心靈完全被功利所充滿和占據的時候,那就是冷酷的。不幸的是,這正是法家對生命和心靈的理解。
法家可以讓人想起很多的名字,不過最重要的代表一定是韓非。這位生活在戰國末期的哲人曾經追隨過主張“人性惡”的荀子,同時還研究和解釋過《老子》,吸取并強化了那種清冷的感覺。在韓非看來,以利害為主的計算之心是人之常情,“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在他看來,這也構成了人和人之間交往的基礎。以君臣關系為例,其性質完全是彼此利益的交換,“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重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臣子出賣的是“死力”,君主用來交換的是爵祿,其間完全以計算之心相待,所以有“上下一日百戰”的說法。
君臣關系如此,這個世界中一般人之間的關系也沒有什么不同,韓非說:“故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天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輿人、匠人希望他人富裕或者死亡與愛憎無關,唯一的理由是利益,這就是韓非揭示的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真相。不過,最讓很多人無法接受的是韓非對于父子之親的理解。我們知道,這種關系被儒家認為是先天之愛的證明。而在韓非看來,其實質和君臣等關系并無不同:“且父母之于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此具出父母之懷妊,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后便,計其長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母之澤乎?”同樣是父母的血脈,男孩和女孩的命運卻大不相同,那些生了男孩的在舉杯慶祝,而女嬰卻有可能被遺棄。我們知道,傳統社會中人們對待男孩和女孩確實有態度上的不同,《詩經》中就有所謂弄璋和弄瓦的區別,而韓非這里說得更加冷峻。究其原因,則是考慮到男孩和女孩在未來對于父母的利益有區別。在韓非看來,如果父母和子女之間都以計算之心互相對待的話,那么這個世界上還有什么樣的關系能夠逃脫計算的命運呢?
在這種理解之下,愛和信任等對于這個世界來說就是多余的。就君主而言,韓非認為不能信任任何一個人,“入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則制于人”。信任他人就意味著把自己托付給他人,也就意味著受制于他人。哪怕這個他人是自己的父兄妻子。韓非子特別寫下了《備內》,認為君主應該重點防備自己的大臣、父兄和妻子。由此,愛一定也不適合于這個世界,君主不應該期待著把權力建立在愛的基礎之上。一方面,“愛臣太親,必危其身”;另一方面,對百姓的愛則會導致無功得賞,暴亂不止。韓非以治家來比喻國家的治理,“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從而提出“一斷于法”的主張。
去除了愛、信任、血緣親情等之后,法就成為韓非世界里的唯一主角。韓非批評了當時流行的各種學說,“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儒家以親親尊尊的仁義禮等挑戰法的公正和權威,而墨家用立足于兼愛的俠義去破壞法的禁令。至于道家所說,不過是一些“恬淡”或者“恍惚之言”,完全不適合于君主的需要。一個明智的君主應該意識到,除了法之外,國家不需要其他任何的文字和主張。韓非說:“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后來秦始皇的焚書坑儒,無疑是這種主張的實踐。韓非認為,官府應將法頒布于天下,群臣、百姓,乃至于君主都要受到法的制約。君主不該為了任何的原因逞其私意,而破壞法的權威與尊嚴。司馬談說“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是很正確的觀察。
從大的方面來說,法的核心不過就是刑德或者賞罰,韓非稱之為二柄。這是有國者的利器,臣民有功者賞之,有過者則罰之。君主必須親自執掌賞罰的權力,落入臣子之手是很危險的事情。這就又牽涉到對法家而言很重要的術的問題。所謂術,是指君主用來控制和應付臣子的方法,包括“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等。在韓非看來,只有法而無術,則君不足以知奸,權力反為臣所用。只有術而無法,則法令不行,不足以富強。因此,法與術的結合才是比較理想的狀態。
責任編輯:韓少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