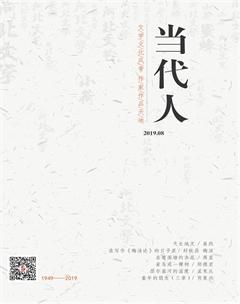底層社會潛流的歲月表情
黃桂元
我常常驚嘆于雖然的筆耕不輟。按說,身為中學一線語文教師的雖然,課程壓力之重可想而知,其業余寫作環境和時間難言優越,她卻總能以行云流水的寫作姿態示人,小說、童話、散文的新作問世已成家常便飯。雖然的取材往往無關乎“宏大敘事”,而是著意于凸現底層社會潛流中蕓蕓眾生的生活原狀,及其覆蓋著的柴米油鹽、婚喪嫁娶、喜怒哀樂、生老病死,諸如此類,點點滴滴,絲絲縷縷,那是底層社會潛流中的細碎浪花,微言大義,令人回味。
杜拉斯在《情人》開篇有句話,“18歲,我就老了”,此言可用來形容我對雖然的某種感覺。雖然來自鄉村,知曉農家的四季耕作,習俗百態,也熟悉鄉野里的草木榮枯,鳥語花香,其文學資源得天獨厚。她的小說不受“文以載道”的束縛,寫作伊始,就跨越了本該屬于天真、爛漫季節的青澀期,甚至給人以某種“中性”的感覺。她從不熱衷于抒寫男歡女愛的浪漫激情,也從不像一些女作家那樣長于彰顯個人的性別意識,卻對家長里短、雞零狗碎的俗世生態有著超乎尋常的表達興趣,且樂此不疲。其敘事文本每每發散出世俗的油煙氣味,用時下的說法叫“接地氣”。世俗不同于低俗、庸俗,關鍵在于是否含有“意義”。
小說《天長地久》,以煙熏火燎的俗世外殼出現,涉及的卻是生命倫理,也是哲學的終極問題。死是文學的永恒主題之一,但這只是就生命倫理意義而言。而在生活中,正如西方哲諺說的,死亡和太陽一樣不可直視。古往今來,無論東方還是西方,人對死亡這個話題都比較回避,尤其對于中國人,貿然談論死亡的話題,多少有些忌諱。雖然卻數次“直擊”這個領域,有板有眼,細膩入微,寒氣凜冽,令人驚悚,去年發表的《紅鬃綠馬》已讓讀者有所領教。《天長地久》則不同,同樣是逼真的寫實,同樣是冷靜和細膩,卻沒有讓人感受到肅然、恐懼與寒冷,而仿佛覺出一種貫通陰陽之間的暖意流淌其間。她把死亡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掰開揉碎,娓娓道來,“她姥姥活到九十一,無疾而終。她娘活到八十九,喝水時喝得急,一口水噎在嗓子里,去了。兩個姨也都八十大幾才過世。娘家那邊的女人都是豐乳細腰,例假走得晚,臨到六十才絕經,這些都是長壽的兆頭。而這邊族里的特點是,男的先走,余個老婆子再倔強地活上幾十年,無一例外。”但畢竟,與自己朝夕相處數十年的老伴兒歸到了那一個世界。雖然寫的是亡人,卻毫無幽魂鬼魅之氣,筆下滿滿的都是人間煙火,濃郁嗆鼻。她甚至以不失詼諧、調侃的筆法,把死亡帶來的陰郁、沉重悄然沖淡,“她躺在床上,蹺起二郎腿,手邊一杯茶水,嘴里一支煙,瞇起雙眼,似乎看到老伴兒盤旋在屋頂,像條十分靈活的黑魚左旋右轉。”處于生命盡頭的老年人,也是時間末端的游蕩者,他們曾經年輕過,性情過,蓬勃過,強悍過,最終必然走向死亡,如同日落西山、寒冬降臨,本是一樁大自然生命物種的生滅規律,再尋常不過。但雖然就是要通過小說敘述,讓死亡這件事變得不尋常,她要圍繞死者的“身后”制造事端,讓活著的人不能消停。小說中的女主人公沒有名字,只有敘述符號“她”,這不重要,有意思的是,這個“她”剛失去老伴兒,滿腦子都是死者的幻影,老伴兒并沒有走遠,使“她”無所適從,茫然失措,“她”覺得像做了一場夢,夢醒之后兒女忽成行,她那四十五年的日子都去哪啦?自己與誰拜過花堂成了親,繁衍出這么一家子?那個人怎么突然消失了?這是個深奧的終極謎團,老百姓卻有自己的看法。最后的解套人還是“她”自己,“她”明白了,老伴兒正在那邊等著她團聚,他們注定將在另一世界重逢。一切也就隨之釋然。
《圣經》里有“向死而生”的說法,佛教則相信生命的“輪回”,中國古代文化傳承不受宗教影響,平民百姓卻有自己的生命倫理觀,他們往往對《聊齋》中的鬼神故事,對那里描寫的人間、人情、人事懷有美好想象,這說明天長地久是可以存在的。這種愿景蠱惑著小說中的“她”,也鼓舞著“她”。死亡不是終極的歸宿,墳墓也不是永恒的黑暗,“她”篤信親人的天長地久適用于生前,也適用于死后。“她”想象那一天,自己在親人的痛哭聲中被送走了,其實是奔老伴兒而去,那邊聚集著一院子親人,都在等“她”如期而至,老伴兒更是一副年輕體健的貌態,已經把那里的家收拾得十分整潔,幾十年后,“她”和老伴兒還要陸續接來兒子與兒媳,孫子與孫媳,大家在陰陽之間不停轉移,你來我去,我去你來,生生不已。小說的意味由此浮現出來。這里涉及兩個層面:一是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如果我們相信“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也會承認一個事實,人是生命的個體存在,同時也是大寫的復數,是我們,是家庭、家族、村落、城市的生命群體組合,關乎社會的整體觀;一是生命的流程由兩極構成,生與死是對立的,又是合一的,死同生一樣,是人降生、成長、發展的一部分,這個全過程構成了人的生命的完整形態。
另一篇小說《門衛的江湖》,則完全是一幅底層人物的世相百態圖,雖然不惜用勾心斗角、雞飛狗跳的俗世舞臺劇場景,以對種種表情包的傳神勾畫,消解了日常生活中的詩意。上面寫滿無趣、無聊與無奈。年近七旬的老朱兩口子給德榮中學看了十幾年大門,這段歲月也是德榮建校史的長度,他們親眼目睹了這個私立學校的浮沉榮辱。大門如一道窗口,可以接觸到社會各色人等,老朱兩口子置身其間,經歷了最后的飄搖風雨。投資人宋董,管理校務的老湯,總務主任的蘇志軍,人人都懷揣著盤算,還有難纏的學生家長,偷雞摸狗秘密鬼混的學生,種種行跡,不一而足。學校最后解散,演了一出樹倒猢猻散的鬧劇,最值錢的自然是樓和地皮,可惜誰也弄不走。“劉保安和萇保安奔入微機室,每人拆了臺電腦,裝入箱子,抱進門房塞到床下。教職工們犯了搶,四處搜羅值錢的東西頂工資。蘇主任四處亂躥,管誰誰不聽,只好也動手,把微機室鎖起來,實驗室也鎖起來。”朱老太僵在大門口蒙圈了,眼睜睜看著大家往外運這個送那個,這么大個學校,說倒就倒了?她是校史的見證人,對德榮懷有感情,但還是腦袋一熱,趁亂把門房的窗簾拽下來,夾在胳肢窩里走了。以寫實又不失詭異的敘述筆墨,把社會生活里的大概率事件寫出小概率妙味,是雖然的拿手好戲。她的小說是放大鏡,顯微鏡,甚至是哈哈鏡,敘述從容,語言老道,恣肆快意。她善于在觀察、敘述、評價的過程中暗含反諷,仿佛看透了人的骨頭縫隙里形形色色的東西,暗通《世說新語》的神髓。
鐵凝認為“小說不是玄學”,是歸納小說藝術特質的一個點睛之論。也確實,有些作家把小說寫成了云山霧罩、令人不知所云的“玄學”,且自視甚高,自鳴得意,仿佛能讓人看明白是小說的原罪和硬傷。其實,把小說寫明白進而引人入勝,需要高超的敘事內功。雖然小說的精妙之處和著力點,不在故事情節怎樣的曲折、復雜和傳奇,而是對世態人物原滋原味的敘述過程。如一些評家認為的,雖然的小說注重的“不是講故事,而是說事”。說白了,舉凡故事性,即故事的推進速度,千曲百折,傳奇色彩,都不是雖然小說敘事的追求目標。不靠故事吸引人,才是小說家的一種能耐,引用雖然自己的話,“應該能講而不講,才算本事”。這種小說很吃功夫,而在“說事”中,她對人最感興趣。“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這決定了人物關系是支撐小說生命的要素,《天長地久》里的“她”和老伴兒及家人的關系,《門衛的江湖》中老朱兩口子與學校相關人等的關系,皆如此。人性的內部秘密和復雜性,是通過人物關系來實現的,人物關系的確立、發展與變化,互為養殖,互為因果,這也為雖然小說提供了敘述的無限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