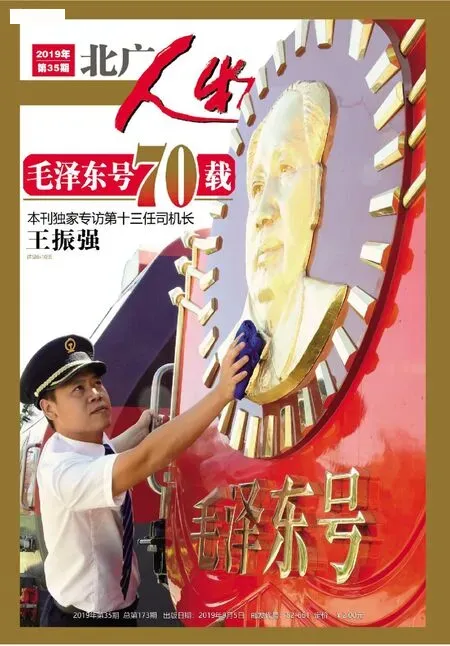徐中玉一位文化老人的硬核人生
一代學人徐中玉先生日前離世,他為語文教育奉獻一生,近40 年,僅全日制本科《大學語文》累計發行3000 多萬冊,其座下弟子何止三千。日前,徐中玉的友人兼同事王紀人深情回憶了一代學人徐中玉。
把失去的寶貴光陰補回來
徐中玉先生生于1915 年2 月15 日,今年華誕已過,虛歲就是105 歲了,在學界是少有的人瑞。我與他接觸較多時,他已度過了坎坷困頓的中年,步入了老年。但他的干勁和作為哪里像是過了耳順之年的人?我推想,除了他身上有遺傳的長壽基因外,還因為他要把失去的二十年寶貴光陰補回來。作為一個旁觀者,我是有深切體會的。
從新時期到本世紀初,徐中玉度過了一個學者兼教學和學術活動組織家的黃金時代。中玉先生本人又是一個有遠見卓識、不滿足偏安一隅的人。早在上世紀80 年代初,他就與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共同倡議,使中斷了三十年的大學語文課程在國內許多大學得以重新開設,并率先主編了《大學語文》教材,選目令人耳目一新,被許多高校采用,在各種版本的同名教材中,市場占有名列榜首。他不僅是倡導者、主編,還是眾望所歸的“大學語文研究學會”的會長,對提高中國大學生的語文水平作出了杰出的貢獻,堪稱當代中國大學語文之父。
中玉先生還是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指導委員會中文專業委員會主任,任《中文自學指導》雜志主編。自考指導委員會中文專業需統一編寫出版相關的自考教材,累計的印數巨大。其中有的教材編寫他親自主持,有的委任主編和副主編,如自考教材《文學概論》。我作為作者之一參與這部長達50 余萬字的教材編寫,去年出了最新的修訂本。
他的謙讓精神值得欽佩
中國文藝理論學會的建立及其直屬刊物《文藝理論研究》的創辦,是中玉先生對新時期以來中國文藝理論獨特而重要的貢獻。中國文藝理論學會的前身是高等學校文藝理論研究會,創立于1978 年5 月。周揚任名譽會長,陳荒煤是第一任會長,副會長是黃藥眠、陳白塵和徐中玉,實際操辦者是中玉先生。學會連續舉辦了幾屆論題富有現實意義、反響甚大的年會。如1980 年7 月在廬山開了文藝與政治關系的理論研討會,此論題正是當時中國作家和理論家迫切關注的。荒煤、丁玲等文藝界的資深人士與高校文藝理論教師共同討論,各抒己見,參會者都覺得收益良多。會議報道和論文發表后,在國內開了此論題的先聲。幾屆下來,要求加入學會的申請者已超出高校的范圍,旁及研究所、媒體、出版等專業人士。1985 年在桂林召開的第四屆年會上,即改名為中國文藝理論學會。中玉先生本人直至1993 年才任會長。他作為學會的創始人,在默默無聞地從事所有實際領導工作達15 年之后才出任會長,固然是出于有利工作的深謀遠慮,但他的謙讓精神值得欽佩。

他不僅是倡導者、主編,還是眾望所歸的『大學語文研究學會』的會長,對提高中國大學生的語文水平作出了杰出的貢獻,堪稱當代中國大學語文之父。
并不是所有的學會都有自己的刊物,而中玉先生創辦的這個學會,在1980 年6 月就創刊了《文藝理論研究》。中玉先生在考慮刊名時,我提出了這個比較直白的刊名,為了強調這是一本理論刊物,而且旨在對古今中外文論的全方位研究。中玉先生采納了這個刊名,并通過荒煤請周揚題字。主編仍由會長荒煤擔任,副主編按副會長序次排列。
1985 年他和錢谷融先生并列刊物主編。此刊最初為季刊,后改為雙月刊,是國家社科基金第一批資助刊物,我記得當時一年不過撥款五千元。后由華東師大出版社刊印出版,并由學會和華東師大合辦。中玉先生是這個刊物的實際掌門人,且事必躬親。我那時是學會的副秘書長和雜志編委。記得當時同為編委的張德林和我經常到他的辦公室商討刊物諸事,包括約稿、選稿和退稿,中玉先生還與我們一起拆信、復信、貼郵票,大家都不拿編輯費。處理刊務晚了,他會邀我們去他家共進晚餐。他常征求我們有關刊物欄目和選題的意見,我們也可向他推薦稿件,但終審權在他那里。如果逢到要開年會了,他也會及早聽取我們的意見。
常人難以企及的充沛精力
除了在不定期的刊務會議上商量,有時他也會寫信征詢意見。如1991 年他致信說:“我們刊物、下次年會,這些問題請先考慮一下。目前,年會尚不成熟(時機)。刊物國外印象頗好(曉明回來講起)。最近有何新作?得意的便請寄來”。2002 年他來信說“我刊準備切近些當前問題”,“也想召開些很小型的座談,談得深些,在刊物上發表。希望提建議。”當年我在回信中提了什么建議已經忘了,但寄過一些自覺不至于辱沒刊物的文章還是記得的,其中有一篇萬字稿他排在卷首,還寫信鼓勵我再寫。但他也退回過我一篇萬字長文,那是我為《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寫的一個條目。對此我沒有意見,因為不一定適合作為刊物的論文刊登。《文藝理論研究》在中玉先生親力親為親自把關下,成為學界公認的具有前瞻性、創新性和權威性的文藝理論刊物。
四十年來,中玉先生以常人難以企及的充沛精力和敬業精神從事了眾多的工作,難以一一盡述。他在上世紀90 年代初致我的一封信中說:“日忙于雜務,荒陋益甚。可能情況下還想做點好事實事,如此而已。”因為他兼任的工作太多,又事必躬親,必然會覺得不勝繁雜,但他始終停不下腳步,“還想做點好事實事”。如此質樸的話,卻道出了一位熱誠愛國和專注事業的老知識分子的肺腑之言。現在他雖然躺在醫院的病床上,意識漸趨模糊,但他留在我記憶中的,永遠是挺直了腰背走路,以及挺直了腰板做人。他生來就是一個不知疲倦的實干家,又是一個寧折不彎的硬漢。這就是他令人敬佩的硬核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