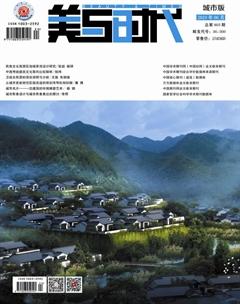“收入-幸福感悖論”與城市居民生活幸福感
葉茂愉
摘 要:為了回答為何社會經濟地位更低的農民及農民工生活幸福感卻并不低于(甚至高于)城市居民這一問題,文章提出了“相對幸福感”這一概念。該概念認為幸福感是一種相對感受,是在具體的生活環境中通過與他人的比較而得出的。因而,個體幸福感的高低,一方面取決于參照群體,另一方面則取決于具體環境中的互動氛圍。以城市社區生活為例,當社區中有良好的互幫互助傳統,能夠營造出和諧互助的社區氛圍,社區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便會得到提升。當參照群體超出社區層面,社會不公以及高昂的房價使城市居民產生強烈的“被剝奪感”,從而導致生活幸福感降低。因而,政府需要在塑造社會公平正義之風以及調控房價上下更多的工夫。
關鍵詞:“收入-幸福感悖論”;相對幸福感;城市居民
一、“收入—幸福感悖論”
以往的研究認為收入與幸福感之間呈現正向關系,收入是影響個體主觀幸福感的重要因素(黃嘉文,2013)。如果說收入對居民幸福感有正向影響,那么,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應該要比農村更高,但實際上卻出現了相反的現象,這該做何解釋呢?換句話說,為何社會經濟地位低的人幸福感反而更高呢(懷默霆,2009)?其實不僅在個體層面出現這種收入與幸福感相悖的問題,在國家層面也存在這樣的現象。早在20世紀70年代,伊斯特林(1974)就發現,國家層面的經濟增長并不會帶來國民主觀幸福感的增長。后人把這一現象稱為“伊斯特林悖論”。圍繞該悖論,形成了諸多理論解釋,如相對收入理論、適應理論和幸福飽和理論。其中,相對收入理論被認為是最為有效的解釋理論之一,在很多經驗研究中被引用。該理論認為,個體的主觀幸福感不僅取決于絕對收入,由于社會上比較心理的普遍存在,更取決于個體相對收入的高低。當經濟增長帶來個體收入增長的同時,實際上帶來的是所有人收入的提高,這在相對水平上,意味著個體收入并沒有增長,因而,個體也便不會感受到收入增長所帶來的刺激,國民幸福感亦不會隨著國家經濟的發展而上升,這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伊斯特林悖論”。
二、參照群體與“相對幸福感”
受相對收入理論啟發,提出“相對幸福感”這一概念,以進一步解釋個體社會經濟地位與幸福感之間的關系。社會經濟地位主要由個體的收入、受教育程度和職業狀況三個維度構成,相對收入理論著重從收入這一維度對幸福感悖論進行了解釋。“相對幸福感”概念則涵蓋了更多的維度。此外,相對幸福感認為個體的感受是相對的,要放在具體的生活環境中才到能夠得理解。
幸福感是一種個人的主觀感受,而人的主觀感受或對自己的評價往往是從他人那里得來的。也就是說,人們會在意別人如何看自己,從而得出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這就是庫利的“鏡中我”理論。按照“鏡中我”理論,周圍的人(參照群體)會影響個體的自我判斷。舉個簡單的例子,如果一個中產階級整天混跡在富人圈里,那么不僅富人會把他當作一個“窮人”,而且他自己也會傾向于把自己定位為一個“窮人”。上述例子表明,人對自我的判斷和主觀感受是受周圍環境影響的,是一種“相對感受”。據此,筆者認為主觀幸福感也就是一種“相對幸福感”。可以將“相對幸福感”作這樣的定義:它是指當人們將自己的實際生活境況與某種標準或某種參照物相比較,發現自己處于優勢或沒有處于較大的劣勢時所產生的(對生活的)某種肯定態度和積極感受。
據此,筆者認為收入、受教育程度和職業狀況等社會結構性因素不會對幸福感有直接的影響,因為每個人所處的具體環境不一樣,他們幸福感的“參照物”也不一樣。收入高低和受教育程度只是相對于周邊的人而言,如果農民和農民比較,工人和工人比較(李培林、李煒,2007),那么職業狀況顯然對幸福感的影響不大。
所謂的“相對幸福感”,即指人的主觀幸福感要放到一個具體環境中來理解,這個環境必須和他們的工作生活學習息息相關,因而才有參照對比的意義,也就是環境及環境內的個體構成了他們日常生活中的參照系,或者參照對比的對象。
人們是如何選擇參照群體的呢?人們往往根據社會經濟特征或者地理范圍界定參照群體。地理范圍體現了共享的環境資源與限制,也代表了面對面交流與互動的可能性。對城市居民而言,社區居民往往就是他們的參照群體,住在同一社區,不僅代表了他們較為相近的社會經濟特征,也提高了日常生活交流與互動的可能性。當然,城市居民的參照群體也有可能超出社區范圍的限制,社會上的其他一些群體也有可能成為他們的參照群體。需要從社區環境建設和社會環境建設兩方面著手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幸福感。
三、如何提高城市居民的幸福感
(一)從社區環境建設提高城市居民幸福感
根據上述分析,人們的幸福感并不應該用收入、受教育程度以及職業狀況等個體的社會結構性因素來衡量。人們的幸福感是一種相對感受,受周圍具體環境的影響,只有放在生活環境中才能夠得到理解。因而,要提升個體的幸福感,應該從提升個體周邊的環境做起。對城市居民而言,這個具體的環境就是他們生活的社區環境。應該從以下幾方面提升社區環境,從而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幸福感。第一,社區生態環境建設。把社區的生態環境建設好,給社區居民一個舒適干凈的活動空間,他們才會有愉悅的心情。此外,如果每個人都關心社區的環境衛生,自覺把垃圾扔到指定位置,不隨手扔垃圾、不占用公共資源等,那么社區內的沖突、鄰里間的爭吵也會減少,這也有利于營造和諧的社區氛圍。第二,社區保障與安全建設。有研究表明,社區的安全系數會對社區居民的生活幸福感產生影響,社區越安全,居民的生活幸福感越高。此外,社區的安全保障程度也會影響到社區居民之間的交流與互動,當社區安全環境良好的時候,人們更愿意在社區公共空間交流,而且不會受到時間的限制。比如,不會因為太晚而不敢在社區散步、聊天等。第三,社區文化建設。社區文化建設是社區環境建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因為幸福感主要是由個體在環境中的位置以及環境的氛圍決定的。如果個體在一個攀比氛圍比較重的環境中,而他在環境中的社會經濟地位又比較低的話,那么他的生活幸福感也會比較低。但如果在社區中形成一種互幫互助、和諧友愛的氛圍的話,盡管個體在社區中的社會經濟地位比較低,他也會有較高的生活幸福感。
(二)從社會環境建設提高城市居民生活幸福感
由于資訊的發達以及社交的需求,人們的參照群體往往會超出社區層面。當參照范圍擴展到地區或國家層面,國家或地區間的收入不平等水平則成為影響個人主觀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二者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系(黃嘉文,2016)。因而,從國家層面來說,要想提高居民的生活幸福感,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減少地區間的收入不平等現象。社會不平等是多面向的,除了收入不平等之外,還存在其他的一些不平等,比如公務員系統中的貪污腐敗。目前中國正處于政府職能轉型期,“反腐”“反貪污”“打虎”等詞匯一度成為熱門詞匯。國家處理了一大批“特權”官員,實際上就是為了重塑社會公平正義之風。只有社會越加地平等公正,人們的生活才會越來越幸福。隨著城市房價的攀升,住房日益成為影響人們生活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城市居民日常討論的話題就是“誰誰又在哪買了房子”,“哪家的姑娘嫁人一定要有婚房”等。住房資源分配的不均勻以及高壓的房價,讓部分買不起房的城市居民有了巨大的“被剝奪感”,這導致了他們生活幸福感的降低。因此,為了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幸福感,政府還需要在房價調控方面下更多的功夫。
四、結語
為了回答為何社會經濟地位更低的農民及農民工生活幸福感卻并不低于(甚至高于)城市居民這一問題,本文提出了“相對幸福感”這一概念。該概念認為幸福感是一種相對感受,是在具體的生活環境中通過與他人的比較而得出的。因而,個體幸福感的高低,一方面取決于參照群體,另一方面還取決于具體環境中的互動氛圍。以城市社區生活為例,當社區中有良好的互幫互助傳統,能夠營造出和諧互助的社區氛圍,社區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便會得到提升。當參照群體超出社區層面,社會不公以及高昂的房價便會對城市居民造成強烈的“剝奪感”,因而,政府需要在塑造社會公平正義之風以及調控房價上下更多的工夫。
參考文獻:
[1]黃嘉文.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與中國城市居民幸福感[J].社會,2013(5).
[2]黃嘉文.收入不平等對中國居民幸福感的影響及其機制研究[J].社會,2016(4).
[3]懷默霆.中國民眾如何看待當前的社會不平等[J].社會學研究,2009(1).
[4]李培林,李煒.農民工在中國轉型中的經濟地位和社會態度[J].社會學研究,2007(3).
作者單位:
上海大學社會學院